手执光芒行于云间的言说
——黎阳诗集《蜀道》的精神维度与审美特质探析
李恒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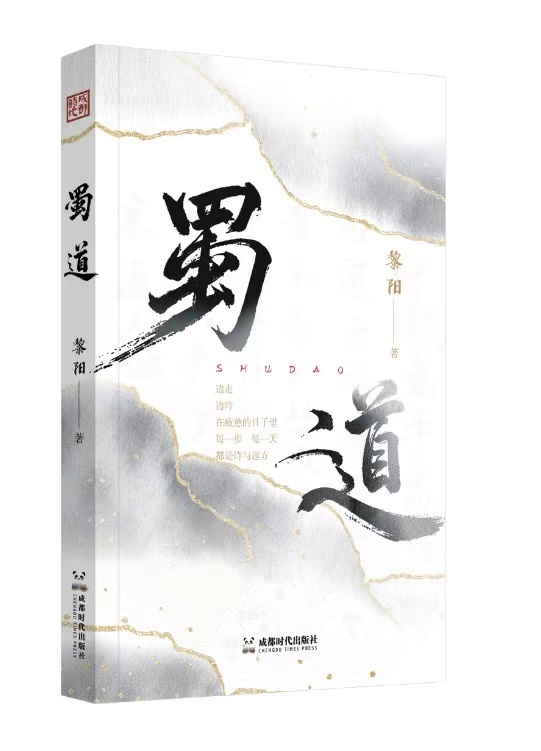
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张炜曾深刻指出:“诗是真正的言说,心灵的回响,存在的隐秘,行动的刻记。”“诗人的光荣,是放射在时空中的生命的闪电。”捧读黎阳的新诗集《蜀道》,其文本实践恰恰构成对张炜诗学论断的精湛印证。《蜀道》之“道”,既是地理空间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亦是人生行旅之道与诗歌创作之道。诗集中的诸多篇章,正是诗人“手执闪电之光,行走于云端”所迸发的“真正的言说”,在个体经验与存在本质的瞬间共振中,照亮了存在的隐秘。
现代诗歌的核心魅力与神性光辉,是潜藏于“个体经验与存在本质的瞬间共振”之中的。它既非宏大叙事的抒情,亦非刻意为之的象征,而是在语言的褶皱深处,某个被日常经验所遮蔽的“裂隙”骤然敞开——它可能呈现为一片落叶坠地的微妙弧度,地铁中陌生人袖口的细微磨损,抑或是午夜梦回时一句语义悬置的呓语。在这些看似琐碎、私密、甚至带有断裂感的瞬间,个体的感官经验倏然触及了超越个体性的存在:时间的绵延质感、万物的普遍关联、存在的荒诞性与庄严感。
这种共振具有“隐秘”性,因其拒绝被理性或科学的逻辑完全拆解,如同水底月影,一经打捞便趋于破碎,只能在语言的留白处悄然闪烁。它构成诗歌的“核心”,盖因诗歌的终极重量从不源于题材的宏微,而在于这瞬间共振所凝聚的精神浓度——它赋予平凡物象以陌生的神性,使私密痛感升华为人类共通的生存经验。
而“神性”正源于此:它不指向任何具象化的神灵,而是在人与世界的遭际中,偶然窥见的那一层“超验的薄光”。正如里尔克在《严重的时刻》中所写:“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个体的孤寂在特定瞬间骤然接通了世界的整体孤寂。这种超越个体边界的普遍共情,正是现代诗歌最动人的神性所在,它使每个普通读者在文字中成为存在的见证者与代言人。
在黎阳的《蜀道》中,这种“瞬间共振”的“闪电”效应清晰可辨,并主要体现于以下四个维度:
首先,历史在场性与时空折叠:在语言的褶皱中唤醒“过去的当下性”
黎阳笔下的蜀道,绝非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是承载着集体记忆的“时间容器”。在《驷马桥》中,诗人伫立桥畔,“北上的身影,还有马蹄声/隐约在时空,只有如今的路灯/还能照亮司马相如的汉赋”。此处的“路灯”与“汉赋”构成奇异的对话结构——现代照明工具转化为照亮历史文本的媒介,历史人物的身影并未消逝于时间洪流,而是“隐约在时空”之中,与当下“我们的脚步”形成深远的互文回响。这种书写策略有效消解了线性时间观的桎梏,使历史不再是博物馆中的静态标本,而成为能与当下主体呼吸相通的“活态在场”。
《宝墩古城》一诗的时空折叠更为显豁:“天府之根,确实有点长/一两块砖瓦不足以见证/光阴的结症”。诗人以“结症”隐喻历史的幽微关联,而“我们雨中来,也在/雨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洗涤,我们心中的困惑”,则将个体的当下探访(雨中寻踪)升华为与历史对话的精神仪式——“雨水”既是自然元素,亦是涤荡认知迷障的隐喻,使“城内的地基和城外的壕沟/分界出家的囯圉”的古老空间结构,在当代凝视下显现出“家的波浪,才能分蘖/枝系的涟漪”的内在生成逻辑。此种书写深度契合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提出的“记忆之场”理论,蜀地古迹被转化为激活集体记忆的“场域节点”,个体经验与历史本质在触碰物质遗存(砖瓦)的瞬间达成深刻共振。
其次,地理空间的精神赋形:山川草木作为心灵世界的“具象符码”
黎阳深谙“蜀道难”的文化基因,却未止步于地势险峻的表层摹写,而是将蜀地自然景观内化为精神漫游的“象征性路标”。在《西岭的肩上》,“白雪凝固千年的风寒”,西岭被赋予“肩膀”的拟人化意象,成为历史重负的承载者;“松塔是白的,白桦也是白的/以至于鬓角的白,算不上白/只是岁月的灰”,此处“白”与“灰”的色彩对比构成存在论层面的哲学思辨——自然的纯净之白与个体生命的沧桑之灰形成张力,最终在“被雪裹紧的身影/消失在一场暴风里”的意象中达成和解,个体生命轨迹与自然的磅礴力量在瞬间获得统一。
《在雪里,不要抱错了人》则将自然景观转化为深刻的生存隐喻:“冰的躯体遇见了一柄/无法可避的软刀/定格在雪光里”。“软刀”意象蕴含多重阐释空间,既可指涉严寒的物理侵袭,亦可象征人际关系的无形伤害。而“这个春天/有很多开不起的零度玩笑/不是所有的暖,都来自抱团”,巧妙地将自然现象(零度)与社会经验(群体性虚妄)进行互文勾连,使“雪光”成为照彻生存真相的镜鉴。诗人最终“把最后一个词,落在牙关/这是流放者的底线”,“牙关”既是生理部位,更是精神坚守的象征。结尾“暖,系在纸鸢上/当落日的颜色铺满雪线/一定是黎明的栅栏”,则令自然景观(雪线、落日)成为精神希冀的载体,地理空间由此升华为灵魂淬炼的“精神试炼场”。
第三,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共生:在私密性中开掘普遍性情感基质
黎阳诗歌常带有鲜明的个体印记,然其“私人化”叙事从未陷入狭隘的自我沉溺,而是始终保持向集体经验敞开的维度。《草堂灯影》中,“母亲还在织补我的衣裤/父亲劳累的鼾声撞壁回旋/‘锄禾日当午’的汗水流入比比画画之中”,这些细节充盈着私密记忆的温度——母亲的劳作、父亲的疲惫、童年启蒙诗句的浸润,共同构筑了个体成长的“精神原乡”。而“而立于天地之间的儿啊/找不到回家的路/只有草堂的灯影,随一条河流/流出笔尖”,则将个体的精神迷惘——“找不到回家的路”——升华为人类共有的存在困境,草堂的灯影超越了杜甫的专属符号,成为所有精神漂泊者的心灵航标。
《思念,一杯浓郁的咖啡》进一步将私人情感推向普遍性的情感结构:“窗外的阴霾,随着风/辗转在温暖的脊背上/轰隆的雷,在远处击打着目光/以外的呼唤”。“两根筷子,夹不住/一根滑润的面条”的日常细节,精准隐喻了思念之情的难以把握;“另外一双筷子去了远方/身体很快就能回到对面的椅子上/但是,整个屋子少了一个/流动的背影”,则以“流动的背影”暗示缺席者的永恒在场——物理空间的空缺反而强化了情感存在的真切感。这种书写印证了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学观点:“最高的现实是想象的现实”。个体的私密经验在诗歌的熔铸下,显露出“世界突然归属于自己这一棵树/自己却不知道归属于哪一片叶子”这一人类共通的存在论困惑。
第四,意象建构的审美特质:瞬间共振的艺术实现途径
意象作为诗人主观情志的艺术性具象载体,是连接主体内在世界与客体外部世界的核心纽带,它创造独特的认知效果与审美体验,堪称诗歌艺术生命的决定性细胞。无意象则无诗歌,此乃诗学共识。
黎阳诗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与最动人的审美力量,正源于其精妙的意象营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被视为深具个人风格的“意象派”诗人。其独特的意象群赋予诗歌鲜活的生命力,构筑起不可复制的“意象图景”。
想象奇崛,神韵契合。黎阳的意象创造常突破常规联想逻辑,在看似疏离的事物间建立深层的精神关联。“雨滴是荷花的来信/沿着流水,奔赴花香的暗示”(《在月花村,遇雨》),将雨滴喻为“荷花的来信”,其想象超越了雨荷间的物理滋养关系,赋予雨滴以信使般的主动性——它“沿着流水”奔赴“花香的暗示”,使自然现象成为一场精神邀约的参与者。此处的“信”与“暗示”构成隐喻性对话,雨与荷的相似性不在于形态,而在于“传递精神信息”的神韵契合。
“锦封未拆香先透”(《锦封未拆香先透》)将花朵绽放想象为“未拆的锦封”,“香先透”的细节颠覆了“先启封后见物”的物理逻辑,使花香成为穿透物质阻隔的精神信号。“花蕊如同腮上的面霜一样/总会陷入一些目光里的期许”,将花蕊比作“面霜”,貌似悖谬,却精准捕捉到两者共有的“柔嫩质感”与“被凝视的期待”,这种基于神韵的相似性使意象张力充盈——花朵的绽放由此成为一种蕴含羞涩与期待的生命呈现。
动态赋形,生机勃发。黎阳擅长捕捉事物的动态瞬间,使静态景观在语言中获得流动的生命力,形成富于视觉节奏感的“动感意象”。“北上的身影,还有马蹄声/隐约在时空,只有如今的路灯/还能照亮司马相如的汉赋”(《驷马桥》),“身影”的“北上”、“马蹄声”的“隐约”、“路灯”的“照亮”,构成一组动态蒙太奇,令历史的回响与当下的光影在时空中交织流动。“我们的脚步是自己的回音/从鬃毛扬起的风势中获得/指南针精确的维度”,则将脚步、回音、风势、维度串联为动态的感知链条,使行走本身成为与历史对话的“行动诗学”。
《罗城船中楼》的动感更具层次:“奔忙的汗水浸在丝绸汗衫上/浅斟慢饮悠闲的时光/躲在云后的笑容开放在一瓣/香甜的新桔之内”。“奔忙”与“悠闲”形成张力性对比,而“船行万里,搁浅在罗城的山顶/楼上的旌旗摇晃出斑斓的历史”,则使“船行”的动态与“搁浅”的静态构成戏剧性冲突,最终在“三两声号子,落进翻开的茶盏”中归于精妙的平衡——历史的壮阔喧嚣与当下的日常声响,在动态语言中达成和解。此类动感意象的营造,使诗歌节奏与蜀道行旅的韵律形成同构,阅读体验如身临其境。
意境唯美,虚实相生。黎阳诗歌的意境营造兼具画面的澄澈度与思想的幽邃感,如中国古典水墨之“留白”,为读者预留丰沛的想象空间。“西岭的肩上,白雪凝固千年的风寒”(《西岭的肩上》),“肩上”的拟人赋予西岭以生命温度,“白雪凝固风寒”在静态中暗含时间的绵延,而“口中喷吐出的热气/形成往事的屏障/薄如轻纱的屏障”,则以“轻纱”意象使“往事”既具象可感又朦胧氤氲,营构出“可触而不可尽”的唯美意境。
“黄钟邛海,我把泸山的月捧着/烟波浩渺,在岸边守望泸山的倒影/用一盏茶的光,沉浸岁月的麻团”(《黄钟邛海,我把泸山的月捧着》),“捧月”、“守望倒影”、“茶光沉浸岁月”,一系列动作与景观交织成空灵画卷——月在掌中,影在水里,岁月在茶盏之内,虚实相生间,物我对话呈现出深邃而温柔的质感。“高原的月亮,或许和平原的不一样/我从水中捧起,就再也放不下”,将捧月的瞬间凝定为永恒意象,“放不下”的不仅是月亮,更是对这片土地的精神皈依,意境唯美而余韵悠长。
黎阳在《后记》中坦言:“蜀道,既是‘说蜀’,也是‘蜀说’。《蜀道》是我的踪迹史,也是我入川行吟的路线图。”这一自述精准揭示了诗集的核心特质——诗人以虔敬的“聆听者”姿态,使蜀道的历史、地理、文化在个体的行走与凝视中“自我言说”,而其诗歌则是这场精神对话的忠实记录与艺术结晶。
从司马相如的汉赋到宝墩古城的砖瓦,从西岭的白雪到邛海的明月,从草堂的灯影到罗城的茶盏,黎阳手执诗歌的“光芒”,行走于云间的蜀道之上,使个体经验与存在本质在每一次触碰中迸发“瞬间共振”。这种共振,使《蜀道》超越了地域性诗集的范畴,升华为一部关于“行走”与“聆听”的精神史诗。它昭示:真正的蜀道不在地图坐标之中,而存在于每一个与历史对话、与自然交感、与自我坦诚相对的刹那。诚如诗人在《天元》中所书:“剑门在上,手执万卷的书生/锦衣怒马踏遍千里云和月”——此处的“书生”既是历史剪影,亦是每一位在精神蜀道上跋涉的现代人的写照。只要葆有聆听的姿态,我们终能在时间的褶皱里,邂逅那束属于自己的“生命闪电”。
李恒昌,1963年生人。铁道战备舟桥处原党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济南市首批签约作家、2021年度泉城实力作家。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香港文艺杂志社签约作家。曾获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中国铁路文学奖、刘勰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山东省第三届视听文学剧本大赛一等奖等。先后出版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20部。主要作品有“大地系列”之《大地上的血粮:莫言创作评传》等六部;“大河系列”《大河赤子》等三部。《大河赤子》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2024年主题出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24年八月“中国好书”、202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年度影响力图书。《大河涅槃》入选山东省委宣传部精品工程提升工程重点项目、山东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大河安澜》入选山东省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山东省“走在前、开新局”重大题材文学创作出版项目。作品散见《长篇小说选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解放军文艺》《香港文艺》《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





茶水分离 市树市花,扫码聆听超然楼赋
超然杯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
丛书号、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