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工四叔
李召新
吃了饺子,四叔又长了一岁。都快三十的人了,可还没娶上个媳妇,愁人。可愁的不是家里穷,而是一个“富”字。
四叔不是我的亲叔。他跟父亲是一个老爷爷的重孙子。在兄弟姐妹六人中,他是老大。一米七八的个头,不胖不瘦,身强力壮。虽然没上过几天学,可也是村里出类拔萃的帅小伙了。按照家族的声望和他自身的条件,应该是媒人能挤坏门框的那一类。然而,他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富农”成份成了他找媳妇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刚满十八岁那年,上级下达黄河清淤任务,村里公布河工名单,他的名字——李现海,出现在了上面。他成了村里年龄最小的河工。大队上的理由很充分,要让他用劳动的汗水洗刷他从娘胎里带来的污浊,跟富农家庭划清界限。自那一年起,他与黄河的缘分算是剪不断了。
开始,没经过世事的四叔并不拿这事当回事儿。庄稼人,推车子、受大累,正常。出河工,那是应尽的义务。你不去,他不去,总得有人去嘛。再说了,四叔身大力不亏,不怕累。他心里还说,出河工咋了?挣的是高工分,吃的是集体的粮食。我一个人上河,全家人受益。可不,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一顿饭跟三个人的饭量。他出河工这些天,家里一锅饼子都格外能多吃一天了。另外,他在黄河上干一天活,还能挣到两毛钱呢。这钱不仅能贴补家用,还能买回点稀罕物不是?
记得有一年,我才九岁。晚上吃饭时,父亲对我说:“你四叔回来了。”我问父亲:“四叔不是去修黄河了吗?”“任务完成了呗。”我刚钻进被窝不一会儿,就听见四叔踏着“噔、噔”的脚步进了屋。但见他从黑色的夹袄兜里掏出两把手指肚般大小、长满了麻子脸的东西,让我看。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东西。正纳闷,母亲说:“这是你四叔给你带回来的长果。”长果?就是小伙伴说的又脆又香的长果?“不光是长果,还是熟的来。”说着,四叔就给我扒开一个,两粒红色的长果仁放在我的手上,“快尝尝,香不香?”我明白,四叔拿我当他的孩子一样待哩。我急不可待,就把两粒长果仁儿放进嘴里嚼起来。“真香呀!哎,四叔,真好吃。”我吃着四叔给我扒得长果,望着四叔问:“四叔,这东西一定很贵吧?你从哪里弄得钱?”母亲忙接过话茬,“这是你四叔上大河、受大累挣钱从黄河边上买的。”
“上大河,受大累!”这话一点不假。听四叔说,他们在黄河上住的是阴暗潮湿的地窨子,喝得是带着泥沙的黄河水。每天早晨天刚亮就上工,直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他干的是推小车的活,当然那是河工里最累的。装满一车泥沙,他要推起车子走桥板、爬河堤,再走三四里的土路,然后爬上一个大大的坡,把泥沙送到二河摊上。先不说这泥沙的重量,单是这来回的路,高洼不平,车把摇晃,弄不好就会人仰马翻,甚至受伤······就这样,一天要走三四十里的路程。四叔说,出河工,最要紧的是鞋要可脚、结识,要多带几双。那些年,四叔虽然还没娶上媳妇,可几个妹妹没少给他做鞋。纳鞋底时用的绳线都是特别结实的纯麻线。
没过三年,年轻、实在、能干的四叔就以肯干、会干名扬工地,得到了营部、团部的好评。那年工程结束时,大家一致推荐四叔为治河标兵。可那时候什么都要政审。很快,政审下来,一个大红的印章上写着三个歪歪扭扭的黑字:“不合格”。打那以后,四叔有点蔫了,本来就不爱说话的他话就更少了。只是他还是跟以前那样,该干啥干啥,该咋干还咋干。
一年,两季;春天,秋上;历城,齐河;清淤,筑坝······只要有黄河工程,他那一回也没落下。就连营长也认识他。有一回,工地上遇到了塌方,连里叫苦不迭,说这活没法干了。没法干?营长说:“快去叫李现海的那个小伙子来,看看他能干不能干。”四叔推着车子,挽着裤腿,来到现场。一声没吭,先是把泥兜儿铺在车筐里,又横握着铁锨,轻手轻脚地把泥沙捞进筐里。装满后,他低下头、挂上袢,架起车,吼了一声:“走了!”在纤工的协助下,他艰难地走出了泥泞。随后,他听到了一阵掌声。
大妹出嫁了,他高高兴兴地给妹妹送行;二妹也出嫁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送妹妹出嫁。可他的心里不知是喜还是悲。五十多岁的父母也曾萌生过给他和妹妹换亲的想法,可四叔坚决不同意:“我不能用妹妹的泪水换自己的笑脸啊。”同村里伙伴们的孩子都上小学、上中学了,可他还是孜身一人。再出河工,老支书问他:“要不今年咱不去了?”四叔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去!”四叔的决定让父母更添愁容。他在身边,这么一个大活人,成天不高兴,当父母的心里难受。离开家一个月,就又挂着他:“天冷了,别冻着。”“身子是自己的,可别累坏了,坐下病根儿。”
不管是左邻右舍,还是修河的工友,都发现:四叔的性格变了!半天不说一句话,说句话就能噎死个人。有人背后叫他斜子。也就是这一年,四叔修河回来,带回一对鸽子。从此,人们看到,他除了干活,就是伺弄他那对鸽子,他跟鸽子成了好朋友。成双成对的鸽子繁殖很快,大的生小的,小的又生小的,不到两年,他的队伍变成了七、八只。白鸽子红眼睛,身上没有一根杂毛。灰色的鸽子,鼻子上还有一撮毛。四叔把精心制作的风葫芦,拴在领飞的鸽子尾巴上。一群鸽子在天空中飞翔,高低不同的声响,引人驻足观看。或盘旋,或远行。那阵势,蔚为壮观。望着它们,四叔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模样。可是,鸽子是要吃粮食的,还得吃好粮食。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那几年,日子紧吧,人也还吃纯棒子窝头呀,何况鸽子呢!唉,没办法,三十出头的人了,还没成个家。当父母的觉得问心有愧嘛!随他去吧。
修河的工地上是绝对不准喝酒的。别说是没有,就是有也不准喝。一帮子男人,喝了酒,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打起架来,那可是无法控制的事情。四叔当然遵守这个纪律。回到村里,他一天三顿饭在家里吃,一年也没有一个喝酒的机会。只是除夕夜,我父亲一定要把四叔叫来,兄弟们守着家堂,让他尽情地喝个年夜酒。然而,为了照顾家人的情绪,局着面子,四叔喝上三两酒就自动退场。他要到村东头的好哥们那里去喝个痛快。一年一场酒,一年一个醉。他要把这一年的不痛快、不开心发泄出来。
我考上中专的那一年年,国家进入历史性转折,四叔家也喜鹊登枝了。一个比四叔小六岁、没了丈夫的女人,来到四叔家,要成为我的四婶。听到这个消息,我赶紧请假回家。我要为四叔写对联,我要把大大的喜字贴满整个家族的大门、屋门,让大红的颜色赶走这多年的晦气。刚刷了黑漆的门边、门扇上,鲜红的对联格外醒目,喜庆极了!生产责任制的第一年,四叔的女儿出生了,第三年,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帅哥降临到四叔家。人们都说:“老天不负实在人呀!没想到,打了十几年的光棍,如今儿女双全了。”这时,人们发现,四叔的脾气不斜了。
从十八岁到四十岁,二十多年里,四叔不知道自己出过多少回河工。但他记得:修黄河的活,他一次也没拉过。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在家。一次是在邢家渡工地,一次是在二级沉沙池上。
四十不惑。四叔的四十岁赶上了好时候。责任田分到家这些年,在河上干活从不耍滑的四叔,种自己的地、干自家的活了,更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他跟四婶儿忙得脚不沾地:种麦子,他家的麦子产量高:种玉米,他家的玉米棒锤最大:种棉花,他家的棉花成色最好。那几年,村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政策好,天帮忙,黄河水的滋润咱多打粮。”四叔说:“要说这黄河呀,我是知道它,这些年清淤筑坝、引黄灌溉,黄河水围着咱的地转,咱这庄稼它能不好?”
时代在变迁,大河保安澜。这些年,机械化作业,调蓄调沙。黄河这匹野马,被咱驯服了,听话了,变害为利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四叔和那些为黄河安澜付出血汗的河工们不可磨灭的功劳!
四叔走了有七、八年了,可在他的大门洞里,一辆车把磨得光滑发亮的手推车还挂在墙上。一个收古董的来过好机会,跟四婶儿讲价钱。四婶儿就是一句话:“这是俺家的宝贝,留着它是个念想,给多少钱也不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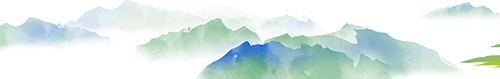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超然杯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