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三)
孙 涛
第二年,奶奶因年迈体弱,积劳成疾,再加上这几年的战火惊吓,终于病倒了,她得的是黄疸病,开始我们这些孙子孙女还能被允许到奶奶床前请安问候,可后来就不许我们再进奶奶的屋。怕奶奶嫌烦需安静,因为奶奶一犯病,就痛的死去活来,不停地叫喊,得一口气吸五六个大烟炮才能止着疼,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很快就被疾病折磨得骨瘦如柴,大伯他们虽然到处请医生来家诊治,可没有一个医生能使病症减轻,反而越治病情越重,奶奶日夜煎熬,全家人却束手无策。亲朋好友闻讯都前来探望,忽然有一天我三姑坐着马车,三姑父骑着一匹日本洋马带着一队伪军来廖家村探视,奶奶知道后立刻向大伯下令,不准汉奸进家门。
三姑父原来是八路军,不知什么原因又成了汉奸队的大队长。
奶奶不仅拒见三姑父,就连三姑也不准进后院,三姑托我娘去给奶奶说情也没用,就是拒见。没办法,三姑一家当天就返回东平县城,晚上听爹娘聊天,知道三姑父是共产党派到东平县城的卧底。
奶奶的病一直不见好,有一天来了一位疯疯癫癫的道士,据说这个道士每天只化缘七个人家,吃不饱就吃柏子仁和松子仁,云游四方。道士是上门求布施的,看门人多给了他一些食物,他拿着就走,不过回头说:“这家老太太积善一生即将驾鹤西去,这家犯重丧,不出百日还要死个长头发的!”疯道士的话很快在全家传开,我听小婶子和二大娘拉呱议论,小婶说:“还得死个长头发的,二嫂,呀三嫂马上生孩子了……”
“别胡说!”二大娘急忙岔开了话:“老三家,人那么好,是不会有事的!”
我的心一沉,我娘要生第六个孩子啦,莫不是,死个长头发的是我娘,我害怕极了。
我奶奶死后,家里准备发大丧,大门口右侧竖起了一根用白不缠绕顶端扎着一个大纸鹤的杉篙,所有的门都贴上白纸,跑差的到亲戚朋友家去报丧,很快吊丧的亲戚朋友都上门吊丧,我们各房小孩不跟着大人守灵,待在屋里。
奶奶死后第二天,我娘顺利生下我六弟,我娘没有死,我放心了。
在奶奶出殡前的红场日,就是封建社会给逝去老人写牌位,在那神主的主字上用银珠点上一个红点,也就是点主。这时候所有孝眷,都要穿青不穿白,所以叫红场。我小叔守灵就叫小婶去拿青布鞋,可去了半天一直拿不来,小叔烦了,就派鸣露嫂子去催。到中院一看,房门关着,叫无人应,门推不开,从窗棂撕破窗纸往屋里一看,啊看到五婶子躺在地上,鸣露嫂子急了,忙叫帮丧的男人,朱康苓用力撞开房门,鸣露嫂进去一看,小婶子已气绝身亡。真是应了疯老道的预言,犯重丧死个长头发的。这个天大的不幸落在我们家中,我大伯立刻派专人,到我五婶子娘家报丧,说急病死亡。她娘家来人,也没说什么。当时医学并不发达,因此也没弄清死因。根据我现在身为副主任医师的经验判断,我小婶子身体胖大,很可能患有高血压病,因忙于我奶奶丧事,几天几夜没能好好休息,过度劳累。所以她回房拿鞋,想在屋内小便,把门拴上,因事急,尿完急着起身,就发生了因排尿引起的体位性休克。因当时无人救治,才身亡。
她娘家人询问是什么急病导致突然死亡,我们家没法回答,只是把事发经过详细讲明,最后两家商议,同意埋葬并同意随老人之棺同日出殡。
这下我可成了苦命的孩子。大人商议之后决定,因我小叔没有儿子,让我披麻戴孝打幡当孝子,还要摔尿盆子,我成了小婶子的亲儿子似的,也不和我商量,我听说后不同意,我爸爸瞪着双大眼说:“不行!你必须听大人的!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出殡那天,我在两个族人的搀扶下,先摔了尿盆子,然后起灵时打着纸幡,跟在奶奶的送葬队后面,向林地走去。路上前前后后哭声不断,可我一滴泪也流不出来,麻木的一点感觉也没有。让人搀扶着走到老林,下了葬,再回到家,累得实在不行,脱去外衣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
丧事结束,接下来就是在舅爷爷的主持下分家,我又有了新任务,代替我四叔这一房抓阄分家产。
我舅爷爷鹤发童颜,宽宽的额膛,寿眉大眼,长长的白胡须飘在胸前,一看就是慈祥老人。自从我奶奶病重他来我家后,就一直没走。
我们这个家是他帮着发展起来的,今天又是他把这个家分开。
先分房产,参加抓阄的孩子是大伯家的小哥哥钢钟,二伯家的小妹贵琴,我们家是五弟小虎,四叔家由我代抓,五叔家是小妹友琴。我大伯家的钢钟第一个抢着抓了第一个阄,接着我抢着抓了第二个阄,因我五弟年龄最小,抓的是最后一个剩阄。
结果,后四合院被我五弟抓了,中院被二伯家贵琴小妹抓到,前院被小叔家友琴小妹抓到。我和钢钟抢着抓,结果是村南头场院,一分为二两家,当然还有建房款。
土地和酒厂油坊的股份都分完后,我大伯又把所有种地户子,和酒厂油坊的雇员以及管事的,长短工,凡是被雇佣人员,都请到家里,由账房先生宣布所有借的债,欠的租,或预借的工钱等等一切账目核实清楚后,我大伯当众宣布,按我奶奶遗嘱,奶奶生前所有借欠账目全部作废。说完把所写的借条和欠款字据当众焚烧,一笔勾销。
家就这样分了。我们搬进后院奶奶住过的大平房,我家兄弟人多,总算能住的宽敞些。不过我大伯仍住在后四合院,也就是对着大平房的南屋里。我大伯的小哥哥,一直很自强,他抢着第一个抓阄,心想一定会抓到这后四合院,可他手臭,就是没抓着。有一次因为天晚,我便把后院角门拴上,可他回来晚,推不开门,就没命的砸门。吴妈听到声音赶快去开门,他进门就在院里大声吼叫:“怎么,想撵我们吗!得三年以后,再说!”
我大伯听见,出屋把他臭骂了一顿,他才住嘴。但是大嗓门几乎把所有人都喊醒了。
我爸爸知道是我栓的门后,狠狠的在我头上扇了两巴掌,“就是你能惹事!”
钢钟哥就到处散布,舅爷爷这次主持分家不公平,分房产不应该抓阄,应该按哪方对家贡献大,出力受累多的应先挑,长子长孙有优先权。这些话,说白了就是他们自己家的心思。
奶奶去世,真是塌天之不幸。家里再也没有往日的欢乐,死气沉沉,分家分的失去了亲情,虽还在同一屋檐下,心早已疏远,特别是住在后院的大伯和我们两家,我们家说话都特别小心,生怕哪句话不当引起大爷大娘生气。所以原来的灶房还是决定让给大伯家用,我们把原放粮食杂物的西房腾出权做灶房。
五叔家的妹妹友琴,母亲去世,甚是可怜。幸亏我二大娘对她很是照顾,让她和贵琴妹妹同吃同住同玩。
昨天她姥姥家的舅妈来了,说是来看看外甥女,还带来了一些好吃的。
她舅妈向我五叔提出续弦之事,想把她家一个堂妹,二十八九的老姑娘嫁过来,当友琴的后妈,这样亲上加亲,友琴不会遭虐待。为了把这事办成,她舅妈,还一一拜访了我大娘二大娘和我娘,逐个解释促成这门亲事的好处。
当晚在奶奶住过的后院大平房内,我大伯二伯,父亲,还有大娘二大娘我娘,全家一起开会。因奶奶生前主张的家风是文明之家,所以奶奶的在天之灵想必一定会同意,我小叔早日续弦,好让这个家有个家的样子。可一谈到魏家这门亲事,我五叔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小婶子生前,曾多次说起她这个堂妹,从小就不正经,外号叫“百洞鞋”。这样一个女人,娶到咱家,会败坏我门家的名声。最后决定由我娘出面以服丧礼俗之由,将这门亲事婉言拒绝。
为了将这门亲事办成,友琴的舅妈,竟以关怀照顾为由带着友琴去了姥姥家,其实她姥爷是个老门头,军人出身,在军阀时当过旅长。不过两个儿子都不争气,吃喝嫖赌,小儿子魏绍文更是吸上了大烟,成了名副其实的败家子。这次续弦说亲,就是他的阴谋,本想续弦成功,他可出面狮子大开口,多要些彩礼。因为他家现在落破到实在入不敷出,他知道亲家富裕大方,在我小婶子活着的时候,他就到我家求过帮,我奶奶看着亲家关系,再说亲自上门开口,可想家景一定遭难,就和大伯商量给过他一千大洋。他吃过甜头,还想继续攀这门亲。可没想到老婆回来说:因服丧礼俗婉言拒绝。不过外甥女领回来倒是上策,先叫堂妹和孩子朝夕相处,增进感情,只要和孩子相处好,达到孩子喜欢堂妹的目的,孩子不愿离开,这门亲事自然就有希望。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仇人林家也看好孙家这门亲事,媒人上门一说,竟成了。
这下魏绍文恼羞成怒,再把友琴妹妹送回廖家村时,放话说我小婶子是被害死的,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得找个地方说清楚。要是继续结亲,可另当别论,。这是明显的敲诈,我们家便没有理会他这个茬。
魏绍文真是穷极生疯,竟一纸诉状告到县大爷那里说我家害死了他妹妹。虽木已成舟,他还托中间人放话说,仍可庭外协商,适当赔偿便可撤诉。
我们是书香门第家庭,而我父亲又是学法律,战前还在江苏做过法官,哪能容忍这种卑鄙小人敲诈戏耍,坚决应诉。
当时伪县长叫王伯芙,经过庭审,魏绍文认定她妹妹是被我们家害死的,竟提出开棺验尸。他认为我们心虚一定怕开棺验尸,因为这样会使我们家名声受到极大的影响,肯定不会同意,可我们家一致同意开棺验尸。
这件事几乎轰动整个东平县。验尸当天,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来看热闹。天气炎热,掘开坟墓,打开棺盖,法医先在全身七孔采样化验,说明没毒物后,又验头颈上肢和前胸后背,也没有外伤痕迹。验完上部无伤,魏家族人怕丢人提出不再追究下验。可我父亲是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又做过几年法官,自然不会同意验尸只验一半,坚决要求法医验下半身。魏方不同意再验,我父亲就向当场监督的王县长陈述验全身的重要性,只有全部验到,才能是非分明。县长准验下身,魏方当众出丑,下身仍无伤痕,说明死于暴病。
围观群众开始起哄,嘲讽魏家,魏家当场提重换一副棺木再埋,我们家不同意,就是这付原棺木,因为本来就是最好的柏木棺,所以只同意在外面再加一层杨木套。
官司判决魏家失利,本想官司结束,该没事了。王县长调走。又来了个叫张勉之的县长上任,魏家一看又来了报仇的机会,此人的父亲曾经和魏绍文的老爹在军阀同一个部队共过事,马上用钱贿赂张勉之,要求案件重审。在旧社会,真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有钱就有人情,有人情,就可以大事化小,也可以小事没事化大,把没影的事都说成有事,以势压人。真理受害,事实歪曲,没处说理,法律面前没平等。
张勉之立刻旧案重审,将原案人等传齐到堂,在堂上我父亲把这位张县长辩的哑口无言,当众丢丑,他彻底被激怒,不再允许申诉,连证人也一起关押在狱中不再审讯。为了挽回县太爷的面子,竟想对证人鸣露嫂痛打威逼,企图逼供。可鸣露嫂坚持她讲的经过是真的,逼供的目的没达到。
当然,你魏家能用钱买通县长,我们也能用钱买通牢头和狱卒。想让我们在狱中受苦遭罪,没门。
我记得,我娘把她姥爷家的表弟请来,专门替我们卖地筹钱,买主嫌贵就贱卖,急需用钱。有了钱,我大哥就先把老飞鹰牌的自行车拆卸开,把纸钱卷成小捆,用粗麻线拴连好放进车把和车梁的筒子里,避免进城门时,被日本鬼子和汉奸队搜去。就是靠这辆破自行车,不断地把钱送进城,然后去贿赂牢头和狱卒,使我父亲和小叔他们少受皮肉之苦。经过和魏家花钱比拼,魏家渐渐没有了底气,官司一直拖着,张勉之也没法审。后经省伪教育厅厅长贺锡龙等人调解,以为死去的小婶子立以“烈妇殉姑”四字牌和解结束。我父亲,五叔和鸣露嫂才被释放。可魏绍文厚颜无耻的一直跟着我五叔和父亲到城里三姑家中,张口就要钱来买大烟吸。我父亲一听,真是气炸了肺。我五叔刚想把他轰走,二大爷说:“咱们宽大为怀。”竟掏出一些钱给了他。魏绍文接过钱便走向大烟馆。
孙魏之诉就这样结束了。魏绍文不但钱没捞到还让自己的亲妹妹死后被开棺验尸,丢尽颜面。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用尽各种卑鄙伎俩,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父亲和五叔回家后,当晚五叔拿着一沓地契到后院我家,当面向我娘表示感谢,并提出把我过继给他,因我五婶子死后我替她摔过尿盆子之事。
我娘一听马上说:“不行,五弟,你再结婚后还怕生不出儿子吗,过继的事情咱就别谈了。”
“这次打官司,你在家卖地筹钱,我一分没花,所以这几十张地契你得留下,算我给小泉的。”五叔对我娘说。
我爸爸把五叔放在桌上的地契,交回五叔手上,说:“亲兄弟别这样,你倒可以给鸣露家些地作为补偿,人家一个证人,白白跟着咱受这牢狱之灾,我和你嫂子商量过啦,我也准备给她几亩地,算是补偿。”
“哥,你就不用了,我多给她几亩地就行了。”
我父亲和五叔继续谈事,我听得越来越迷糊,不一会就睡着了。
很快,我五叔把林家小姐娶进门,友琴妹妹终于有了后妈,家也算有了家样。
有一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听见父母两人谈话。
我娘说:“我总觉得住这后院,心不踏实,生活没着没落,你是不是和二哥二嫂商量商量,咱再搬回中院原来的东屋住。”
“说实在的这十几天,我住的心里也别别扭扭,不过,搬回去住也不是常法,等抗战胜利后,我在大城市有了工作,把你和孩子都接出去,到时把这个家交给老管家鸣珂大侄子管,不就行了。”
“那可好。”
我爬起来尿尿,才打断了他俩的谈话。
有一天突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人们高声呼喊着,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战乱终于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
没过多久,我父亲从报纸上,看到国民政府第二绥靖区招聘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官,我父亲当夜就去济南了。
报名考试,我父亲被录用为第二绥靖区军法处,中校军法官。
我父亲在济南安定好,立刻写信,兑现承诺。让我娘把家安排好,带着孩子去济南。我娘安排妥当后,又把打官司曾帮我们卖地的表弟请来托付他替我家监管,我娘把整个家交给了老管家鸣珂,并嘱咐他有事到苇子河找表舅商量。一切事情办妥之后,老鸣珂叫手下套了两辆马车带上家中细软,把我们全家送到泰安火车站。一直等到我们全家坐上火车,他才回去。就这样,我离开了生我养我,至今仍会在梦中再现的故乡廖家村。
到济南后,一切都很新鲜。喝水不用去井上打,院子里一个铁管子,接上一个铜管,把上头的一根小棍一拧就有水流出来。晚上再不用点油灯,把墙上一根绳一拽,灯就亮了,这叫电灯。我父亲已经给我找好了学校,是我们东平老乡,抗日英雄韩多锋办的学校社会部育幼院,我插班三年级。有一天放学回家,听我大哥说,他要去旁听审判日本战犯,主审法官是我父亲。我也闹着一起去,最后跟着我哥哥去了。审判地点在经二路纬二路和纬三路中间路南,紧挨着第二绥靖区大楼的西临。我哥哥持票领我进入大厅后,厅内已经坐满来旁听的人。台上坐着穿法官衣服的一排人,我认出我父亲坐在中间,他是主审。
宣布开庭后,宪兵把受审日本战犯押了进来,站到被告席上,这几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鬼子,终于站到中国的法庭上,接受中国法官的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我听不懂日本话,和翻译说的事,不过我知道这审判,给我们中国人出了气。
第二天上学,我就向同学讲述审判日本战犯的事,大家都觉得解气。
我虽是插班三年级,但并不吃力。功课我都能跟上,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叫张效良,他有一次出的作文题“记一件有趣的事”。
我写了在农村“翻湾”全村抓鱼的事,没想到竟得了一本小字典作为奖品。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声枪响,济南迎来了解放,结束了背着整布袋金元圈买东西,物价一日三涨的苦难日子。
渤海军区文工团就驻在我们学校,他们白天出去上街宣传演出,晚上学文化,练习唱歌,好不热闹!我和同学们都很羡慕。有一天他们正围着圈,在操场上吃晚饭,我和同学李家谌,贺俊三个围上前看。竟不约而同的问:“老总,我们能参加你们的队伍吗?”
一个女同志喜笑颜开的问:“你们想参加我们的队伍?”
“是啊!”“是啊!”
女同志向另一群人喊道:“团长,这几个同学要参加革命!”
团长急忙走过来,打量了我们三个人一下,就问:“你们真想参加我们的队伍?”
“老总……”
“别叫老总,那是国民党的叫法,咱们叫同志。”
不等团长说完,我们又异口同声地说:“同志,我们愿意参加!”
就这样,我们参加了革命,那年我们都十四岁……
第三天,我们就坐汽车,开赴到青州,分配到山东省卫生处卫校学习,到校后我们就发了军装和洗漱用品,很快投入到学习中。
我们分队的队长姓刘,对我们很关心,把我们安排好之后就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你们可以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啦。”
给家写信,可把我难住了,我只记得我们家住在一个巷子里,门口有棵槐树,什么街,什么号根本不知道,信没法写,好在我家庭观念不强,可时间一长,确实也想家,可没办法。
紧张的学习,占去了整个时间,这时才意识到文化的重要,还有好多字不认识,幸亏育幼院教语文的张效良老师奖给我一本小学字典,是我一篇作文获得的奖品。张老师告诉我:“字典就是不说话的老师。”说实在的,这本小字典一直伴随我到抗美援朝的战场。我能有今天的文化素养,这本小字典,功不可没。
六个月的卫校学习完,结业后,我被分配到省直属医院,当助理护士。队长又分给我两个护理员大姚和小朱组成一个护理小组,让我负责带教她俩,我负责执行医嘱,给病人打针服药,她俩负责病人的生活护理。她俩年龄都比我大,文化水平比我还低,那个大姚还是文盲,正在扫盲班学习,小朱扫盲班已毕业。有时她俩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我,我就耐心地告诉她们,可有时我也不认识,就和她们一起查字典。
我工作积极认真,经常得到队长表扬。月底在发津贴时,发现我比大姚和小朱多,我怕弄错,就向队长报告,队长笑着给我解释说:“没错,你多的是技术津贴!”
入秋的一天,队长分配我们组去护理一个肝硬化腹水的危重病人。危重病房设在村边场院的一间茅草屋内,吃过晚饭,我们就去接夜班。白班护士交代说:“病人病情危重,已无法治疗,梁军医交代要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病人虽处于昏迷状态,但是知觉还是有的,所以,还要按时测量血压,一旦发现病人血压下降或呼吸困难,你就给他注射,抗木否尔或牛司太母抢救”。我知道她说的是拉丁语的强心和兴奋呼吸的药品名称。
太阳很快落山,屋内已黑暗,大姚赶忙把屋内的棉子油灯点亮。我再次给病人检查了血压和脉搏,病人仍昏迷不醒,但仍吃力的呼吸着。
十点钟,梁军医来查房,检查完病人说:“病人的病情更加恶化了,做好临终护理准备吧!”
梁军医走后,大姚就把长板凳搬到门口,拉着我和小朱坐在凳子上。
我虽坐在门口,可眼一直瞅着屋内病人,病人因腹水而鼓胀得像皮球一样的肚子,一起一落,证明病人还有呼吸。风吹的屋内煤油灯火苗晃来晃去,静静的秋夜,传来秋虫的呻吟声,再加屋内马蹄表的滴答声,耳边又响起梁军医的嘱托:做好病人临终护理准备……一种恐惧袭上心头。
突然,小朱说:“看,病人肚子不鼓了,不鼓了……”
我赶忙进屋,检查病人血压没有了,心跳停止了,我扭头一看马蹄表,正零点二十三分。
大姚说:“孙老师,赶快去报告队长吧。”
可我怕狗,就说:“你俩去报告。”
“好!”说完她俩就走,可她俩刚出门口,我又大声喊道:你俩回来!”
大姚毕竟比我大,再说这种场面她早见过,就说:“孙老师,你是不是一个人害怕啊?”
我坦诚的说:“害怕,你摸摸,我心都快跳出来啦。”
“那好,你和小朱留下,我个人去报告。”她看到我还在病床前傻站着又说:“你俩到门口坐着就行,千万别让狗猫进屋。”
我紧抓着小朱的手,坐在门口的板凳上,再不敢看屋内那晃动的油灯和已死去的病人。时间一秒一秒的过着,我焦急的等待着队长的到来,秋虫仍在深夜呻吟着,我的心跳的更快了。……
当远处传来狗叫的声音,漆黑的村夜出现了手电筒的亮光,又听到了队长和大姚的说话声,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我跟队长到病床前,队长又用听诊器听完诊,又用手电检查病人的眼睛,发现瞳孔已放大,就说:“大姚你和小朱到总务科领军装,打热水,做死后护理。”
她们走后,队长就对我说:“对这些病故的同志,死后要做死后护理,要给去世的人净面净身,现在已进入秋冬季节,受条件限制,就只做净面净手护理就行了,然后给死人换一套新军装,待葬。不过给死人换衣服有一定的方法,当然像咱们四个人一齐给死人换衣服比较容易,要是就你一个人给死人换衣服怎么办呢,待会我教你,你一定好好学。
不一会,大姚和小朱就领来了新军装,并提来了热水、拿来了脸盆、毛巾。队长接过军装放在床头就把自己的裹脚解开,系了一个套,脱鞋上到病床,拉扒开腿站到死人身体的两旁就讲道:“一个人给死人换衣服,首先把这个套套在死人的脖子下面。”他边说边操作着:“然后把套再套在咱们自己脖子上,就这样,只要我们抬起头身来就能把死人拉坐起来给他穿衣服了…”
就在队长用力把死人拉起的瞬间,死人胸腹中的余气呼出,发出“呕”的一声。
“唉呦,我的妈呀”小朱撒腿就往外跑,我和大姚也不知不觉跟着跑出去。
队长也懵了,大声叫到:“回来,回来。”
我们回到屋内,队长已下床,再不教一个人给死人换衣服的方法,而是说:“来,一起换!”
我们仨赶忙就上前和队长一起给死人换衣服。大姚倒了盆热水沾湿毛巾,正准备给死人净面,队长制止道:“让小孙来!”
我接过有些烫手的毛巾,刚往死人脸上一敷,吓的手就哆嗦起来,脑子一片空白,再不知如何做。
还是大姚好,她看我已吓傻,就一把抢过我手上的毛巾:“队长,还是我来!”
队长也看出我是真害怕,就安慰我说:“别怕,多接触几次就不怕啦,当初大姚和小朱比你还胆小。”
死后料理结束,队长把门关好。挂上门挂。
在回驻地的路上,大姚还悄悄告诉我,小朱第一次做病人死后护理时,都吓的尿裤子啦。
回到宿舍,同室的战友都进入梦乡,可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刚进入朦胧,就又被吓醒。
队长知道我胆小后,就亲自带着我,经常把危重病人的护理工作交给我做,并亲自带着我做死后护理,换衣净面净身。慢慢我就胆大起来,很快我就学会了一个人给过世病人换衣服的操作技术。
一九五二年,我又在济南军区军医学校学习,没毕业就接到命令,抽调五十名学员,补充军队,参加抗美援朝,我们都纷纷写了决心书,我光荣入选,补充到二十三军,赴朝参战。
在老秃山战斗中,我学到的医疗技术派上了用场,亲自抢救伤员,止血包扎,背送伤员,在坑道内为伤员缝合伤口,夹板固定,连续战斗两天两夜没合眼,排长看我累的实在不行就说:“你先去歇一会,有事我叫你。”
因为我们是在坑道内,照明不好,我便随便找了个洞钻了进去,我用手一摸,有人已睡在里面,我就扒了个空躺下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当太阳照进坑道内,我听见排长在大声呼叫我,我急忙起身钻出洞。
“呦,你怎么在太平间睡啦,我说怎么找不着你!”排长看到我惊讶的问。
“哎!大概是累傻了吧!”尽管我伴着烈士的遗体睡觉,可心里一点也不怕。战斗结束后,我受到嘉奖。
经过战火的锻炼,我更加成熟,也更深深的认识到医疗技术知识的重要,所以在战斗的空隙,又把军医学校没学完了课程,自学完,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军医请教。又参加了一次后勤部组织的《医干轮训班》的学习,使我的医疗技术提高很快。
因我热爱文艺,我还在战地报上发表了一篇《战地红花献英雄》的散文,并和文化教员一起编了个数来宝,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参加了志愿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文艺汇演荣获三等奖。
一九五六年回国,到地方医院工作后,组织又照顾老同志,让我参加了干部文化补习班,并保送山东医学院业余大学学习,提高了我的医学技术水平,并发表了三篇医学论文。
因为我爱好文学,一九六三年为参加济南市职工文艺汇演,根据医院先进人物的事迹,结合朝鲜战场,失明战友的情节,编写了个小话剧《医生的职责》被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同志看好,在省市委宣传部长领导下,派专业话剧专家,兰澄和翟剑萍同志参与指导,改写成大型话剧:《医生的职责》,一九六三年携剧本赴上海参加了由洪森副部长主持召开的华东地区话剧创作会议,该剧并在北京上海演出受到好评。为此一九六五年,我赴京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荣幸的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因受鼓舞,我又相继发表了《做无谓的人》《处方》《复诊》《新居》《秋菊》《疚》《夜出诊》等多篇小说诗歌。医生职责剧本,还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所以,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
一九九五年五月离休在家,闲暇之际,回味我大半生走过的路,感慨万千,是啊!没有党,没有国家,就没有我的成长,就没有我幸福的今天,伴着快乐的晚年生活我由衷地发出感慨:感谢党!感谢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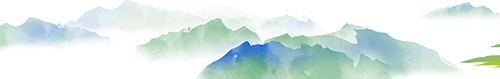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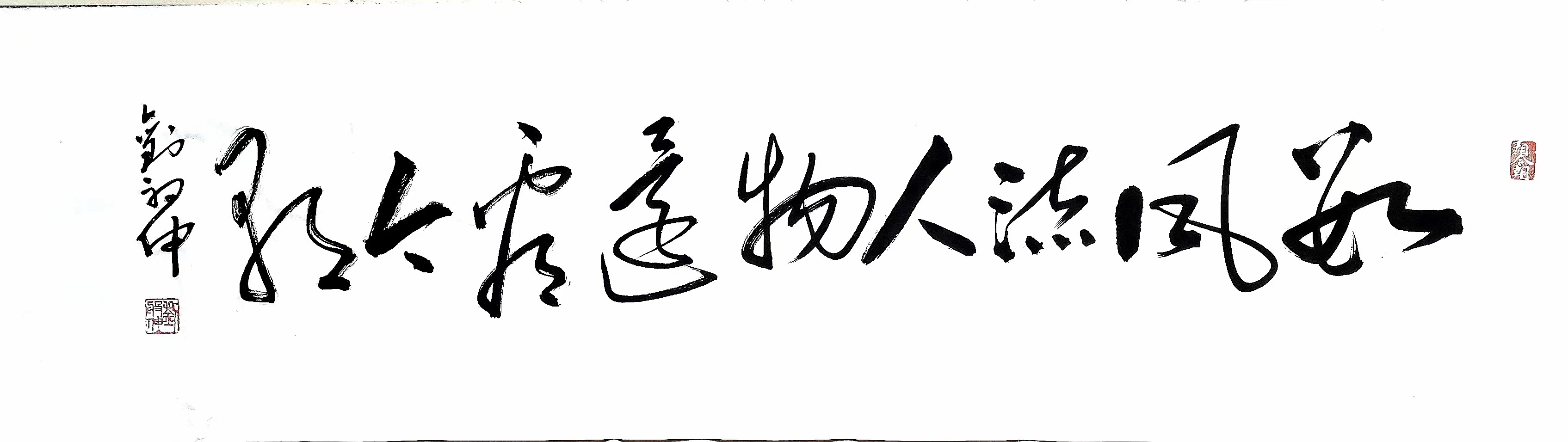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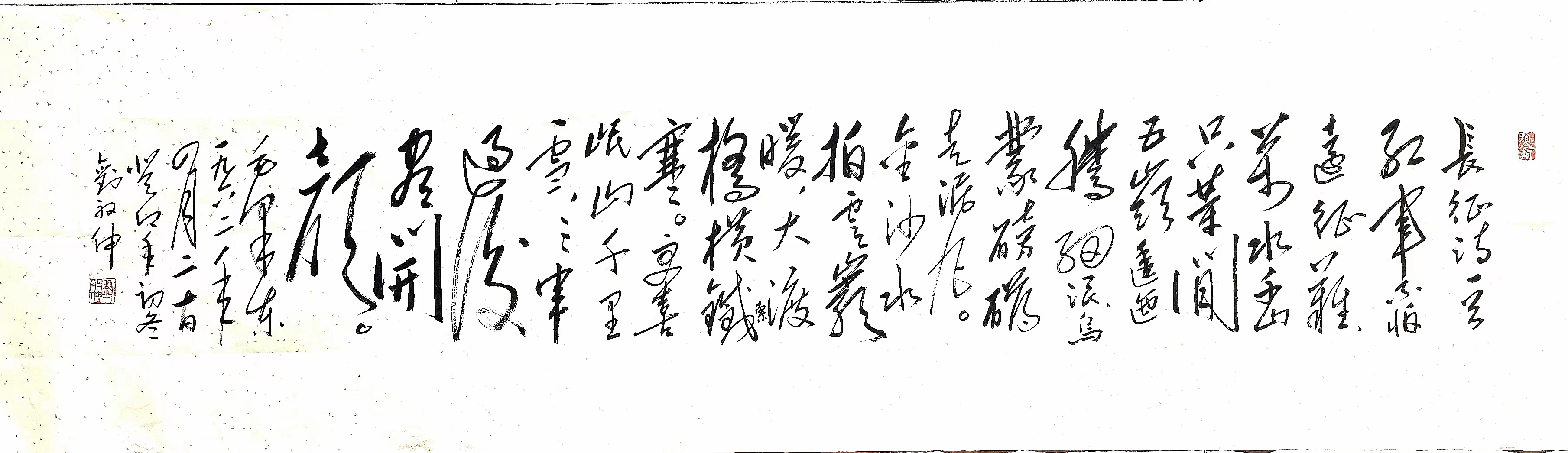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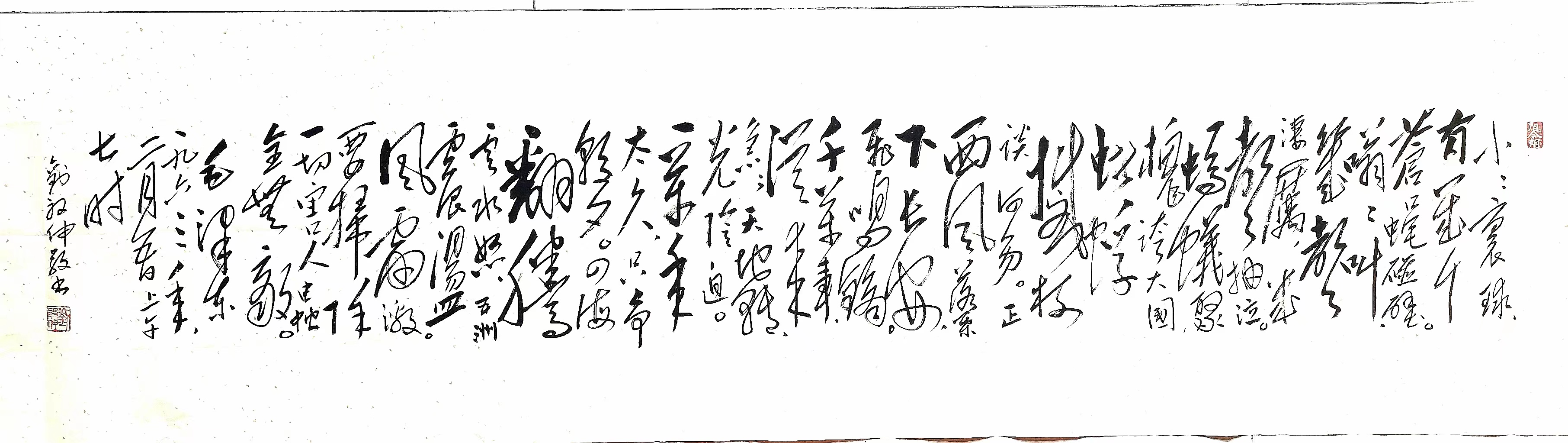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