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足迹(7)——十年风波
邵禄昌
(1)四清运动。1966年夏天,我回到村里时,四清工作组的人员已经撤离了。是四清工作组把我弄回来的,可是我连工作组的人都没见过。其实,他们让我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政治上封杀我,唯恐我在外面干出了成就,来揭发他们的邪恶勾当。
回来后,母亲和我说了父亲在四清运动中挨整的事情。工作组是1965年秋后进村的,成员有七八个人,工作组的主要领导是岭子公社的李社长。现在看来,李社长就是一个整人魔王,他们来就是要打倒一切,把大队小队10多名干部作为斗争对象,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罪行”。最终通过造假账、假证人,说我父亲“贪污”了一千多元,没有的事,父亲能承认吗?父亲认为“干屎抹不到人身上”,不论工作组采取什么卑鄙手段,父亲就是不承认。没想到工作组在进村不到半年取得了“全面胜利”后对我父亲下了毒手(从大队书记、大队会计、大队外出的磨商、大队供销社代销员、小队长、小队会计10多人,都是“贪污犯”,都是“四不清”干部。最后经工作组研究,对于那些“贪污”一二百元的,或减或免,就算过关了)。
最后,他们把父亲叫到大队部关起来,对我父亲说:“你什么时候承认,就什么时候放你回家。”让母亲一日三餐给父亲送饭。为了从精神上彻底整垮我父亲,工作组人员实行了“车轮战”,他们三班倒轮流审讯我父亲。白天不让休息,夜里不让睡觉,连续七天七宿了,都快腊月三十了还不让回家过年。娘去送饭,看到父亲被他们折磨的没人样了,娘心疼了,对父亲说,咱认了吧,要不他们会把你整死的,只要人活着就行啊,钱没了咱再挣,你死了我和孩子咋办?在娘的劝说下,父亲只好承认了,他们这才把父亲放回家。回家后,按照工作组的要求,承认了就得“退赔”,当时叫父亲退赔一千多元。
此事让乡亲们知道后,左邻右舍都来给父亲送钱,其中有东邻的王焕章大哥,西邻的刘安申大哥。还有中央村的我干大爷,栗家庄大姑家表哥,西铺村的二舅,长申地的小姨夫,王洞村三姑家的大表哥,都来给我家送钱。另外,父亲还把我结婚时的方桌、大椅和缝纫机也都折钱交给了工作组。当父亲把1200元钱交上后,工作组一算还超了,又找回来180元,最终结论是我父亲“贪污”1020元,这在整个淄川区也是数一数二的,父亲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千字号”。大年三十晚上,父亲召开了家庭会(只有我不在家),告诉母亲和孩子们,春节后可能去坐牢,要做好思想准备。
其实,当时工作组的目的,是想要我家新盖的大西屋。但是我父亲宁愿借钱也不给他们大西屋。他们的伎俩在我父亲那里没有实现,只好无奈的说:“还是邵永才有钱。”因为在我父亲之前,磨商毕佺承、毕俱承兄弟俩不仅赔上了大西屋和全套院落,还赔上了一个几亩地的大园子(俗称南店),张国岭赔上了东屋和东园子,其他干部都是砸锅卖铁、东借西拉交了现钱。
我父亲挨整的原因,就因他是在任的大队长。为了让社员们多分两个钱,让社员们生活好一些,在生产上大搞副业,到山上开石窝打磨。石磨生产多了销不出去,就安排毕佺承、毕俱承和张国岭出去卖磨,支持他们把送出去的磨坯子,就地加工为成品磨,这样就能多卖钱,大队按销售金额给他们一点提成,这本来是好事,却被工作组认为是“多吃多占”,各“退赔”800元,父亲和他们是“同流合污”。等父亲交上钱之后,腊月三十下午,全村分四清“胜利果实”,每个社员分得两块钱。有的社员说,“才分了两块钱,多分两个还不行啊”。可说这话的人没想想,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是工作组逼着人家“买人”的钱。
由于我父亲的“问题”,不仅把我从萌山水库要回来,后来还牵扯到我的兄弟们。大哥是淄川农机修造厂创业者(亦工亦农)和车间主任,村里坚决把他要回来,让生产队里扣发他的口粮,厂里三番五次来协商不成,最终只得回家。三弟在七三二厂当工人,村里也想把他弄回来,可七三二厂是国营的军工厂,厂里就是不放人,村里才死了心。四弟和五弟都是淄博八中的优秀生,毕业后不能推荐上高中,只得回家务农。
现在想起来,真是又可恨、又可笑。当时的工作组,就像个土皇帝可真了不得,可不到一年的工夫就走了。让我实事求是的给来我村的工作组来个公正的简短的评价:从工作组进村,就搜集黑材料,对大小队干部是小会批、大会斗,挑动群众斗干部,采用逼供信的手段,无情打击队干部,它的伟大“成果”就是年终每个社员分两块钱。
(2)当饲养员。从萌山水库回来,正好我们队的北饲养处缺个饲养员,队长安排我去干饲养员,当时的老饲养员是毕德山。饲养员的任务,喂好猪牛,垫好栏多攒粪。俗话说:“喂猪攒粪,得利是必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 这说明了粪肥对农业的重要性,垫栏、攒粪也有技巧,不光攒得多还得质量好(又黑又臭,越臭了越好)。再说喂猪,那时喂猪不是现在,猪有定量,每头猪每顿需用多少饲料(主要是地瓜干子面)都有数,称好面子,打熟猪食再掺上粗饲料(豆叶、地瓜秧打成细面,放在池里泡发了)开始喂,每头猪喂多少,得有数。喂牛要先把玉米秸铡细,铡草还有个歇后语叫“书记铡草,决定(蹶腚)一切”,说明了铡草的姿势,就是一人坐在铡墩一头,另一人撑住铡刀把,坐铡墩的人把草续好,撑铡刀的人用力摁铡刀,就把玉米秸铡断,可不能铡粗了。把铡细的饲草放到牛槽里,牛就开吃了。随吃随添,未了的草渣子,再加豆饼拌上饲料,牛继续吃。春秋两季用牛耕地时要多加料,一定要喂饱。冬天,牛吃饱后,还把牛牵出来晒太阳,只能喂好不能喂瘦,喂瘦了多丢人。
(3)“运动”十年。1966年6月,“那场运动”开始了,村里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不仅批斗四类分子,也批斗我父亲。按理说父亲经过了四清这一关,应该是没问题了,可不是那样,不仅“四不清”的帽子永远戴着,还被污蔑为“历史反革命”。父亲白天和社员们同样干活,晚上社员们都休息了,父亲还和四类分子一样去扫大街。看到父亲年纪大了还受这些洋罪,我在暗地里掉泪。那时的口号是:革命红旗迎风摆,牛鬼蛇神脚下踩,脚下踩;行动是: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每次批斗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都少不了父亲。在批判父亲的大会上,还要父亲“坐飞机”(低头弯腰。两只胳膊向后翘起来)。1968年在王村批判淄博市委书记刘千,父亲也是同台受批判。父亲是农业劳动模范,去市里开会时认得刘干书记,没想到两位老朋友在这样的场合相遇。
当时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成为造反派,真理战斗队、烈火战斗队…… 可哪一派也不要我,说我是“四不清”子女。不管他们要不要,我都是积极劳动,努力工作。可有人又说:“你还想当书记不成?”那10年,可受了些委屈,现在看来,什么派都没参加还对了呢。
1967年春的一天下午,二队的生产队长毕坤德来饲养处找我,谈论当时的形势,我们俩谈得认真、活泼、从容。后来坤德老弟为此事还给我写了首诗:青年才俊气魄宏,岂料前程山万重。四清“文/革”交厄运,牛棚论势语从容。古贤八旬还登第,邵公大器重晚成。祝愿我兄松乔寿,子孙绕膝乐无穷。1984年队改村时,毕坤德当选为首届村主任,后来他任村党支部书记时,我连任三届村主任,我俩搭档多年,共同为大史村的发展而努力。
运动结束后,政府为我父亲平反昭雪,四清工作组和造反派给我父亲整的那些黑材料全部被销毁。1978年父亲再次当选为生产队长,卸任后调任王村公社水利专业队任施工员。
这还真正应了父亲说的那句话:干屎抹不到人身上。再看看那些靠运动发家的“运动红”都没有好的归宿。
(谢谢大家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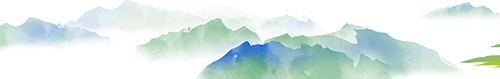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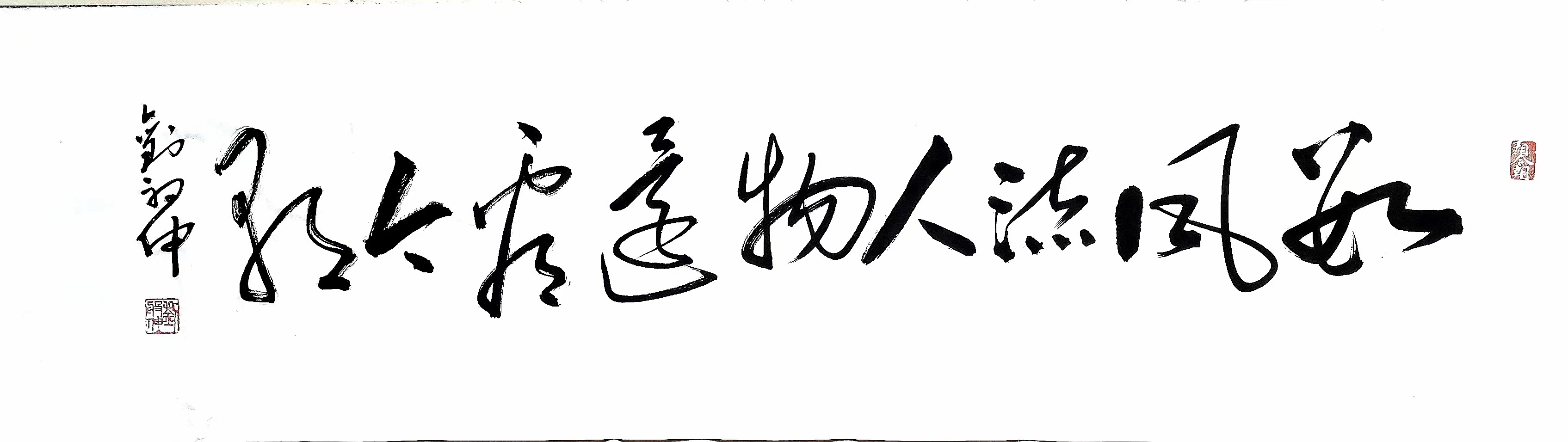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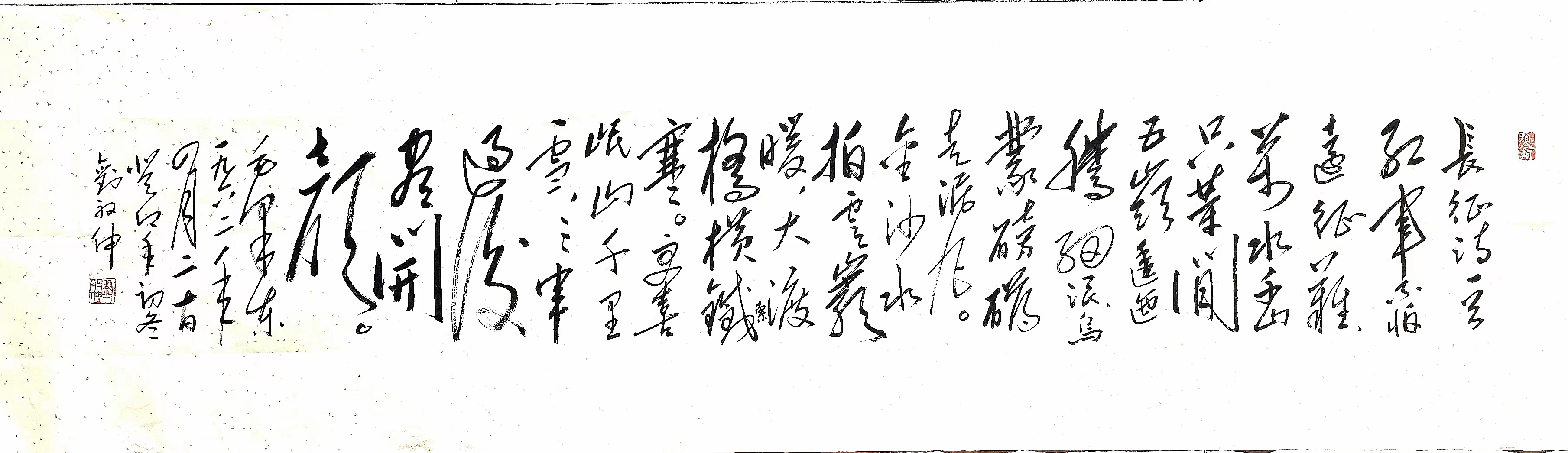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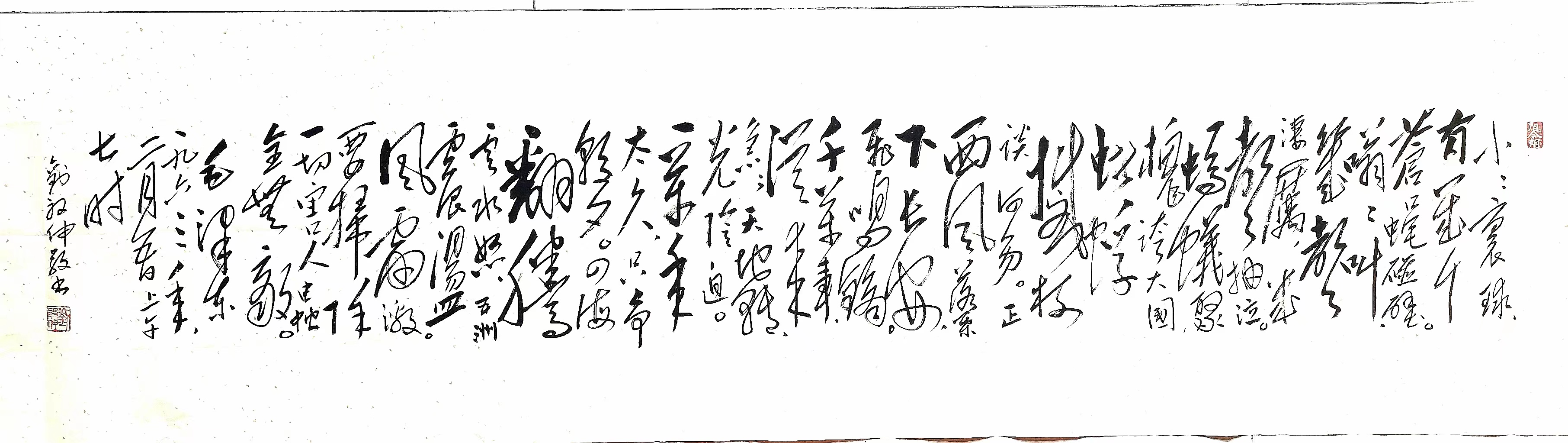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