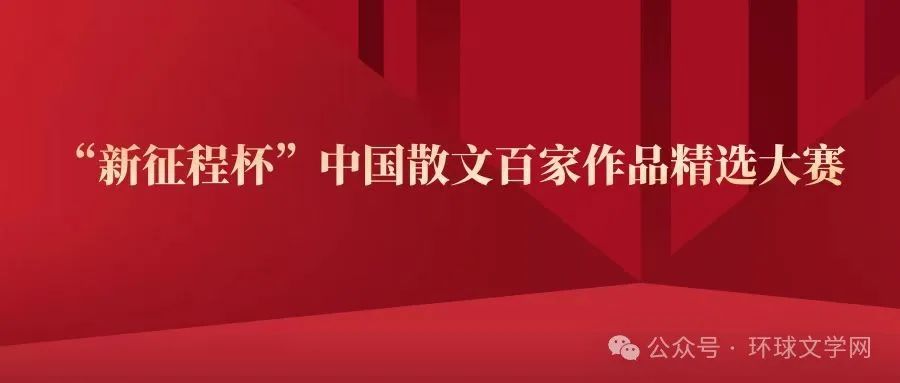
一条大河忆乡愁
作者:凌震三
记得我十岁左右那年初夏,大哥从外地途经盐城,要带我到乡下姨娘家去。姨娘家在离盐城七、八十里外的花川港。花川港也是我的故乡,是我出生的地方。六十年前的花川港,还是很偏远闭塞的。从盐城到花川港,轮船几乎就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了。
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大哥带着我,从老盐城西门的轮船码头上船。
随着一声汽笛声,船离开码头,慢慢地开出了我熟悉的城市,儿时每天见到的小街不见了,渐渐地映入眼帘的是另一番景象:头顶上是一大片湛蓝的天空,白色的云朵,就象一片片轻薄透明的棉絮,悠闲自得地飘来飘去。河两岸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田野和隐隐约约的树林,近处,大片大片金黄色的油莱花,在阳光下照耀下显得特别的亮丽。远处,一个巨大的白色圆形的风车,在蓝天白云和绿色田野之间悠悠地转动着……真的好美啊。
轮船在轰隆轰隆的马达声中继续向前开去,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河面渐渐地窄了起来,我发现我们的轮船绕过了一个小小的滩岛。那个小滩岛面积不大,上面没有房子没有人,除了稀疏地长着几棵树木和一些杂草外,就是一堆黄巴巴的土疙瘩。我很诧异,船走到这儿,怎么出现这么一个孤零零的荒漠的小滩岛呢?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孤寂荒凉的地方叫大洋湾。再后来,连我自己做梦也想不到,这大洋湾今天已成了我们大盐城的一张城市名片,成了一个被誉为“世外桃源”的风景优美的4A旅游景区。近几年来,我常常来到大洋湾风景区。寒冬过去,春风吹来,大洋湾那满眼的粉红色的樱花,以及从花瓣上飘来的阵阵馨香,将大洋湾变成了一个梦幻般的乐园。深秋时节,蓝天白云,碧波荡漾,那错落在绿树红花丛中的仿明清风格的亭台楼阁,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曲水长廓,真的犹如人间仙境。尤其是夜晚,璀璨的灯光,迷人的色彩……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怎么也无法将它与当年的那个只见树木不见人的弹丸之地联系在一起。
大约下午四点半钟左右,轮船终于到我们的目的地一一花川港了。船停靠后,我们上岸来,岸上除了我们几位乘客,什么也没有。大哥告诉我,这是河的北岸,我们要去的地
方在南岸。大哥说,不着急,等会儿有个渡船来接我们过河。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一条小舢舨来到我们面前。撑船的是位老大爷。他与我大哥很熟悉,亲切地说了一句:“回来啦?”接着指着我说,这就是你盐城的弟弟吗?大哥说,是的。老大爷好奇地望望我,我也好奇地看看他。老大爷庾瘦的脸,高高的身材,可能是因为长年累月在河上撑船,风吹太阳晒的缘故,皮肤是黑黑的古铜色,瘦长的脸上,布满了刀刻一样的皱纹。
小舢舨不大,一船装十来个人。上船后,老大爷用竹篙对着河岸一点,小舢舨就离开河岸了。他又接连撑了几下,小舢舨慢慢地驶向河心。这时大爷放下竹篙,开始摇起橹来。
摇着摇着,我看到汗珠从大爷那古铜色的脸上流了下来,耳边也听到了大爷轻微的喘气声,搖着摇着,这喘气声也越来越大,时不时地还听到他吃力地哼了几下。船靠岸了,大爷又特地过来搀扶着我,将我送上岸。路上,大哥告诉我,这大爷姓陈,他儿子是姨父的学生,正在跟姨父学医呢。
后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坐轮船到姨父家来一两次,也就说,每年都有机会坐陈大爷的舢舨渡船过河了。夏天还好说,最艰辛的要算冬天了。数九隆冬,天寒地冻,陈大爷双手将冰冷的竹篙从水里拔出来,又撑下去,我抬头看着他那张古铜色的脸,看着他吃力摇橹的样子,嘴里呼出一阵阵的热气,鼻子下面流淌着粘粘的半透明的鼻涕,粘在胡鬚上,冬日的阳光一照,泛着青冷的光,叫人一看就觉得浑身寒丝丝的。
难怪人们说,世上最苦的三件事,撑船打铁磨豆腐……看到陈大爷艰辛摆渡的身影,我不止一次地问大哥,陈大爷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干这么苦的差事呢?
大哥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淡淡地回答我说,没办法,家里穷,生活困难啊......
几十年过去了,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出生于我们花川港的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医学院副院长陈义汉,当选为中科学院院士了。随即,我又在百度上搜了一下他的简历,才知道,陈义汉先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人类心房颤动致病基因,鉴定出人类心房颤动的部分遗传学和电生理学机制,成果发表于《科学》杂志。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为中国
在国际心律失常研究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
啊!花川这块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竟然能走出样一位令人敬佩自豪的科学家,一位在盐城地区也屈指可数的中科院院士,实在了不起!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位中科院院士原来竟是我姨父学生的儿子,这位撑船摆渡的陈大爷的孙子。我脑海里又浮现出童年时代的那条大河,浮现出凛冽的寒风中,陈大爷从冰冷的河水中拔出竹篙的情景,又看到了冬日的寒风中的那张古铜色的脸上刀刻一般的皱纹......
一条大河,载着我童年的记忆,系着我挥之不去的乡愁。
作者简介:
凌震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盐城电视台主任编辑。出版散文集《永远的魅力》(中国文联出版社),《此生最爱是梅花》(作家出版社)。另有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羊城晚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