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斌推荐语:25年前,我亦师亦友的北大荒作家杨孟勇,创造了57岁做心脏移植的世界奇迹,并接续创造了心脏移植不久后停止服药、健康地存活了25年的人间神话。杨孟勇用一颗不正常的心脏,把生命的不可能活成了可能!他的神奇故事,曾经由中央电视台等几十家电视台制作专题广为传播。长篇纪实散文《活下来再说》,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推荐连载此书,意在引起读者对生命的尊重和感动,同时感受这个社会的优越和温暖。尤其要向给予杨孟勇二次生命的哈医大二院、及其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活下来再说
著/杨孟勇

26、生命祭日
出院之后,从妹妹玉玲那儿得知一个消息:三叔病重期间,做心动彩超,检查结果竟然与我一模一样,也是心肌扩张。只是没有我这样严重。也没有机会做我这样的换心手术。
我没有死去。与我同样患上心脏病的三叔,却于5年前去世。
枪林弹雨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心肌扩张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4月5日,农历三月十二,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早早地吃了饭,与妻一起乘车来到郊区的香坊农场养母家。弟弟妹妹们都已到齐,早就约定好了的,今天一起去向阳山革命烈士公墓。三叔的骨灰就存放在那里。
天气十分晴朗,弟弟租来一辆面包车,一家人直奔向阳山扫墓。在我的记忆中,扫墓是含了特定意义的。家乡的村头上,埋了几个当年抗美援朝牺牲的人。每当清明来临,坟茔地开放了金灿灿的迎春花时,学校里就要组织一次扫墓。拔草,填土,向死者致礼等等,还自编了一首哀歌在坟茔地里唱。
三叔的墓,值得一扫的。他18岁在胶东参加了区中队打鬼子。没有枪,只发两颗土地雷背在肩上,听说鬼子出动,便在必经的路上挖坑埋雷。看了《地雷战》的电影,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说,那是邻县的民兵干的,人家干得漂亮,从烟台出来一小队日军,被地雷炸得寸步难行,一整天的工夫,只走出6里地。
后来三叔被秘密派往东北,加入了第四野战军。那一批共有上百人,从胶东半岛坐上小木船走了一夜,天亮后到了一处海岸,又遭到炮火袭击,差一点出师未捷身先死。
三叔可算福大命大之人,在他离开区中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区中队在距离烟台几十里的地方遭遇几倍的敌军包围,四十几个人只活下来一个,差一点全军覆没。这消息是几十年之后才得知的。那是一次农垦局的工作会议上,有个陌生人急急找到三叔,问他是不是胶东人,问他是不是参加过区中队。三叔一一回答了之后,被对方一下子抱得紧紧的。原来他也是从区中队到东北战场的,只是比三叔早几个月。区中队几乎全部战死的消息就是他告诉的。从此两人只要凑到一起,话题总离不开当年的故事。有时想起来,他会跟我说:“我就是不该死呀!”
逃过一劫,伤残是免不掉的。在东北战场上,先后三次挂花。可幸的是,三次都未能奈何于他。普兰店那次,一颗炮弹在身边炸倒了5个,他是其中之一。当场死掉两个,三个炸成重伤,而敌兵正排着队从不远的距离朝他们走来,甚至听得到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他的腿被炸断,双臂倒是好好的,于是摸到了枪,顶上子弹,准备与敌同归于尽。那次侥幸得很,敌军的队伍从十几米外走了过去,没发现他们。
三叔成了残废军人,1950年转业到了黑龙江边的一片荒原开辟农场。那一年,正是我生父病逝的那年,母亲改嫁,我只得与祖父母相依为命。1954年春,从军的三叔第一次回乡探亲。假期到了,临走时祖母把我拉到他身旁,跟三叔说:“你把孩子领走吧,你二哥死了,你把他领走就是你的儿郎。”
三叔想也没想就说:“那我就把孩子领走。”
从那天起,三叔就成为我的养父。
其实,那年三叔还没结婚成家,我俩就住在办公室里的双人床上,吃饭在隔壁的大伙房。叔侄俩就这样开始了荒原生涯。
寒冷的冬夜,三叔会紧紧搂住我,用他的体温暖和我瑟瑟发抖的身子。
有时三叔会让我摸遍他身上的伤痕,他会十分耐心地告诉我,身上的许多部位还有炮弹皮没取出来。他说颈后那一块,虽然小如米粒,但是太深,下刀是有危险的。
三叔还告诉我,医院里的一个日本医生,怎样企图锯掉他的伤腿,怎样被他用一根拐杖打得人仰马翻,眼镜也破了,碎了一地。
当然后来受了处分,但那很值得。一条腿保住了。起码不用终生拄拐走路。
出奇的是,三叔回乡领我那年,村里人还能看出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身后常会招引来一帮淘气的孩子,一边哄笑,一边学着瘸腿走路的架式。后来竟神奇的康复了。“文革"时被造反派押到场院扛麻袋,他那伤残的一条腿竟然硬顶了下来,像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口气装满一个大解放车厢。
“文革”中,三叔被打倒了,被专政了,关进一所空房子好几个月。那时我已成家,自己单独出去过日子。期间好几次想去探望,但一想到要经过造反派们几道检查,那些检查的人很凶,即使通过了检查,也可以随便找个理由不允许你进去见面。我知道此时的三叔一定十分盼望我去看他,哪怕仅仅一次也好,但我一次都没去。说穿了,没敢去。三叔抽烟,连一包烟也没给他捎去。为此我像一个罪犯似的,深深地自责了许多年。我责备自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忘了三叔的养育之恩。
我坐在弟弟租来的面包车里,心中依然在谴责自己。
“文革”后,重新给三叔安排了工作,由边疆地区来到哈尔滨郊区。但身体状况日渐不好,最终患上重疾几次住院抢救。
有一天,突然接到妹妹玉玲的电话,说三叔病重,病中几次都说很想我。我心里咯噔一下,请了假往哈尔滨赶。到了医院,看到命大的三叔又一次从危险中挣脱出来,甚至能坐在床上,面容憔悴,极度虚弱,两只眼睛却出奇的明亮。三叔本来就有一双漂亮的大眼,此时竞像少女般那样流光溢彩。出出进进的护士们十分惊讶,都说,这老爷子的一双眼,从来没见过!
我在病房里陪了他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就说:“你回去吧,别再来了。”
我知道这是三叔最后说给我的话了,也是最后的见面。
果然,我回到佳木斯不儿天,妹妹来电话说,三叔与世长辞了。
听弟弟说:“三叔在弥留之际,家里人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三叔断断续续地说:“想在死后的身体上盖一面党旗。”弟弟把这一要求转告了农场,农场请示了上级组织部门。回答是可以的。于是,三叔心满意足地走了。
扫墓之前,我正在为出版诗集一事奔忙,心想把书印出来,一定再来公墓,献给我三叔一本,就放在盛装他骨灰的盒子下面,永远陪伴他老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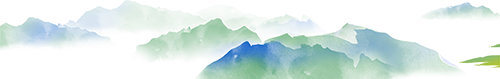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