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萧”之误何时休?
李 皓

近期,湖北某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吴伯箫散文选》,有别于此前几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同名书籍,该出版社在编辑此书时,特地邀请吴伯箫研究专家、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的子张教授,对入选的每一篇散文都进行了点评。这是一个好的创举,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吴老的名篇佳作。可美中不足的是,封面设计上一同出现的一大一小两个吴老的名字却“各有特色”,大字写作正确的“吴伯箫”,小字则写成了错误的“吴伯萧”。书在印厂已印装完毕,正在网上做推介宣传时,被细心的读者发现。反馈给责任编辑后,无奈,出版社只好通知印厂做更换封面处理。
吴伯箫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和教育家,其散文名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猎户》《难老泉》《灯笼》等,被收入新中国各个时期的中小学《语文》课本,熏陶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按说出版过程中是不该闹出这样的“乌龙事件”的,可它还是令人意外地出现了。警钟响起,亡羊补牢,它提醒有关方面,书刊出版,校对工作不是小事,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才行!
实际上,在不同时期的吴伯箫文集出版过程中,将“箫”字错写成“萧”字,湖北这家出版社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而是第N次了。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身居上海的王统照先生,在将吴伯箫离开莱阳乡师辗转奔赴延安之前,托付给他的《羽书》剪贴稿本,安排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即将“箫”字印作了“萧”字;1954年7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吴老的《出发集》时,封面署名也印作“吴伯萧”。或许是当年上海有关出版方的这两次没有征求过作者意见的“统一”,给早期的全国广大读者留下了刻骨印象,“吴伯箫”本就是“吴伯萧”。
后来,吴老又先后结集出版了《黑红点》《潞安风物》《窑洞风景》《烟尘集》《北极星》等多种散文集,封面署名均印作“吴伯箫”,被选进各个时期中小学《语文》课本的吴老文章的署名也是“吴伯箫”。“伯箫者,大箫也!”其中之意,学子们都懂得。


可不知怎的,到2009年6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第三次出版《吴伯箫散文选集》时,在前两次“箫”字(印刷体)均用字正确的基础上,新版封面上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手写体的“吴伯萧”。出现如此低级错误,百花文艺出版社不仅没有向作者和广大读者致歉,相反,还在吴老逝世后才推向社会的吴老最后一本散文集《忘年》的封面上,继续重复了这一错误。实在是既荒唐又可笑。
错误的署名,出现在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的封面上,似乎可以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可具体到同一张封面上同时出现一大一小、一对一错两种署名,就完全不应该了。这种出版流程和审核上的漏洞,实在是太大意了,必须坚决堵塞!值得庆幸的是,湖北这家出版社的这次漏洞,在产品流向社会之前被及时发现侥幸地堵上了!
汉字是博大精深的表意文字,每一个字都承载着独特的意义与文化内涵。取名时的不同用字,自然有着不同的意义。吴伯箫先生以“箫”这种古老的乐器为名,其中蕴含着对优雅艺术与文化的追求;而“萧”字,虽读音相同,却在表意上大相径庭。将二者混淆,不仅是对作者名字的不尊重,更是对文化严谨性的亵渎。

曾几何时,由于国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一些大众场合的大众书写中,人名书写被看成一件“只要发音基本正确就无大碍”之事,尤其是对那些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的普通人来说,更是如此。但随着国人文化水平的日益提升和网络时代人名管理的日益严格,人名的书写多一笔或少一笔都是不被允许的,更何况将人名用字写作含义相反的其它字了。
好面子乃国人的传统,自古以来,对于长辈、贵人、高人以及社会名流,国人轻易不言其错,以致出现了把此类人写错写别的字称作“通假字”,以及“书法无对错”之类的“遮丑之辞”。因了几家出版社的屡将“箫”字印作“萧”字,国人(尤其是像《闪闪的红星》作者李心田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者)也不乏将“吴伯箫”写作“吴伯萧”者。更甚者,这种错误还熏染到了当今正站在三尺讲台上传授知识的新时代的语文教师们,课堂讲述过程中,课件表达上,误将“箫”字写作“萧”字,或者“箫”“萧”混用者,也不在少数。此种现象的不断出现,让热心吴伯箫研究人士哭笑不得。无奈之下,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伯箫研究专家子张先生,只好在有关文章中,将误写的“吴伯萧”称作是“吴伯箫”的又一个“笔名”了。
书籍出版无小事。前车之鉴,必须记取。笔者衷心希望,在今后的出版流程把关上,我们的出版行业,能够认真认真再认真、严格严格再严格,决不让此类低级错误再度出现!
(作者李皓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副会长,高级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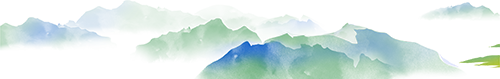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