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燕记人系列散文之二
南山有光
——记“雷锋姑姑”
文/邱燕
失落的信号:一个谜的开端
2023年5月30日,一个寻常的日期,却成了“雷锋姑姑”在数字世界留下的最后刻痕。朋友圈凝固在那一刻,信息石沉大海,电话那头只剩下冰冷的忙音。人间蒸发?不,更像一颗炽热的星辰,骤然隐入深邃的夜空。她去了哪里?是遭遇了不测?是奔赴一场不为人知的约会?还是被虔诚的信众,当作行走人间的菩萨悄然供养?牵挂,像南山上蔓延的薄雾,萦绕心头,挥之不去。那个用光和热温暖了无数生命的人,如今安在?
微雨初逢:琉璃檐下的暖流
2019年中秋,微雨如织,济南南山仲宫。佛缘居古朴的琉璃檐下,水珠串成珠帘。就在这氤氲水汽中,我初次见到了传说中的“雷锋姑姑”——那位全国道德模范。
她像一幅鲜活的版画跃入眼帘:健康麦色的脸庞刻着风霜的印记,一身洗得发白的夏季绿军装,旧军帽檐下目光如炬。最夺目的,是那条披在肩头、在微凉雨丝中猎猎舞动的鲜红围巾,像一团不灭的火焰,燃烧在灰蒙蒙的雨幕里。她手持话筒,笑容在细雨中绽放,声音清亮:“雷锋姑姑开始理发了,有需要的老人请过来理发。”
路过的老人无需言语,默契地坐下。姑姑操起推剪,动作麻利得如同削土豆皮,指掌翻飞间,银白的发丝簌簌落下。 哪位老人爱平头,哪位需要留鬓角,她心中自有一本账。三下五除二,一个原本略显颓唐的老人便焕发出矍铄神采。她身旁,几位年轻义工也默契配合:剪、推、扫、刮,轻声细语地询问:“长点还是短点?”“鬓角还留吗?”末了,总不忘一句朴实的赞美:“更精神了!”“是个帅老头儿!”没有煽情,只有家人般的熟稔与熨帖,在冰凉的雨丝里蒸腾起暖意。
屋檐深处,二十多位“红马甲”像跳动的火苗,正为络绎不绝的老人分发粥食和月饼。人群里有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有沉稳的青壮年,有带着孩子的母亲,甚至是一家三口。粥香饼甜混合着雨水的清新,飘散在空气里。他们脸上洋溢着纯粹的、近乎透明的快乐,一边分发,一边解释:“这是咱们定做的,糖少、真材实料!”“定了一万份,要送给一万位老人……”“对不起,只发给老人,家里有老人的可以代领……”中秋的温情与无私的善意,在此处无声地流淌、弥漫,汇成一片温柔的海洋。
人心悦义理。我正沉浸在这份难得的清流中,忽被一声惊喜的呼唤惊醒:“邱老师,你也来了!”一位熟悉的“红马甲”兴奋地走来,随即呼唤她的女儿:“斌晖!邱老师来了!”正低头忙碌的少女斌晖闻声抬头,脸上瞬间绽放出惊喜又羞涩的笑容,眼睛亮晶晶地喊了声“老师”,便轻盈地穿过人群来到我面前。紧接着,小帅哥王铭硕和他的父母也围拢过来,“邱老师,真是缘分!”铭硕妈妈笑道,“人以群分,竟在这里遇上了。”小铭硕机灵地接话:“妈妈,这,就叫磁场相同!”一时间,我被这团跳动的“红”包裹,仿佛也被那无形的“磁场”温柔地吸纳。
寒暄未落,一曲《爱的奉献》悠然响起,清越的女中音穿透淅沥的雨声,古老的仲宫小镇仿佛被这歌声托起,缓缓沉入一片由粥香、饼甜与无边亲爱酿成的温柔之海。
那双浸透岁月的手:初次相握
雨势渐急,人群微动。“红马甲”们开始利落地将物品向干燥的檐下归拢,我也搭手帮忙。斌晖妈妈引着我走向那个绿军装、红围巾的身影:“这就是我常说起的邱老师。这是雷锋姑姑。”
“姑姑。”我自然地唤道,伸出手去。
盈盈一握间,我触到的是一双“土地”的手——掌心覆盖着厚厚的老茧,皮肤粗糙、硬实、有力,传递着一种奇特的温度,仿佛握住了大地的根脉,浸透了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劳与奉献的印记。它完全不像一位六旬妇人的手,倒更像属于田野,属于岁月,属于无数被它抚慰过的苍老额头。
南山小院:平凡与超凡的栖息地
粥食分发完毕,义工们分得一碗清粥、一个月饼,权作中秋晨餐。红马甲被细心叠好,人群带着满足的笑容散去,回归各自的生活轨道。
姑姑走过来,话语直接而温暖:“我们要回去了,你跟着我去包饺子吧,咱过十五吃饺子。”没有丝毫客套,仿佛我是她熟稔的家人。正中下怀!我心中翻腾着巨大的问号:眼前这位68岁的老太太,如何能挣脱“中年大妈”的刻板桎梏,赢得如此广泛而深沉的爱戴?是怎样的磁石,吸住了那些为生计奔忙的中年人,让他们甘愿追随她栉风沐雨?又是什么力量,让俊朗的大学毕业生,情愿将求职的脚步暂缓,先侍奉这位“姑奶奶”一年?我渴望走进她的内心世界,那片看似平凡却孕育着非凡光亮的土壤。
坐上姑姑那辆饱经风霜的面包车,同行的有河北大学生小卢、一个四年级的阳光少年和司机刘师傅。车子驶入仲宫北村石板街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小院。
院门外,几畦青菜青翠欲滴;过道里,刚脱皮的鲜核桃晾晒在竹匾上,散发着清冽的草木香;院内花池中,花草自在生长,几株月季开得泼辣而热烈,仿佛不知秋凉。四合小院,房舍简朴环绕。姑姑引我参观:西屋是宽敞整洁的大厨房,锅碗瓢盆锃亮,地面光可鉴人;西屋连通北屋,最西侧是设施简单的单间;往东是采光良好的女生宿舍,高低床铺纤尘不染;南屋是男生宿舍;东屋南端是仓库,被褥叠放如豆腐块;北侧则是一间静谧的佛堂,相好庄严的观音端坐莲台,佛前长明灯吐着幽微而恒定的光焰,仿佛这方寸之地的心脏。
姑姑递给小卢20元钱:“5块钱买豆腐,剩下的买几样青菜。”二十块钱?一大家子过中秋?这近乎苛刻的节俭让我心头一震。她平静地解释:今天她的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子都会来小院团聚。然而,她已有二十年未曾归家过年过节,家人早已习惯。七岁的孙子,她一天未曾照料,但提起她,家人言语间唯有骄傲。姑姑的神情也流淌着同样的自豪。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家庭?那位隐在幕后的“姑爸爸”,如何面对这位“有家不回”的妻子?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他们维系着怎样一种超越凡俗的情感纽带?好奇的藤蔓在我心底疯狂滋长。
“捡来的”馈赠与沉甸甸的日记
姑姑端来洗净、水灵灵的茴香苗。刘师傅显然是厨房好手,利落地切馅、烫粉条、炸豆腐,小卢则笃笃地剁着白菜。姑姑又捧出一叠洗烫得翠绿欲滴的卷心菜叶,脸上是孩子般的欢喜:“这是我捡来的菜,你看多好!”
“捡来的菜?” 我一时语塞。说实话,生平还真未曾想过,盘中餐竟有如此“来历”。一丝难以言喻的酸涩掠过心头。
这时,小卢递来他的硬皮日记本。我如获至宝。本子沉甸甸的,翻开来,密密麻麻的字迹扑面而来。第一页便是最朴素的流水账:
“X月X日,晨4时起,捡拾街道垃圾。7时抵张村敬老院,为王大爷理发、洗脚、翻身、换洗床褥。午饭后赶赴李庄,为独居赵大娘劈柴、清扫院落。傍晚接保定电话,有急症老人需照料,连夜乘车前往……”
足迹遍布临沂、费县、北京、天津、合肥、包头、新疆、保定、沧州……哪里有绝望的呼救,电话线便是集结号。 途中遇伤鸟病犬施以援手,亡故则妥为掩埋。乞者予饭,痴者理发更衣,病者守护,甚至看顾疗愈精神困顿者。姑姑的话语,如同铁锤砸在砧板上,铮铮作响:
“没人吃的饭,我吃;没人爱的人,我爱;没人要的人,我要。天下老人皆是我父母,男人是我父亲,女人是我母亲。”
曾有女孩问:“姑奶奶,您穿多大的鞋?”
姑姑答得坦然:“孩子,捡的鞋多大,我的脚就多大。从36到43的鞋,我都穿过!”
原来,近二十载寒暑,她未曾舍得为自己购置一衣一袜一鞋。身上所有,皆来自尘世的遗弃或馈赠——那是她选择的“百衲衣”,一件行走的慈悲袈裟。
歌声、红包与三千元的重量
心中的震撼已如惊涛拍岸。眼前的姑姑,岂止是人?她分明是泥泞路上,负重前行的活菩萨!姑姑拿着放饺子的盖垫出来:“面和好了,咱在大门过道包?”话音未落,手机唱响。
一位广州女子的声音传来,带着浓重的思念:“姑姑,我想您了!”她恳请姑姑为她唱首歌。姑姑欣然应允,对着手机,录下一条60秒的语音。歌声质朴,情意真切。
唱罢,姑姑对我笑笑:“全国各地我有几十个干女儿、干儿子,他们都很疼我。”手机提示音此起彼伏,转账信息接连不断:500、300、50、30、20、10元……数额不等,情意无价。姑姑一一收下,一一道谢,声音温和。她告诉我,就连这辆承载着无数奔波与救助的面包车,是别人给买好送来,这里的一切皆是众人一元一角汇聚的爱所铸成。
我们开始包饺子。我忍不住问:“姑姑,您有退休金吗?退休几年了?”
“有,不多,三千块多点。”她手下不停,话语平静,“每个月我只留100块。剩下的,都用于公益,给那些更需要的人。从没给过家人一分。菜,舍不得买,干粮多是捡着吃,万不得已才买一点。2000年退的,快二十年了,没在家过过一个年!”
“那…您过年去哪里过?”
“在敬老院啊!”她抬起头,眼神笃定,“那些老人,太需要我了!他们就是我的爹娘。”
“咱这个‘雷锋姑姑’团队注册了吗?”
“注册了,是‘民非’(民办非企业单位)。”
提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好人”等耀眼光环,她神色淡然,仿佛在说别人的事:
“别人说我是什么,随他们便,跟我没关系。我从不参加,也不出席。别人说得再好,你没做到,白说!别人说你不好,而你天天在做,没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你看看多少人需要帮助?我一天不干活,一刻不干活,就觉得虚度光阴,浪费生命。”
道场在路上:三条腿的行走与消失的长发
与姑姑的另一次交集,是她邀我去听一位高僧的课。路上,她如数家珍地说起哪个村哪个屯里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明天、后天、大后天该去哪个敬老院。她给我看手机里存着的照片,一张张笑脸在屏幕上闪过。又翻出一个视频:“你看你看!这个一条腿的小伙子,马富强!”
视频里,一个失去一条腿的年轻人,拄着拐杖,却精神抖擞地单腿跳跃着,努力跟上姑姑的步伐。镜头一转,他在家中熟练地操持家务,自力更生。姑姑的声音充满欣慰:“你看!这台阶上的两个人,是我和马富强,三条腿……”
视频中的姑姑,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引人注目。“姑姑,您这头发真好,这个年纪了真让人羡慕!”我不由赞叹。她闻言,突然抬手,一下摘下了那顶旧军帽——露出的,竟是一个近乎男子的、短短的平头!
我愕然:“这么好的头发,为什么剪这么短?”
姑姑的语气平静得像在讲一件寻常小事:
“去年大年三十,我把所有的钱都买了米面粮油,准备去敬老院过年。突然接到信儿,马富强的爷爷去世了,家里实在没办法。我…就把头发卖了,让他拿钱去给他爷爷修坟了。这头,是收辫子的人给铰的。”
车内一时寂静。过了一会儿,和司机、小卢聊起即将拜见的高僧,我心中那个盘旋已久的问题终于脱口而出:
“文殊菩萨在五台山,观音菩萨在普陀山,普贤菩萨在峨眉山,地藏王菩萨在九华山……姑姑,您的道场,在哪里?”
姑姑明显一怔,随即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声在车厢里回荡:
“哈哈,我的道场?在马路上!在敬老院!”
南山长明:那束不灭的光
姑姑,整整两年了,你音讯全无,偶尔听他们道听途说似乎是你身囹圄。笔者都认定是他们嚼舌根子胡说八道: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姑姑过处水流花开,她走遍三川四峪大街小巷连一只狗都不肯吠叫,如此怜老温贫,如此的人畜无害,怎么会!那些散落在乡野村屯、敬老院陋室里的“爹娘”们,该是怎样的翘首以盼,又是怎样的黯然神伤?他们粗糙的手掌需要您去温暖,他们脚该洗了、趾甲该剪了,头发该剪了、衣服该换了、浑浊的眼神需要您去点亮,孤寂的岁月需要您去填满。他们习惯了您带来的那束光,那束驱散阴霾、带来生机的光。您是他们绝望深渊里,那根唯一的、坚韧的藤蔓。
南山有光。
那光,曾是一个身着绿军装、肩披红围巾的身影,在风雨中奔走,在陋室里操劳,在无数孤苦的心灵上刻下温暖的印记。
那光,如今隐于何处?唯愿那光,只是暂歇,终将重新亮起,继续照耀这人世间的沟壑与荒凉。
因为,有太多角落,等待着被这束来自南山的、名叫“雷锋姑姑”的光,温柔地照亮。
(于2025年6月)

【作者简介】邱燕(女),祖籍山东泰安肥城,早年从事教育,热爱文字,笔耕不辍,陆续在各大报刊、各大知名网络平台发表作品数百篇;2018年主编红色经典专著《沂蒙精神·中国梦》;2020年获“中国诗歌春晚十大新锐诗人”称号;2022、2023年入选“山东省文联文艺两新创作骨干”。现居济南,任山东省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文博学院副院长、客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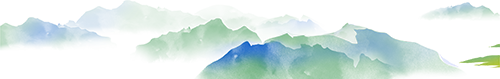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