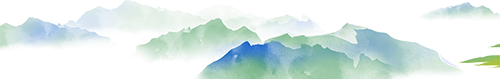新诗话:静安居说诗—高昌

静安居说诗
在诗书山海中
赴一场灵魂之约
新诗话—高昌
01
重回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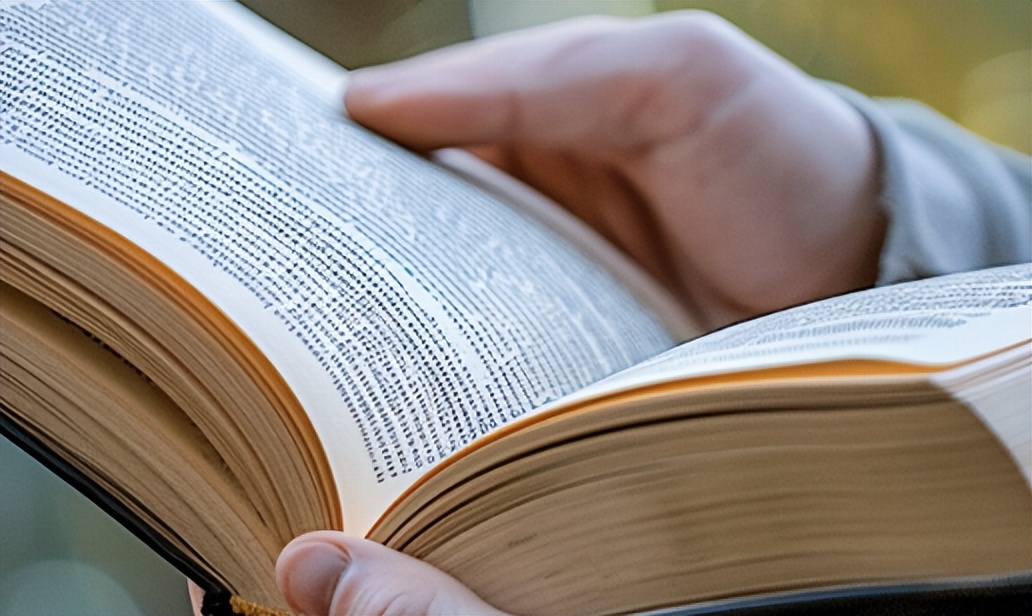
诗词热是传统诗体形式的回归,但并不意味着五四时期已遭痛打的陈腐观念沉渣重泛。周笃文老师曾经和我说过,现在有的女诗人写诗词还在用妾自称。这种现象确实令人深思。记得2019年的某期《中华诗词》杂志,也刊发过这样一首《留守少妇》:“桂子飘香夕雁横,窗开一扇待归声。妾身最怕中秋夜,月向檐前分外明。”这首诗是经过笔者终审发出来的,当时没有留意,但是发表出来之后才意识到,以“妾身”来作为当代留守少妇的称呼,显然是不妥的。
古人确实有不少用“妾”来作为女子谦称的作品。比如唐桃花夫人的《在紫霄夫人席上作》:“昔时训子西河上,汉使经过问妾缘。自到仙山不知老,凡间唤作几千年。”唐崔氏的《述怀》:“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及卢郎年少时。”唐李白的《陌上赠美人》:“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唐戴叔伦的《织女词》:“凤梭停织鹊无音,梦忆仙郎夜夜心。难得相逢容易别,银河争似妾愁深。”宋严羽代拟的《闺中词》:“良人西去击狂胡,妾在闺中对影居。万里长看天外月,一生空得梦中书。”……这些作品中的妾字都带着特有的时代印记。
当代人当然也有用到这个“妾”字的作品,比如田遨的“青蓝涂抹作生涯,唱本偷来属妾家。欲扮女皇终不似,只应常扮赛金花”。缪荃孙的“眉山浅画髻云梳,生小鱼娃惯水居。妾自持篙郎系网,今朝准网罽花鱼”。……这些作品都有特定的语言环境和表达需求,用的位置也都是很恰切的。但是如果当代人真的把“妾”“奴”这类代称,直接写在抒情达意的诗词作品中,则显然是与强调思想解放和人格尊严的当代思潮是相悖的。
遗憾的是,当今某些诗词作者并不认为这是在开历史倒车,反而美其名曰“继承传统文化”。不错,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继承,但其中的糟粕呢?如果“诗词热”成了《封神榜》里的申公豹—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只往后边看,那么,这种狂热气氛中克隆出的诗词作品,也只能是机械的封建灌输和格式化的陈词滥调。
近来有一种风潮,说是“五四”以来,中华文化出现了断层。当年反对白话文的林琴南、章士钊、吴宓等,也被某些人捧为文化英雄式的人物。不错,过去对他们的评价或许不够全面,但借吹捧他们来质疑新文化运动,则是大谬特谬。难道五四之前的年代,就是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难道四书五经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还要在今天一概恢复旧貌?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伴随着吸收的过程,也伴随着扬弃的过程。古典文化中确实有值得继承的精华,但也不应忽视其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不能囫囵吞枣地还原和克隆这些东西。
当代诗词从复苏到复兴再到振兴,离不开独立人格和自由气韵,离不开时代思想的激扬和现代精神的滋养。五四精神不灭,科学与民主的圣火不熄,自由解放和光明新生的追求永不过时。在当下的诗词热衷,冷静思考一下百年来诗词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是一种必要的文化反省和历史反思。诗词作者不能人为钝化了思想的锋芒。
没有思想,形同僵尸。百年回首,“重回五四”!
02
本色说

晚清民国诗词研究,目前似有显学之势。当年主张“不墨守盛唐”“不专宗盛唐”而尊崇“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祜)的旧体诗人,也重新得到很多学人的关注。我陆续读了这一时期几位诗坛大佬的作品,觉得他们确实都有自己的色彩和光辉,也有耐人回味之处,但是也感觉其中的门户意识和乡土圈子意识过强了些。他们“风气相囿,结为宗派,类似封建节度”,一方面过分强调学习古人,偏重师承和借鉴,另一方面又喜欢纤靡委随,拉帮结伙。如果无一字是从肺腑流出,而是千人一面,百啭同音,原样克隆,就令人生厌。这一拨诗人也批评别的诗人“蓄积贫薄”“非其人而为是言,非其时而为是言”,但对照他们自己的创作实践,反而像是一幅自画像。
所谓“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主张,发展到极致就是“无一字一句不自读书创获”。重回五四起点衡量,这一拨儿诗人当年“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师古而不能驭古”所留下的历史教训,也是颇值得反思的。林琴南讽刺他们:“搜取枯瘠无华者,用以矜其识力,张其坛坫,……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林庚白批评他们:“沾沾自喜,以为得古人之真。”今日观二林之论,仍觉其中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年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新体诗人们的诗情如长河乱注,而旧体诗人们还躲在书斋一隅悠哉游哉地吟风弄月,自矜于“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些诗界大佬们孜孜不倦地在死文字里绕瞎圈子,脱离时代风云,远离苍生疾苦,最后只剩下个枯枝败叶般的文字窠臼。这些遗老遗少被新诗人打个落花流水,就当年的文坛氛围和社会环境而言,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前人说过:“本色者,所以保全天趣者也。故夷光之姿必不肯污以脂粉;蓝田之玉,又何必饰以丹漆?此本色之所以可贵也。”一味泥古而不能化古的诗人,做的就是蓝田玉上饰丹漆的事情。
“最好文章惟本色,是真富贵不繁华”,这幅咏白牡丹的对联,倒是可以送给诗坛仔细品味。
03
夏说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纳秀艳教授回忆,他的老师夏传才先生对她说过这样几句话:“你的作品写得很规范,有古雅之气,如果放到唐诗宋词里,很难区分。”纳教授开始以为这是先生给予的褒奖,欣喜不已,后来才理解夏先生说“放在唐诗宋词里看不出来”一句评语,包含两层含义:肯定诗有古雅之风,但缺乏时代特色。夏先生一语点中当代诗词的关键穴位,引人深思。
20世纪90年代,夏传才先生曾经在我的本子上写下过一首诗留念,记得有一句是“七十正少年”。那时,年过古稀的老先生依然还像少年一样透明真挚而又活力四射。后来虽然山水相隔,红尘纷扰,我和先生接触不多,但心里一直很敬重他。夏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曾写下几句挽词:“在春之记忆,为秋之燃烧。诗传新璀璨,才续旧风骚。”先生品行豁达,学养深厚,著述丰稔,是一代名师。他把“放在唐诗宋词里看不出来”这句话当作鼓励,同时更当作一种委婉的批评,这是需要后来者多品味一番才能感悟的。
诗言志是中华诗词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诗贵独出机杼,抒写心声。格律形式虽然是祖传的,但是思想和情感绝不能复制粘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沸腾、悲悯和恬美。唐诗宋词的经典魅力和语言技巧,给我们今天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但是其特有的时代氛围迥异于今的,不能砍削今天的韵脚去硬穿唐诗宋词的鞋子。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发达的大数据时代,模式化的排列几首所谓的“唐诗宋词”并不太难,难的是怎样把自由的呼吸、沸腾的体温注入那饰金挂银的冰冷泥像呢?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好叠韵、次韵,剌剌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谓之骨董开店。”此言一针见血,果然妙论。
文末再抄夏先生一段话,与诗友共勉:“写诗化用古诗句、用古诗意境未尝不好,但要做到脱胎换骨,有风骨,有表现力,尤其有现代感。诗歌要反映时代,要写出现代人的情志。所谓‘诗言志’‘诗缘情’,就是每个诗人所处的时代,有该时代的思潮和文化,用传统诗歌的形式去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这才是诗歌的意义。”
04
“桃花”悚?

据周笃文教授回忆,他的老师夏承焘先生曾就“鬼灯一线,露出□□面”让大家填空。“□□”填哪两个字呢?有的学生说“鬼灯一线,露出狰狞面”,有的学生说“鬼灯一线,露出血盆面”,有的学生说“鬼灯一线,露出獠牙面”。然而最后夏先生提供的答案却是“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桃花二字虽美,用在这里却举重若轻,更铺垫和反衬了惊悚的感觉,而且增加了想象的余地。诗词的修改,一定要记得删掉那些概念化的、生硬的词汇,也要避免人们用熟用滥了的腔调。
因为先入为主的错觉,我原来一直认为“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是夏先生自己的词句。后来读清代黄仲则先生的词集,才知道是出自黄先生的《点绛唇》,全词如下:“细草空林,丝丝冷雨挽风片。瘦小孤魂,伴个人儿便。寂寞泉台,今夜呼君遍。朦胧见,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全词应该是表述相思和怀念亡人,这是一首言情之作。所以作者这里用桃花面,本义大概不是为了表述惊悚,而还是为了表示女性的姣好容颜。不过如果单独作为一个填空题的题目,夏先生的讲解,则让我们对诗词的修改有了更多的感悟。
古往今来,诗人们在诗词修改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这也是写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房子盖好,总要装修之后才能入住。我们来看姜夔的“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这里的“吹”用得多么美妙,仿佛阵阵寒意从角声中透了出来。再请看苏轼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一个挂字,一个断字,前者把静景写出了动感,后者把平静写出了尖锐。再请看周邦彦的“风老莺雏,雨肥梅子”,把“老”和“肥”这两个形容词变成动词来用,既添加了灵动的韵律,又突出了意象的质感。再请看辛弃疾的《临江仙·探梅》:“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剩向空山餐秀色,为渠著句清新。竹根流水带溪云。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这首词里的“态度”“精神”和“破”字、“剩”字、“带”字的韵味和魅力,值得细细体味。前两个名词不动声色地把花和雪全部拟人化了,后三个动词营造出一种奇特的流动美,突出了探梅人的愉悦惊喜,也渲染出以动衬静的丰赡绵邈的独特风致,让平凡的山间景色有了不平凡的灵气和情感。
调换上去的词汇,其实都是平常多见的词汇,而且也多是平常多见的表达方式。夏承焘先生出的填空题中,为什么“桃花”更惊悚?其中的温度感和形象感,体现在平中出奇、陈字生新的功力上。
05
捻须说

唐代诗人卢延让说过:“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他的苦吟,是被当作诗坛佳话来叙说的。可是老先生捻断数茎须之后吟出的成果,还真是不好一概恭维。比如他的名句“狐冲官道过,犬刺客门开”“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只能当作行为艺术来看。究竟好在哪里?真是不好说。
作诗看的是写作的结果,不是写作过程。写作的过程即使被描写得再苦再累再感人,但最终没有好诗,也只能把一切归零。
一语天然万古新才更得诗家真趣。而像卢老师傅这般穿凿诘屈,蹇涩殊馁,则越雕琢则越显出扭捏,越苦吟则越显出才力困窘。正所谓:随口吟出句最奇,此间妙谛少人知。忍看卢老承追捧,一代吟风叹可欺。言诗苦似演小品,行卷仗得猫狗题。未必吟安一个字,何劳捻断数茎须?
06
虚实笔

宋初僧人惠崇圆寂二十年后,苏轼才诞生。苏轼写作题惠崇春江晚景诗的时候,和惠崇本人并没有交集。我曾把惠崇与惠洪弄混,在一篇文章中说“苏轼有个好朋友叫惠崇”,是错误的。惠崇所画《春江晚景》后世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通过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的妙笔,我们仍然能够想象和感受到惠崇图画中的温暖、美妙和鲜丽。
作者在诗的前三句描绘了画上的实景,第四句则转笔叙写了虚拟的关于河豚欲上的内心活动,进一步开拓了画面的想象空间,机智地增加了诗画中的动感和韵律。通过苏轼的诗句推测,惠崇的原画中其实并没有河豚,河豚只是作者的合理想象而已。我曾试着用实写的方式改写一下这首诗的第四句。比如: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曳尾河豚逆上时。
“逆上”就是向着河流的相反方向奋力游泳,这两个字把“欲上”那种想象性的动作变成了实际的动作描写,直接把河豚的形象勾画了出来,只是画面则显得拥挤了一些,塞得太满,不符合传统中国画虚实相生的美学原则。
再比如: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白日依山欲下时。
这里的“白日依山欲下时”把虚拟的河豚换成了实景中的太阳,时间写得更明确了,只是意境直白浅显,没有了苏轼原有的那种含蓄蕴藉的丰韵。
再比如: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坐看东山月上时。
这里的“坐看东山月上时”恬淡幽静,只是从黄昏到静夜,时间跨度有点太大,而且加了一些晦暗和朦胧,失去了原作特有的空灵和明丽。
这三种改写方式虽然都是实写风物,但反而不如虚写河豚更加耐人寻味些。画有留白之美,诗有留白之妙。题画诗贵在开拓新境,扩大想象,借题发挥,棋高一着,以少胜多,有心领神会之趣。
07
孤独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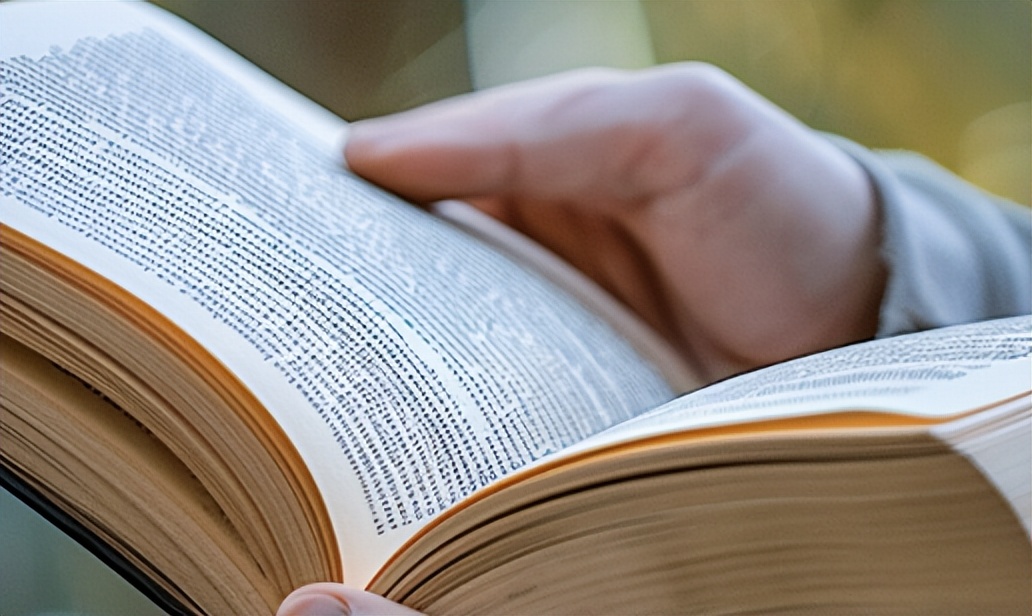
诗人们,有自己的原则和精神指向,有自己的追寻方向和青草世界,因而同时也有着一份单调简约而又是祖传的孤独感。
孔平仲的《静化堂》:“四境静山川,一枕闲风月。野水抱城幽,青天垂木末。”笔墨镇静而清丽,表达的却还是震撼人心的凄冷和孤寂。
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心无旁骛地笔墨,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天地之间的巨大的灰色调的孤独感。
畅当的《登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描写孤楼独伫般的激荡况味,以及四野包围的苍凉孤寂,画风诡异,动魄也惊心。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很多人说其中有着高瞻远瞩的种种哲理,但是我从文本之间,感悟到的其实首先还是一种无奈而绝望的孤独和寂灭。太阳落山,逝水横流,前路空茫,欲再举足向上,而楼层早已到顶,登高无望。至此,作者构建起来的正是一个凝固的绝灭的冷漠的感情空间。其中个体生命所体验出的这种另类的寒酸的孤独感,又有谁人会得?
陈子昂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里写的同样也是一种纵横六合的孤独感。“翻译”成五律,就是杜牧的《题敬爱寺楼》:“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孤独就像敬爱寺楼,是一座独立在旷野的建筑物,坚硬,冷漠,沉重,把诗人的心紧紧包围在其中。
古往今来的孤独感,是一个肃杀的苍白的历史幕墙。外国哲学家叔本华站在这沉重地幕墙前,对诗人们冷冷说道:“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08
相诗说

伯乐曾经推荐九方皋为秦穆公寻找千里马。九方皋三月而返,说在沙丘找到千里马了。穆公问:“何马也?”九方皋说:“牝而黄。”派人找来这匹马却是“牡而骊”。也就是说,九方皋把马的毛色和性别都说错了。伯乐因此评价说:“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者也。”要真正能够认识一件事物,是需要透过现象来发现本质的。关于清平乐的“乐”字读音问题,就类似千里马的“色物牝牡”而已。
另外,近来关于古诗词的读音,经常听到一些比较新颖的观点。比如“京口瓜洲一水间”的“间”字应该读一声还是读四声,就有不同见解。我认为,现代学者据古籍推断出一些字句的古音,可以作为非物质遗产的学术成果,但不可作为当代的审音标准。今天读者读古诗,还是宜以普通话为依据、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准。语文教学中遇到古今读音不同的韵脚字,可以特别注明押的是古韵即可,而现代阅读,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阅读,还是要按照普通话读音为正音。倘若各行其是,各读各音,并坚持以我为据、以我为尺,这就不是在推广传统文化,而是添乱了。
现在关于“清平乐”中“乐”字读音的争辩中,有一种考证思路是明显值得商榷的:即寻找前代读音资料为论据,以其中的年代远近作为正误的标准和取舍的依据。然而汉字的读音是伴随年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正如河水是在不断流动的一样。即使找到一个前代读音的资料,哪怕考证完全靠谱、证据铁板钉钉,也不能断定后代就必须以此读音为准,否则不就是在重复刻舟求剑的老套路了吗?
09
律金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苗春女士约我谈谈对英国BBC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看法,我找到纪录片从头到尾看了几遍。这部纪录片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中华诗词的恒远魅力和时代价值。杜甫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杜甫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颗圣洁的心灵闪耀着穿越时空的永恒光辉,不分种族,不分国度,任何时候都能唤起同一频率和节奏的共鸣。我们在屏幕上真切感受到一位伟大诗人细腻真实的心灵史,同时也透过这样一个独特的精神样本,更真切地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丰富传奇的时代细节。我想起美国诗评家丹尼尔·霍夫曼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诗歌是一个时代的感情气候。”只有杜甫这样的为苍生歌唱的伟大诗人,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不过坦率讲,BBC纪录片中的杜甫形象,和我心目中的杜甫形象也有着一些差异。包括杜诗个别字词的解释,也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比如纪录片中关于“剑器”的呈现,中国的观众还可能会有一些另外的解读。杜甫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话,杜诗精美的语言艺术因为中英文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很难得到原汁原味的保留。杜甫还曾自豪地说过:“晚节渐于诗律细”,意思是老来对于诗律的追求更加谨严精细。而汉语诗词格律的美妙,对于英文翻译而言则是一个巨大的美学考验。纪录片中的英文翻译可以传达诗意,却无法传递汉语格律诗词平仄和骈对的特有魅力,这也只能算是一种美丽的遗憾吧。
诗词格律被诗人马凯称誉为“黄金格律”。这种黄金格律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划时代的美学贡献,音韵美、形式美、和谐美,三美臻一,妙合无垠。诗词格律是汉语言特有的,只生长在汉语言的土壤里。《庄子·天道》中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中国的诗词格律之美,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在汉语言环境中心领神会,却无法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来展现。
10
束律说

现代科技不仅能够帮助诗词作者进行格律校验,甚至还能够电脑作诗,这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现象。电脑作的诗代替不了人脑,但是用电脑进行格律校验,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年来新创的诗词作品格律越来越精严,而且越是青年作者,对诗词格律的讲究也越认真和执着。这和电脑、手机,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给诗词格律校验所带来极大方便,是分不开的。但是倘若以今人的技术去衡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年间作品,嘲笑人家不拘格律就是不懂诗云云,这种观点是难以服众的。
李叔同在20世纪初写的《春游》,非常漂亮:“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这首诗类似现在人们常说的“新古体诗”。全诗明净轻清,恬淡欢快。虽然没有依照传统格律来写,但也依然别有一番韵味令人流连和咀嚼。
1962年,陈毅元帅在诗刊社举办的春节座谈会上曾经提出:“不按照近体诗五律七律,而写五古七古,四言五言六句,又参照民歌来写,完全用口语,但又加韵脚,写这样的自由诗、白话诗,跟民歌差不多,也有些不同,这条路是否走得通?”20世纪后半叶,诗坛上也出现了一批借用旧体形式而又突破平仄格式的作品,有的称解放体,有的也标七律五律和词牌曲牌,还有的称新古体。其中的成功作品如“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以及《某公三哭》,等等……影响也都很广泛。这种试验在今天看可能会有争议,但在当时文化环境中的探索意义和突破勇气也是应该尊重的。脱离了当年的诗词写作环境和读者基础,所做评判就是不全面和不公正的。
诗词格律只是个简单的技术话题,并不是衡量诗歌高下的依据。我们不能根据现在的诗词尺子,去苛求前人的诗词格律意识。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过评诗的四字标准:“汉、魏之诗,正大高古。……正,谓不淫不伤;大,谓非叹老嗟卑;高,谓无放言细语;古,谓不束于韵,不束于粘缀,不束于声病,不束于对偶。”吴乔特意将“古”字放在衡量标准的四字之中,是颇得我心的。
11
一字不易

秦代吕不韦曾经把《吕氏春秋》书稿挂在咸阳的城门上,“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也就是谁能够在上面修改一个字,就赏赐千金。这是文化自信,也是一种高明的广告艺术。
我读深圳大学徐晋如先生《百花冢行》时,对其“诗人热恨噀长天,忠臣漆血染木棉”“惟有断石饱斜阳,万人海中独如醉”等句反复咏叹,而至“当日残碑镌弘光。麝土一坏阅兴亡。百花尽锄佳城堕,人间无觅锁骨香”四句,则有一个疑问不解,随后发信问晋如先生:“坏”字是否“抔”字之误?晋如先生回复此处确实用的是“坏”字。并言“坏”音pēi,土丘;而“抔”音póu,一捧,二者音义并异。后来查资料,见到前人有“千车拥孤隧,万马盘一坏”“惆怅江南土一坏,斯人地上不胜忧”“一坏骨肉仍同穴,百代衣冠择所安”等用法。我想晋如在怀念古代诗人张乔的《百花冢行》这首诗中,特意选用“坏”这个字,情感上可能寄托着一份尊重的感怀,语感上也自蕴一份典雅的古意。而如果按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改“坏”为“抔”,则只余下“捧”“把”“握”的语义,无形中减少了几许韵味。这可算是一字不易的一个当代例证吧。
宋王禹偁在《寄献鄜州行军司马宋侍郎》中,写了几句很爽的句子:“醉挥拔萃判,一字不复改。传写遍都下,纸贵无可买。”这里的“一字不复改”五个字,多么牛气啊。今人中也经常遇到自称“一字不易”的人物,这就要拿出文本认真掂一掂分量了—前提是做到方东树《昭昧詹言》称赞谢灵运的要求:“康乐无一字不稳老,无一字不典重,无一字不沉厚深密。”倘若果真文从字顺、精准恰切,当然值得敬重。而倘或没有足够斤两的文本支持,所谓“一字不易”的自信,就不过是大话炎炎的笑话而已。
此时就要重温袁枚老人的话了:“惟糜惟芑,美谷也,而必加舂揄扬簸之功;赤堇之铜,良金也,而必加千辟万灌之铸。”把这几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并“一言以蔽之”的话,也就是:美文离不开修改啊。
12
“门槛”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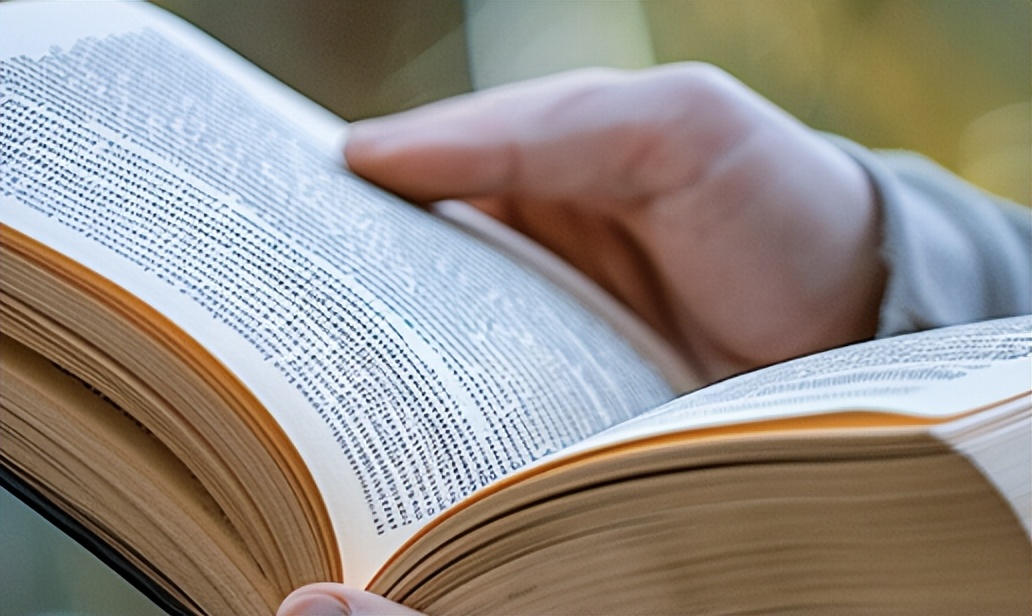
诗人赵京战老师曾经谈到某名家提出的当代诗人界定门槛,必须要有“名门、名师、名友”。所谓名门,就是要有祖传。所谓名师,就是要有派系。所谓名友,就是要有圈子。我们当时是当作笑话来讲的。
客观而言,有了“名门、名师、名友”的优越条件,对诗词学习和诗人成长当然更便利,在诗词传播方面也大有帮助。但这三“名”并不是认证诗人的玉牒金书。若以此夸耀并傲视同侪,则面目殊为可憎。
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并不隐名。考官除了看试卷成绩,还要看其社会评价因素,有所谓“通榜”“行卷”“纳省卷”等说法。我们熟知的白居易,在唐贞元三年科举考试前,就带了诗文谒见著名前辈诗人顾况,就是一次著名的“行卷”。顾况当时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开了一个流传千古的玩笑,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又夸奖说:“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唐代这种科考、自荐、举荐三结合的取士方式,当时也引来了营私舞弊等弊端,到宋代就废止了。
《围炉诗话》中说:“诗乃心声,非关人事,如空谷幽兰,不求赏识,乃足为诗。……自唐以诗取士,遂关人事,故省试诗有肤壳语,士子又有行卷,又有投赠,溢美献佞之诗,自此多矣。美刺为兴观之本,溢美献佞,尚可谓之诗乎?”现代人写诗词,没有科举压力,也没有行卷风习。一泻情怀,四起吟声,原以为“血统论”早就没有市场了,不料却仍然不时碰到标榜家世、攀附师承、拉扯朋社的鲜活例证,无可奈何,只好当作小品来看。
《沧浪诗话》说:“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我想,还有一俗需摒除,就是“俗气”—骨子里的。
13
“尊奉”说

某些当代诗词作者的自我简介中,不时出现“词尊谁谁”“诗奉谁谁”的腔调。无以名之,称其为“尊奉派”吧。被尊奉者有的是古名家,有的是今名师。倘出于返本开新、桃李深情的初衷,其心自是可敬,但也有“尊奉派”人士以为加上“尊奉”二字就“根红苗正”“门户端然”了,头顶上仿佛也立刻增添了光环。
说到“尊奉派”,我想起京剧花脸袁世海先生的一段回忆:郝寿臣先生首次给他上课时,曾经问他:“跟我学戏,是把我捏碎了成你,还是把你捏碎了成我?”袁世海说:“当然是把我捏碎了成您啦。”郝寿臣听了哈哈大笑:“错了,把你捏碎了,你永远成不了‘郝世海’。你得把我捏碎了,再成一个‘你’。”郝寿臣先生的话,其实涉及的是关于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袁世海先生将墨守流派之见的京剧演员讥为“伸手派”:“他们不是想着如何创新,而是满足于把前人的东西伸手拿过来,吃现成的饭。他们爱问:我像不像某某派?说他不像就不高兴。”遇到这种演员,袁世海先生只好说:“不错不错,再努力。”记得谈起这些的时候,老先生拿扇子往桌子上一拍,冲我哈哈一乐:“他们的耳朵只听进去了前半句,后边那个‘再努力’就被风刮走了。”的确,流派是京剧艺术的精华,但流派并不是艺术小圈子,也要有新的发展、新的创造。只有创造才有转化,只有创新才有发展,只有创造和创新才能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以之验诸当代诗词,同理。
“尊奉派”,其实也就是“伸手派”。习惯简单重复和机械模仿,不肯下创造和发现的气力而已。诗词写作要吸纳传统,也要检验传统;要固守本根、不忘初心,也要知古倡今、求正容变,从而革故鼎新,包容互鉴,在前人脚印终止的地方继续向前探索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