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斌推荐语:25年前,我亦师亦友的北大荒作家杨孟勇,创造了57岁做心脏移植的世界奇迹,并接续创造了心脏移植不久后停止服药、健康地存活了25年的人间神话。杨孟勇用一颗不正常的心脏,把生命的不可能活成了可能!他的神奇故事,曾经由中央电视台等几十家电视台制作专题广为传播。长篇纪实散文《活下来再说》,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推荐连载此书,意在引起读者对生命的尊重和感动,同时感受这个社会的优越和温暖。尤其要向给予杨孟勇二次生命的哈医大二院、及其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活下来再说
著/杨孟勇

14、死神与生命的第二次较量
经历了手术台,经历了第一个危险的夜晚,还远远不够。
这场手术,犹如一个人独自走在陌生的路上,不会知道迎面而来的事件是什么,继续走下去,还会发生些什么。当一切出现的时候,又那样悄然,那样不露声色。死神不是望风而逃的家伙,他能够操纵和调动起来的力量,常常难以想象。
专家们说,心脏移植要过三关。第一是手术关,看样过来了。第二是感染关。我迎接的下一次生命考验,是一个57岁的生命对术后感染的抵抗。病菌一定会趁我在危难之机大肆人侵,看我能否扛过去。扛不过去,只好向对方投降,如战场上的败军,打出一面白旗了事,无条件接受死亡的整编。有幸扛过去,便是柳暗花明,又一番景象。
日趋老化衰弱的躯体,手术中锯骨开胸的创伤,手术前就开始服用减低免疫力的硫唑嘌呤,术后又加上终生必须服用的环孢A,这都是不利于一个生命的。严格地说,这场对抗是在不公平的状态下进行的,犹如拳击台上凶狠有力的泰森,面对一个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中学生,一拳过去,不打个半死才怪。但这一切又不可避免。虽然事先有了各种措施和防范,但决定成败的,只剩下一个因素——那就是命运。
第二天一早,医院来电话让妻去监护中心,这个通知让妻脸色顿白,她在思索是否出了什么事情。虽然第一天夜里出现的险情,她全然不知,但她知道,只要我还在监护室一天,死亡的危险就存在一天。
她疑虑重重地走到监护室门口,进第一道门时,护士帮她穿上消过毒的白大褂,戴上消过毒的帽子口罩。走进第二道门,在消毒液里洗了手,走进第三道门时,看见我躺在床上。
妻来到床边,见我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孙晨光教授走过来对她风趣地说:“你们好几天没见面了,你摸摸丈夫的手,或者接个吻吧。”
孙教授爽朗地笑了。
妻没有采纳孙教授接吻的提议。她也是个年过半百的人了,生命中的浪漫与激情早已被岁月随手带走。
我没有被笑声感染,只是黯然地把手伸给妻,她轻轻握了握。
一切尽在心里。
这是术后第一次见面,一次刻骨铭心的相见,她见到了活着的我。她的那根红毛线绳儿,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还是把我的一条命拴住了。
也许因为百感交集,她并没说几句话,我知道她此时心中有话说不出。坐了一会儿,她执意要离开监护中心,刚跨出大门,她哇的一声哭了,边哭边往病房跑。
病房一旦响起哭声,往往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结束。
哭声惊动了护士长,她跑过来问:“怎么啦?怎么啦?”
妻握住护士长的手说:“我这是高兴的哭哇——你们真的把他救活了!”
护士长说:"那你就哭吧,这些天你也太难了,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
今天早晨起来,身上轻松了一些,略有了精神。
孙晨光教授值班,作为监护中心主任,我从手术台上下来,日夜监护的重大任务全部交给了他。
孙教授走到床边鼓励我说:“下地走走,行不行?”
我略一思索,爽快地答应了:“行!”
护士小夏帮我把起搏器导线接头卸下,把右腿输液管撤掉,我跃跃欲试。
几天没有下地,不知道能走几步,也不知道能走成什么样子。我试探着从床上下来,两脚刚着地时,并没有什么异常。往前迈了一步,立即感到两腿无力支撑身体,膝盖之上的肌肉像被一条条全部抽空,腿上只剩下一副无血无肉的干枯骨头。我惊疑,刀口明明在胸部,腿上为何无力?
迈出第二步,左腿突然颤抖了起来,腰一闪,差一点跌倒。孙教授显然看到这一切,忙问:“行不行?行不行?”
“没问题——"我说,“只是有点不习惯。”
护士小夏举着药瓶,我试探着绕床走了几步,竟没有摔倒。走不远,只能绕床走一圈儿。
"好!太好啦!”孙教授在一旁为我喝采,"真不愧是男子汉,被锯开的胸骨捆了六道钢丝,第3天就能下地走路!——老杨,神啦!”
李医生也在一旁为我高兴,忙拿起数码相机拍下了我颤抖着走出这几步的情景。
我下地走路的消息,立即传回4号病房,妻和儿女们陆续到监护中心探望我。
夜色渐深,偌大的监护中心平时要住4个心脏手术病人,病人多时,还要加床,现在只有我自己。我想不受干扰静静地睡一夜,但难以做到。护士在夜晚10点交班,在这之前要把我喊起来服药,睡下不久,12点又服一次,天亮之前除了一次口服药之外,又采了一次血,拔出针头,睡意也被带走。这一夜迷迷朦朦,似睡非睡。
好景不长,我迎来的是一个倦息无力的早晨。
食欲不好,勉强喝了几口黑米粥,不一会儿就感到腹中一阵翻腾,张开嘴猛地一下吐了出来。呕吐物喷了一地,最后一口吐到床单上。我看到黑红的米汤溅在四周,颜色有些像淤积了很久的黑血。
死神的一双手,就这样伸了过来。
陆护士长一边收拾一边问:“今早你吃的什么?”
“黑米粥——”回答她时,我已有气无力。
一整天都昏昏沉沉,许多人来看我,问我的感觉,我半闭着眼分辨不出他们是谁,只是懒懒地简短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那情景,与重病时的我,与躺在母亲身边濒死的状态差不多。头一个夜晚的危险我无法体验到,这一次全给补上了。
氧气罩依然扣在面颊上,从细小软管里冲出来的气流,风暴一样呼呼作响,吹得鼻孔像干裂了多年的焦土。
傍晚,志勋来看我,虽然他戴上了消毒帽、大口罩,只露出眉眼,但我一眼认出了他,并觉察得到他的内心正在为我分担着苦难。
他是个性情内向的孩子,又容易激动和莽撞,这一点有些像我。
海光来过之后是云松,这几天云松有些感冒,不然早早就会来的。怕感染我,只好拖到最后。
夏教授来监护中心,在消毒液里洗了手,走过来给我作了全面检查。这次检查使他发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虽然我温度不高,也不咳嗽,但已处在感染之中!
他让我张大嘴,发现我口腔出现黏膜斑块,听诊又听出肺部有湿罗音。回到办公室他立即召集医生会诊,研究抗感染治疗方案。
心脏移植之后,感染发生率几乎百分之百。监护室的里里外外,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灭菌,那些无所不在,无孔不人的病菌病毒们,还是不肯放过我。
陆护士长一溜小跑赶到4号病房告诉妻,让她准备电锅熬桂皮水,给我嗽口消毒。
妻问她:“什么桂皮?”
“中药店卖的那种。”陆护士长催促说,“赶快去买吧。”
海光穿上大衣去市中心寻找中药店,寻找家电商场买锅。
从那天起,我吃的香蕉要用开水烫外皮,喝的饮料罐要在拉口附近用酒精杀菌,9套餐具轮回消毒,每两个小时就用桂皮和口泰两种药液清漱口腔。抗菌素几天几夜不停。换药时拔出针头,血管中饱和的药液就会顺着针眼向体外汩汩流淌。
抗感染的严峻如同洪水到来,人们纷纷上阵,在大堤上抗洪抢险。
姚教授急匆匆来到小监护室,让我张开嘴,发现口腔粘膜已成块脱落,我用舌头舔几下,吐出来的是一块块白粘膜,很像误食了白塑料膜的动物,消化不了,又一块块吐出来。
肺部仍然有湿罗音。这是肺部感染的征兆,控制不住肺感染,下一步就是死亡!
可以推进监护室的移动X光机每天都为我拍一张片子。右肺下部已经出现模糊阴影。
护士们把我扶起来用手掌适度拍打后背,想用拍打震动的方法解除肺粘连。
那些日子,小监护室10平方米的空间里,除了各种固定仪器之外,移动X光机早晨推进来拍片,下午心动彩色超声仪推进来检查刚移植的心脏,加上各种测试,真有些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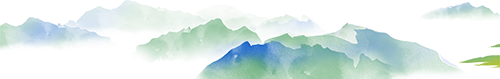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