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斌推荐语:25年前,我亦师亦友的北大荒作家杨孟勇,创造了57岁做心脏移植的世界奇迹,并接续创造了心脏移植不久后停止服药、健康地存活了25年的人间神话。杨孟勇用一颗不正常的心脏,把生命的不可能活成了可能!他的神奇故事,曾经由中央电视台等几十家电视台制作专题广为传播。长篇纪实散文《活下来再说》,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推荐连载此书,意在引起读者对生命的尊重和感动,同时感受这个社会的优越和温暖。尤其要向给予杨孟勇二次生命的哈医大二院、及其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活下来再说
著/杨孟勇

8、走进生命课堂
本来我是可以依靠自己仅存的一点力气走进手术室的,可护士小姐和妻还是把我扶上了来接我的手术车。车上有一床印有红十字的棉被,护士们给我盖好,妻怕我这一路受风寒,又极不放心地掖了掖被角,车子就被推走了。没走出多远,妻突然双腿跪倒在走廊上,朝窗外尚未放亮的天空磕了三个头。拜天,拜地,拜神灵,也拜命运。这种时刻,一个热爱丈夫的妻子,还能做些什么呢?她的这一身不由己的行为,引起很多人过来观看。有的咂咂出声,有的长吁短叹。
那天是2000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早晨5点,车停在手术室门口,我下了车,身着湖绿色服装的护士们无声地把车推走。门前只剩下了我。
我站立在原地,望了一眼已经敞开的两扇宽大的金属门。看得出来,时间一到,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你就无法逃脱了。生也逃不脱,死也逃不掉。手术室里只有一两个人的身影。我想,手术恐怕还要等一会儿才开始,留下了这段空余,做些什么呢?想了想、心血来潮,忽然摆出一副悠闲的模样,像一个前来参观的局外人。而手术室向来是拒绝参观的。
我像早晨散步那样,轻松地走了几步,迈进手术室的大门。
我的脚步竟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活动在手术室的那两个人,只顾低头做着自己手中的事。这种情景让我好好体验了一下手术室的安详与宁静。听不到一句言语,没有一声突然发出的响声,有如一个迷路人误入了一座空谷。
我有些起了大早赶晚集的小小遗憾,除此之外,一切皆无,头脑里一丝浮沉也没有。
据说,有人没进手术室就紧张得要死,躺在手术台上就昏迷得不省人事了,弄成手术没开始,人就猝死的慌乱局面。
看来医生们不必担心我会出现这类情况。为此,我突然产生了不给医生们带来麻烦的些许轻松,也许还有几分洋洋自得。
时间尚早,手术室又走进一个人,依然对我视而不见,甚至看都不看一眼。
不看更好,我像个参观者向右侧靠了靠,身后是一堵墙。手术室大而空荡,不便站立在屋中央。那样,常被视为发傻,或者被称为没眼力的。尤其在这种时候,万不能失去眼力的。
“把衣服脱了吧……"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传来,听得出是个男人的话语声,但语音柔和,又十分神秘。
我知道这是在跟我说话,抬起头寻找跟我说话的人,环视一圈,没发现有谁在面对我。于是越发地神秘了。
这是一种命令。命令是要执行的,找不到人也要脱的。只是碍于室内的温度有些低,估计了一下,好像在14-15℃左右。
我慢吞吞地做,很像磨洋工,也有点消极对抗的意味。因为我不想过早地赤裸着身子站在屋子里打冷战。
先是上衣,再到衬衣。本来棉裤和裤头可以一并脱下来,却一件件磨蹭着单脱,直到脱光为止。我估计这段时间被我故意拖了足足三分钟。
真的有一阵冷意袭来。低下头看一眼堆在脚下的衣服,像一堆无用的垃圾。如果我在手术中死掉,真的就是一堆令人发指的垃圾了。
“上手术台吧……"
那个神秘的声音发出第二道指令。
对面的墙上出现了一个不算很大的方孔。刚才我进来时,已经对手术室作了全面的观察,但还是把那个不大的方孔给忽略掉了。我想,是不是在我迈进了手术室那一刻,那个平时处于关闭状态下的小方孔突然打开了,方孔内有一双眼睛一直在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像那种军事行动中隐蔽的暗哨。
想证实这个想法不太容易,方孔内光线较暗,看不清里面有什么动向。
我极为平稳地向前迈出第一步,朝手术台走去。
原以为在这样的非常时刻,一定会有人过来,慢慢搀扶着我的胳膊,或者在前面作个引导,像国际大赛中的运动员出场,前面必有一个举办国的儿童高举木牌,徐徐前行。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不免让人有几分失落感。
既然什么也没有,只好单独出场,步伐一丁点儿没乱。正中是一个孤零零的台子,上下打量了一番,我不想承认那就是手术台,但它的确是。当我接近了之后,更是令人大失所望。呜呼,那只是一块极为普通又显得有些狭窄的板子而已,外表似乎没有什么包装,简直像战地包扎所从老乡家里借来的一副门板,与我想象中的能够置换心脏的手术台相去甚远。
我已经在手术台前立定了,看了看长度没什么问题,所担心的是它的宽度。如我这样的57公斤,1.64米的人躺上去尚可,换上个大块头上来,就显得窄了许多,不小心压坏,或者压偏,掉下来如何是好?
两年后,《东方时空》的主持人问我:"杨先生,上手术台的那一刹那,你感到过恐惧吗?“我回答:“上手术台的前一天,我就不再顾虑什么了。"
“为什么?”主持人问。
我说:“是一种预感在支持着我,那个预感是:这次手术一定会成功。”
手术台不高,抬腿即可以迈上去,我用一只手把住了对面板子的边缘。轻提一口气,脚和膝盖已搭在了台子上,我奇怪,此时的我哪儿来的一股子力气?收一下腹肌,整个的人已经上了手术台,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便平静地躺了下来。要知道,若在心衰发作时,完成这一套动作,不亚于自由体操中的那些苦苦练就的高难动作。此时,我却连大气也没出一口。
躺下不久,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不用扭头去看,就知道是麻醉师来了。
麻醉师到了,生与死的大戏就要拉开帷幕了。麻醉师走到手术台边,和蔼地问我:“怎么样,紧张吗?”
她的靠近,使赤身裸体的我有几分羞涩。
我抱歉地笑了笑说:“高教授,我一点都不害怕……”
“那就好,那就好……"麻醉师对我的状态十分满意。
我忽然想起了刚才注射的那两针,就问高教授:“做手术非要注射镇静心理的药吗?我用不着那种药,护士们非要坚持注射。”
高教授说:“你不害怕更好。用了就用了。”
真的想同她唠上几句家常,多好的一个倾诉对象。在这样特殊场合特殊见面方式中,倾诉一定别具风格的,这种时刻同她多交谈几句将是多么惬意的事了。遗憾的是已经不可能了,此时,感到左脚踝上方凉丝丝的。经验告诉我,这是酒精棉球擦在皮肤上引起的。果然麻醉师告诉我说:“现在给你用药了,扎个小针儿,一点儿都不疼。”
左脚踝上方有刺痛感传来,但很轻微。
麻醉师低声问我:“是不是不怎么疼?”
我又笑了笑回答:“像蚊子叮了一口。"
我知道,说完这句话,用不了多久就会昏迷。我想极力地多感受一些什么,但药液已在我血液中扩散,渐渐地,我失去了知觉。
早晨我曾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见自己微笑的面庞。
此时,我微笑着进入一个未卜的世界,风险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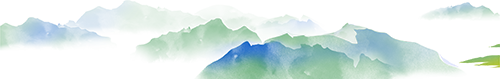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