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主人公“老刘”,一位没有文化的农民。拾过粪贩过豆,当过兵打过工,养过鸡喂过猪,凭着正直善良和一点“小聪明”,与贫穷奋斗,与命运拼搏,换来了幸福的晚年。
纪实散文|邻居老刘(中)
文图|崔方春
四、贩黄豆
1982年11月,他大喜,女儿出生了 。孩子的到来,给这个小家带来了无限欢乐,同时也给他增加了巨大愁肠。妻子的照护,女儿的喂养,都需要钱。冬天,地里没活,人闲在家里“一分钱不进”,小日子怎么过啊!
他到处打探门路,寻找挣钱的机会。一日,有人告诉说高平县城黄豆比较好销,价格也高,但不了解具体情况。他动心了。第二天一早讨了一袋五十斤豆子,装进退伍时的帆布包,急乎乎去了孟匠火车站。
从孟匠到高平五十公里,绿皮车票五毛一张。到了高平,黄豆很快销了出去,比进价每斤高三分钱,赚了一元五角。第二趟扛了八十斤,他希望多挣几个钱。可是一算账,来回车票一元,饭费三角,基本没钱可剩。怎么办?他脑袋一转,有了办法:凭着熟悉的环境混进孟匠站,到高平伺机出站。回来,买张站台票上车……五分钱解决了来回问题。这种不合规行为,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与此同时,自家弟弟和两个要好的邻居也加入了贩豆。
乘火车省力快捷,但靠逃票总不是办法。另外,搬运百十斤重物,两头都是麻烦。他想到了自行车。去高平的砂石公路崎岖不平,有的路段需要下车推行爬坡,一般人要骑行两个半小时以上,困难可想而知。然而,他们各驮一百五六十斤大豆,却一天一个来回。他更是能干,每次都比别人多,最多时驮了一百八十斤。太行山的冬天滴水成冰,汗水天天湿透他薄薄的棉衣,衣服表面都现一块一块冰硌渣。
进入腊月,黄豆需求量大增,价格不断上扬。挣钱的机会来了。他讨来洋槐木找人做成平板车架,买上一对车轱辘,牵来邻居家的毛驴,人驾辕驴拉套,与小弟弟搭档做起了“大买卖”—-一次能贩上千斤!然而,驴子太小,速度太慢了。两趟下来,人和毛驴都撑不下去了。眼看着要丢掉挣钱的机会,他急了,急得上蹿下跳。“不行!必须买具大牲口——马或骡子”。他想。
一匹好马或骡子,起码得上千元甚至更多。钱从哪里来,考验着他的能力和智慧。他想到了邻居近亲,想到了战友同学,想到了一切可以求助的熟人。最后,是一个同学作担保,找在农村信用社工作的老乡贷款五百元。是最高额度。不得已,他找了位熟悉的牲口经纪,趁钱吃面买了匹掉牙的老马牵回了家。
几天下来,年老体衰的老马撑不住了。一到爬坡,他兄弟俩全力以赴推车也无能为力,老马动不动就抛锚路边。咋办,可难煞他了。谁知,他想到了家住中途某村的姐姐,想到了姐姐家的壮骡子,靠这一招解决了问题——他套马拉到姐姐家,换上骡子到高平,卖完黄豆再去找姐姐套马回自己的家。

人都有背运的时候,他也倒了一次楣。这天,兄弟俩到场早,占位好,买得人多。弟弟收钱他掌秤,偏晌午黄豆已全部出手。他们走进一家小馆,想填填肚子。“哥,今天行情不错。饭前咱们清清账,看赚了多少。”弟弟边说边从裤兜里掏钱。一合计,结果不但没赚反而倒贴了几块钱。俩人傻眼了。弟弟捶胸顿足,后悔不小心丢了钱。“没关系,咱这几天把它找回来”。他拍拍弟弟的肩膀。次日,他买了个带拉链的人造革包,挂在弟弟的脖子上,再没出现丢钱的情况。
这个冬天,他挣了八十元。不但过了个宽裕的春节,还为第二年春种打下了基础。
五、闯兰州
1983年开春,黄豆生意不好干了。只靠刨那几亩薄地,不能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他整天愁眉不展,百思找不到出路。这时,妻子的一位亲戚来电话说,急需一位做瓤皮子的师傅,问他愿不愿试试。一听有活干可挣钱,他二话没说立马乘火车赶到了兰州。原来,这个亲戚有门以面换瓤皮子的生意,原来的师傅因故返乡,叫他是填补空缺重启开业。
瓤皮子是兰州的风味小吃,工艺独特,酸辣可口。那时,当地人有付加工费以面换皮,回家自己调料配菜、调拌食用的习惯。做瓤皮子,需将面粉加水揉成硬面团,醒面后多次洗面,使面水与面筋分离,面水沉淀后倒掉上层清水,留下面浆。接着在平底罗罗刷油,舀入面浆均匀铺开,上锅蒸至表面鼓起大泡,取出放冷后揭下,刷油防粘。面筋单独蒸熟切块。然后,皮子切条,与面筋一同兑换给需用的人们。
制作过程连环作业手工完成,未经师傅真传或专业培训不可能轻易上手。另外,做出的皮子能不能及时换出去,同样考验着经营者的意志和能力。从未见过吃过瓤皮子,面对一堆盆盆罐罐、锅灶瓢勺,他一脸茫然。对如何走街串巷兑换皮子,更是不知所措。
这时,亲戚发话了:“我不懂。懂的师傅走了,没人教你。要么,我说说大路子,你自己摸索着干。要么,你打道回府,我再找人。由你自己定!”。一听这话,他低下了沉重的头。“我两手空空,脑袋空空,咋干啊?!”
这一夜,他没合眼。翻来覆去,想来想去没找到合适的主意。但有一点是成熟的,坚定的。“我不能回去。因为,回去没有出路。”他说。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找亲戚表明了态度:“我干,您给不给工钱我都干!”从此,他凭着机灵的脑瓜,勤劳的双手和不服输的劲头,走上了一条新的谋生之路。
做皮子费时费力,利润微薄,挣得是辛苦钱。如技术娴熟,工艺过硬,一斤面粉可产三斤皮子、二两面筋。若功夫不到,总量会在三斤以下。当时通行,一斤干面换二斤皮子,外付两毛钱加工费。他认真听亲戚讲制作路子制作过程,仔细揣摩其他主家的操作技巧,边听边试大胆摸索。他睡变了形的行军床,吃住操作在不足十平米的棚厦里,起早贪黑不知疲倦地一个人忙活。从和面洗面蒸煮切条,到搬上搬下,用辆旧自行车载着串巷叫换,都一丝不苟扎实去做。
他经历过挫折,遭遇过失败,也收获了小小的喜悦。经不懈努力,他终于叫响了“牌子”,积攒了人气,获得了周边居民的认可和信赖。皮子兑换量,从开始的每天三十斤、五十斤,逐步上升到八十斤、一百斤,最高达到一百二十斤。当然,劳动时间也延长到十小时、十二小时。兑换量上升,赚头越来越多,但他却没得到应有的收入。
这年腊月二十八,在外拼打了九个月的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亲戚给的全部四百元现金,回到阔别的老家。离开时,翠绿的庄稼已收获归仓,浓密的树叶已化为根根枝条,襁褓中的女儿已呀呀学语蹒跚迈步,迎来的将是又一个四季轮回。面对憔悴的妻子、不认识爸爸的女儿,他眼泪横流,泣不成声……

饭桌上睡觉前,他向妻子叙说在外打拼的经历,吃过的苦头,做“皮子”的艰辛,寄人篱下的苦衷。与妻子一起分析打工的利弊、经营的前景,琢磨未来的发展、潜在的问题,探讨在兰州继续干下去的可能性可行性。最后,他决定:继续闯拼一把,得混出个“小样来”。过罢春节,把承包的二亩地托付给父母,将家里那辆旧自行车办理铁路托运,他肩背衣物被褥,手提水瓶奶粉,扶着怀抱刚逾周岁女儿的妻子,再次登上了绿皮列车。
六、谋生苦
赶回兰州,妻子女儿吃住在亲戚家里,他饭时过去吃饭,凌晨加工皮子,半晌傍晚两次上街兑换,晚上睡在棚厦,一切还算正常。然而,一个月后亲戚那边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邻里纠纷,棚厦被停止使用。活儿没了,落脚地没了,脚跟未稳的一家三口陷入了困境。不得已,他四处寻觅租了地处半坡的两间土屋,作为加工皮子和妻儿的安身之地。
这间土坯垒成、空空如也的房子,破旧不堪的屋顶,高洼不平的地面,变形的木门木窗,四处透风撒气,甭说住人就是放杂物都难保安全。简单维修后,他靠一头盘灶弄锅,支架放盆,辟为加工皮子的场地。居中盘了个土炉子,装几节铁皮烟囱,用于烧水做饭。在另一头,用烧灶蒸皮子的煤饼干垒成“大炕”,铺些谷秸干草,作为仨人的睡觉之地。他一家三口住进去,连个挂衣服放碗筷的家什都没有。他街上捡块石板,顺路寻根棍棍,隔壁讨个框框,对门要条木板,各取其材用其所能,做成日常用具以满足“家的需要”。
日子一天天理顺,生计一日日上道。他一如往常凌晨即起,点火升灶,和面洗面,打罗蒸煮,一天两次走街串巷换皮子。妻子则烧水做饭,收拾家务,照看孩子,有时间帮他料理一下“皮子”上的事情。他心地善良,懂得感恩,没忘记唤他到兰州、给他一技之长的亲戚。从微薄的收入中,每月拿出六十元,不逾期不间断,亲自送到亲戚门下。一家人虽然收入有限,生活清苦,但有饭吃有地儿住,心里安逸,其乐融融。
不日,妻子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这天大的惊喜,让他有了新的希望,添了不竭动力。他像一只四处采蜜的工蜂,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不停地飞,不停地转,不停地为这个家奔波。同时,他尽其所能,照顾妻子女儿,照顾未出生的孩子。妻子妊娠反应严重,胃口不好,吃啥吐啥。他跑遍周边餐馆食店甚至骑车几十里,买回妻子愿吃的水果食物。他请来一位退休产科医生,为妻子作检查调胎位。为减少爬坡,方便妻子出入和为生产作准备,他又一次租房搬进条件相对较好的村居。
这个同是两间的房子,院子略大,道路平整,透风撒气的地方也少了许多。关键是有一盘现成的宽敞土炕,可以生火取暖,可以容几个人居住。妻子在这里“坐月子”,会更好更安全。但需要他重新打理,重整炉灶,包括搬运存储的成吨煤球煤饼。他说,他凭着年轻,凭着力气,凭着对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楞楞一个人担了下来,重筑了新的小窝。
妻子的预产期到了,他忙乱中更多的是担心。预约的产科退休接生婆(医生),年龄大距离远交通不便,来一次都需要他用自行车接送。那个漫漫长坡,都是他一步一步推着老太太爬上去。临产的那个晚上,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出出进进,坐立不安,生怕有什么闪失。把待产的妻子交给妻舅母,他摸黑路半夜接来接生婆,做助手烧热水烘热炕,期冀孩子平安到来。
他终于盼来了开心的时刻。哇的一声啼哭,打破了严冬夜晚的宁静。“男孩,是个男孩。”听到接生婆的话音,他原地蹦的老高,仰天长叹:“儿子,儿子,我有儿子了。老刘家的福哇!”这天,是1984年12月20日。孩子根在晋城,生在兰州,他给儿子起了个有意义的名字:晋州。
儿子的到来,增添了家庭喜悦,也加重了他的压力。妻子奶水不足,孩子基本靠奶粉喂养,稍大一些还要添加鸡蛋白糖等辅食。三元五毛一袋的甘南牌奶粉、两元一斤的绵糖,在他手里都沉甸甸的。为了孩子,他每天要早起一小时晚睡半小时,多和几斤面多做几斤皮子,多挣几毛钱的加工费。为这个家,他每时每刻幸福着快乐着,努力着奋斗着。
时间过的好快。转眼到了7月中旬,到了兰州的雨季,儿子也到了“七翻八爬”的龄段。不知怎么了,那时节老天下起了漫长的连阴雨,三天,五天,一周了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样的“倒楣雨”,对简陋的土房子是最大的祸害,对他一家同样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天下午五点多,天气阴沉,中雨淅沥,他在街巷的雨水中兑换着皮子。儿子躺在炕上酣睡,女儿坐在那儿玩耍,妻子正在料理家务,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意外正悄悄地袭来。忽然咔嚓一声,以秫秸报纸塑料布做成,用于防灰防尘的仰棚,裹挟着尘土烂泥突然从土炕上方塌落,把两个孩子盖在了下面。他妻子一把拽出女儿,双手扒出儿子,惊魂未定地搂着俩灰头土脸的孩子嚎天大哭……他看看透明的屋顶满屋的狼藉,瞅瞅瑟瑟发抖的娘仨,牙咬得咯咯作响!

连夜,他们一家四口搬离危险境地,栖身于亲戚家。8月中旬,他通过铁路零担托回了衣物、做皮子的工具器具,包括那辆勉强能骑的自行车。携妻带子绕道看望移居西安的妻舅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老屋,也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凄惨生活。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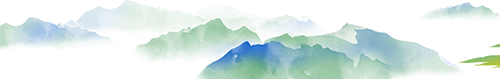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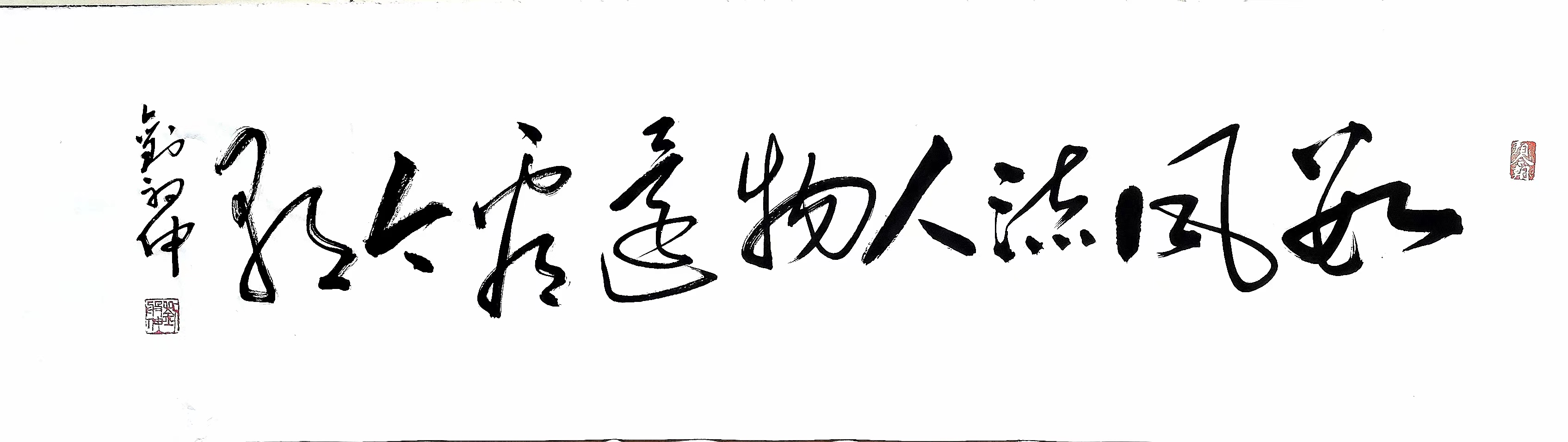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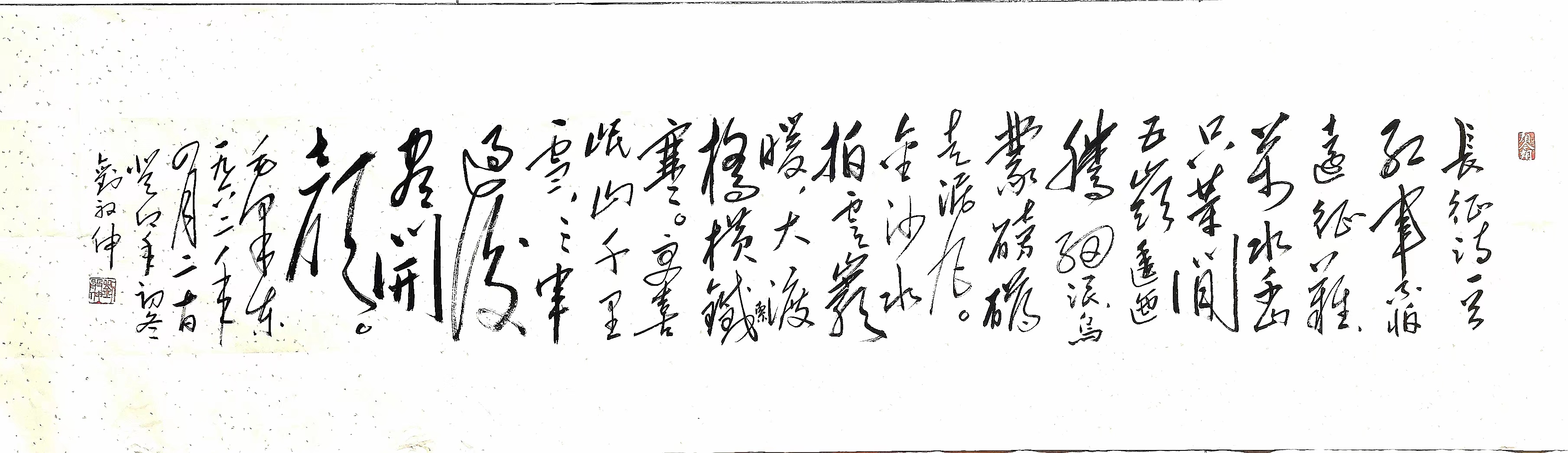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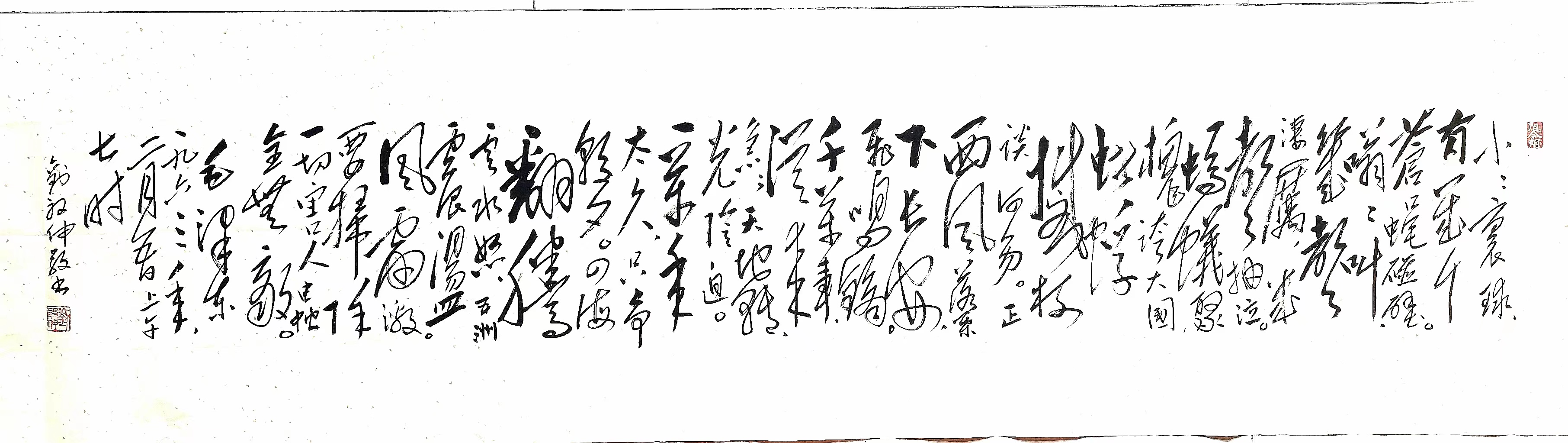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