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衍生真爱诗性的特殊“土壤”
——读吕剑先生的《青石关》
张宗发

吕剑先生从1938年夏天开始写作,并以《大队人马回来了》一诗引起广泛关注。他直到1984年离休前,都在竭尽全力创作。他一生创作的诗歌、评论、杂文、散文等结集出版二十一种,可谓产量惊人;智慧过人;风格袭人。读了厚重的《青石关》,我却又有了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和判断,感觉它是“一种真爱的逻辑诗性表达”,把对事物的爱表达的淋漓尽致,使读者在不经意间与之产生共鸣。
“青石关,青石关!你是齐鲁古国的界关吗?(吕剑先生的《吕剑诗存》第3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你还记得不记得?曾有一个农家孩子,从莱芜城北的穷村,攀越七十里山路,通过你窄窄的隘口,到博山城里去读书?你且说说,你且说说,那也算是‘出国留学’吗?(吕剑先生的《吕剑诗存》第3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青石关就联系着齐长城,齐长城就联系着齐国和鲁国,齐国和鲁国就联系着军事对垒,重要的关口说明什么?政治,经济,军事都在这里集中体现。所以,一般来过青石关的人,都会联系到两国的政治差距;经济交往;战争烽火,干干巴巴地猜想那遥远的过去。然而吕剑先生写两国的国土一笔带过,转而写自己从青石关的来来回回中,悟道了一个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出国,把自己的求学之路说成是“出国留学”,利用这种潜在的古今关系,审美与剪裁的关系,去符号化艺术,最终实现审美需要、审美理想、审美心境、审美态度,引起大家的特殊注意,并作出特殊的美学价值判断、回味。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在创作状态下看出的“花”与“鸟”的另一种诗意风貌,其实作为客观外物的花不会“溅泪”,鸟也不会“惊心”,这就是诗意创造。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很少人为青石关书写,就是写过青石关的人也未必从心底里、情义里、暧昧里去“越过你这道险峻的关隘,通过你这段崎岖的峡谷。”吕剑先生就不一样了,他说:“我每次路过你那里,总要在你身边站上一站。”“如今,多少春秋过去了,那列置在你关头上的城阁还在吗?小姐还在吗?古碑还在吗?老树还在吗?当时来来往往的人们,他们的破鞋踩下的足迹,他们的灰汗交流的面颜,那种独轮车的悲嘶声,那种牲口的哀鸣声,那些汗气,那些粪味,还有无留在你的记忆之中?(吕剑先生的《吕剑诗存》第3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其实这是一种“始于喜悦,止于智慧”的趣与爱。是对城阁的爱;是对小街的爱;是对古碑的爱;是对老树的爱;是对人们足迹的爱;是对人们汗水的爱;是对那独轮车的爱;是对那牲口的爱,他的爱无处不在,只用一个“还有无留在你的记忆之中”来表达就够了。
记得许庆胜老师说过:“诗歌无论是社会化写作还是个人化写作,都必须有个性,个性的形成便是诗人写作成熟的标识之一。先锋派诗歌,说它是一种文学现象,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诗歌个性。先锋诗歌的晦涩难懂,说到底主要是一种表达策略选择,对它的解读不能再按传统路径,而须用先锋式规律来解。”现在,诗歌主要的流派有新月派、九叶派、朦胧派等等,拿这些流派的个性来论吕剑先生的诗,是不符合逻辑的。但他的诗带有时代的特点,时代的气息,时代的光彩。他的情真意切,他的胸怀宽广,他的坚定执著,点点滴滴都渗透在炯炯有神的诗眼里。“陡峭的关坝,荒寒的深谷。从你的关顶俯视,真乃‘下临无地’,从你的沟底仰望,则又是云气飘绕。”特别是“一片片铁青的陡崖,一蹲蹲狰狞的怪石”中的形容,“铁青的陡崖”“狰狞的怪石”毫不亚于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继而从“你是大好河山之外的一段无人眷顾的地界吗”开始,娓娓道来:“你那山峡的两岸,是白猿难攀的绝壁,是苍鹰不至的巉岩,只有卑微的短榆酸枣,只有枯黄的荒艾败草,毫无变易,年复一年,零乱无章地错杂其间。哪里有花枝的招展?哪里有鸣禽的啁啾?你是一道与农民的居处同样寒伧无比的穷沟!(吕剑先生的《吕剑诗存》第3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就是这道穷沟,却年头到年终承载着博莱之间的重要贸易,“博山要的莱芜的土产,多少都要从这里运去,莱芜要烧的博山的煤炭,多少都要从这里运出。”进而联系到自己的亲人,乡亲们,即使运到家的,全是使百年老屋越熏越黑的浓烟,还是在努力奋争。
“他们从煤窑办上一车,几十里山路盘到关前,才能蹲在关顶的石头上喘上一口气,抽上一袋烟。”“在只能通过一辆车的狭路上为争一线之地,为了先走一步,他们经常破口大骂,经常打得头破血流。”
鲁迅在世的时候,就非常重视“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他说:“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可能吕剑先生早就意识到,或者说早已看透了这一点,受家庭的培养,受社会的熏陶,受历史的打磨,吸取了肥沃土壤中的特殊营养,写出的诗行才既朴实又威严、生动。在山洪暴发的时候,他没有强力去写山洪的气势、山洪的美姿、山洪的精神,而是笔锋一转,去写山洪中的人们,“那些运炭者,那些唯命论者,却又无不协力搏战,抢救那一辆辆可怜的小车,抢救那一车车可怜的煤炭,他们倘遇损失,看得比命还重,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此时的山洪还是山洪吗?这里的山洪已经窜出了山涧,窜出了大地,窜出了历史,它和大众的命运息息相通,它和历史的潮流链在了一起,促使着人们急盼着“斗柄回寅,吉星高照,好年月实在不容易盼到!——不能只是祈求神灵的护佑,应以自力从古代走向今朝。”
当吕剑先生听说青石关修了盘山公路,人们不去走那狭窄、盘曲、坎坷的深沟时,发自内心的喜悦,发自内心的祝福,发自内心的歌唱,促使着他对青石关深深留恋。“如今你被投闲置散了。那么,当你告别了你的寒伧之后,或许要变为大树参天的山林,在你的新史上绽出一枝奇葩吧!而你和那里的人们,曾经共过忧患,同过血汗,那么,他们的贫穷、苦难、劳累,也应当投闲置散了,并在与他们的寒伧告别之后,也要一变而为文明富足了吧!”瞧,他想到的还是走过青石关的人们;居住青石关的人们;敬仰青石关的人们。对青石关的将来有所顾虑。1996年的时候,人们对古迹的重视成度还在觉醒、起步阶段,他已站在一个大文学家的高度来审视青石关,对没有开发青石关,没有让青石关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感到惋惜,同时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充满了热切希望,衷心的祝愿:“青石关,青石关,我少年时代的青石关!你要永远成为一处,仅供后人凭吊的遗迹,丝毫也不感到恋惜,断然和我们挥手道别吗?………(吕剑先生的《吕剑诗存》第3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又提出了“生态诗”的观点。其实,诗歌是为社会形态服务的,现在讲生态文明,跟上形势,就出现了生态诗,其实还是老祖宗讲的那句话:“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现在的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社会形态;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这就要求作者紧跟形势,在继承中发展,不能忘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形式和风格之真美、形式和风格之本色,“紧贴时代脉搏,纪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充分体现时代性是生态诗的重要标志。”
“一般人往往地咬一咬带皮的香蕉,酸苦,以为不好吃,而这其实只是香蕉皮的味道;而诗人作家则在‘抽象地倾听’中剥掉那皮,所以他获得了‘香甜’,完成了审美创造。”(见许庆胜《苗得雨诗文赏艺》362页),吕剑先生写的《青石关》跨度多少年,小时候上学时的所见、所闻、所历,在诗中一一展现,但最终他没有忘记自己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做到了天衣无缝,令人起敬不已。
全诗自始至终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旁征博引,也没有笔扫千军的词调,让人看到的是他成长的环境,“不是由我的父亲,就是由我的叔父,赶着一头小毛驴,来回地把我接送”,那是他生根发芽的“土壤”。他不知多少次地经过青石关,青石关的一切他悠记心房;青石关历练了他的经验;青石关铸就了他的主张,“青石关,青石关,你是大好河山之外的一段无人眷顾的地界吗?”那是他茁壮成长的“土壤”,那是他注定饱写“青石关”的土壤。他成功了,成为大众眼中的著名诗人。他的存诗量多,堪称当代宝贝,值得大家细读深研,让他回过头来服务于“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让他大张旗鼓地做回属于人民大众的“土壤”;一种衍生真爱诗性的特殊“土壤”。
2025年3月17日

附:吕剑原诗
青 石 关
吕 剑
青石关,青石关!
你是齐鲁古国的界关吗?
你还记得不记得?
曾有一个农家孩子,
从莱芜城北的穷村,
攀越七十里山路,
通过你窄窄的隘口,
到博山城里去读书?
你且说说,你且说说,
那也算是“出国留学”吗?
是幸还是不幸?
我是那个村子里
独一无二的中学生,
且因我个小体弱,
受到过分的宠爱了。
每逢寒假,每逢暑假,
不是由我的父亲,
就是由我的叔父,
赶着一头小毛驴,
来回地把我接送。
越过你这道险峻的关隘,
通过你这段崎岖的峡谷。
我带着一身村气,
这样通过你的道路,
在颜山中学攻读三年。
我每次路过你那里,
总要在你身边站上一站。
岁月无情地流逝,
众木频增着年轮,
如今,多少春秋过去了,
那列置在你关头上的
城阁还在吗?小街还在吗?
古碑还在吗?老树还在吗?
当时来来往往的人们,
他们的破鞋踩下的足迹,
他们的灰汗交流的面颜,
那种独轮车的悲嘶声,
那种牲口的哀鸣声,
那些汗气,那些粪味,
还有无留在你的记忆之中?
青石关,青石关!
陡峭的关坝,
荒寒的深谷。
从你的关顶俯视,
真乃“下临无地”,
从你的沟底仰望,
则又是云气飘绕。
一片片铁青的陡崖,
一蹲蹲狰狞的怪石。
关沟又那样迂回盘萦,
使人们难于举足止步,
使车子难于推动刹稳。
我们的小小的毛驴,
就在千车之间磨鞍擦蹄,
那些山地的子民,
穿越十里砂石赶到颜神①。
青石关,青石关,
你是大好河山之外的
一段无人眷顾的地界吗?
你那山峡的两岸,
是白猿难攀的绝壁,
是苍鹰不至的巉岩,
只有卑微的短榆酸枣,
只有枯黄的荒艾败草,
毫无变易,年复一年,
零乱无章地错杂其间。
哪里有花枝的招展?
哪里有鸣禽的啁啾?
你是一道与农民的居处
同样寒伧无比的穷沟!
这道寒伧无比的穷沟,
却是莱博之间的通路。
博山要的莱芜的土产,
多少都要从这里运去,
莱芜要烧的博山的煤炭,
多少都要从这里运出。
那些苦力,为赚一升半斗,
推着独轮车,打这里贩运。
多少农民,我的父亲和叔父,
一到农闲,都来“盘窑炭”,
为了寒冬能取到一点温暖,
为了自运能省下几吊钱,
为了赚上几吊,好度年关,
即使运到家来的,尽是
使百年老屋越熏越黑的浓烟。
他们从煤窑办上一车,
几十里山路盘到关前,
才能蹲在关顶的石头上
喘上一口气,抽上一袋烟。
在只能通过一辆车的狭路上
为争一线之地,为了先走一步,
他们经常破口大骂,
经常打得头破血流。
他们不是农民弟兄吗?
这时不是,而是冤家相逢。
饥饿、苦难、劳累,
使他们很不容易互相忍让,
反而相互仇视,丧及人命。
青石关,青石关,
这些你还记得吗?
夏季大雨骤至,山洪暴发,
但见乱石滩里巨浪滚滚。
那些运炭者,那些唯命论者,
却又无不协力搏战,
抢救那一辆辆可怜的小车,
抢救那一车车可怜的煤炭,
他们倘遇损失,看得比命还重,
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
而当朔风摇山,满沟堆雪,
那些运炭者,那些唯命论者,
却又必须协力相挽,
从难于辨认的故道上,
缓慢地新压出一道黑色的车辙,
就是在那数九寒天,
浑身也都蒸腾着热汗,
他们却每每竖起大拇指,
笑夸谁是勇推六百斤的壮汉。
青石关,青石关,
这些你还记得吗?
青石关,青石关,
多少年来不能相见了。
你有没有在夜间听到
我为你作过多少次的祷告?
斗柄回寅,吉星高照,
好年月实在不容易盼到!——
不能只是祈求神灵的护佑,
应以自力从古代走向今朝。
听说盘山新修了广路通途,
如今你被投闲置散了。
那么,当你告别了你的寒伧之后,
或许要变为大树参天的山林,
在你的新史上绽出一枝奇葩吧!
而你和那里的人们,
曾经共过忧患,同过血汗,
那么,他们的贫穷、苦难、劳累,
也应当投闲置散了,
并在与他们的寒伧告别之后,
也要一变而为文明富足了吧!
青石关,青石关,
我少年时代的青石关!
你要永远成为一处
仅供后人凭吊的遗迹,
丝毫也不感到恋惜,
断然和我们挥手道别吗?………
1981年8月,“青岛笔会”归来后作
①博山旧时又名颜神。

张宗发简介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济南市民间文学研究会会员;济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济南市莱芜区散文学会会员。
中国长城研究会会员。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济南市民俗学会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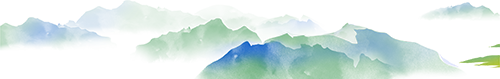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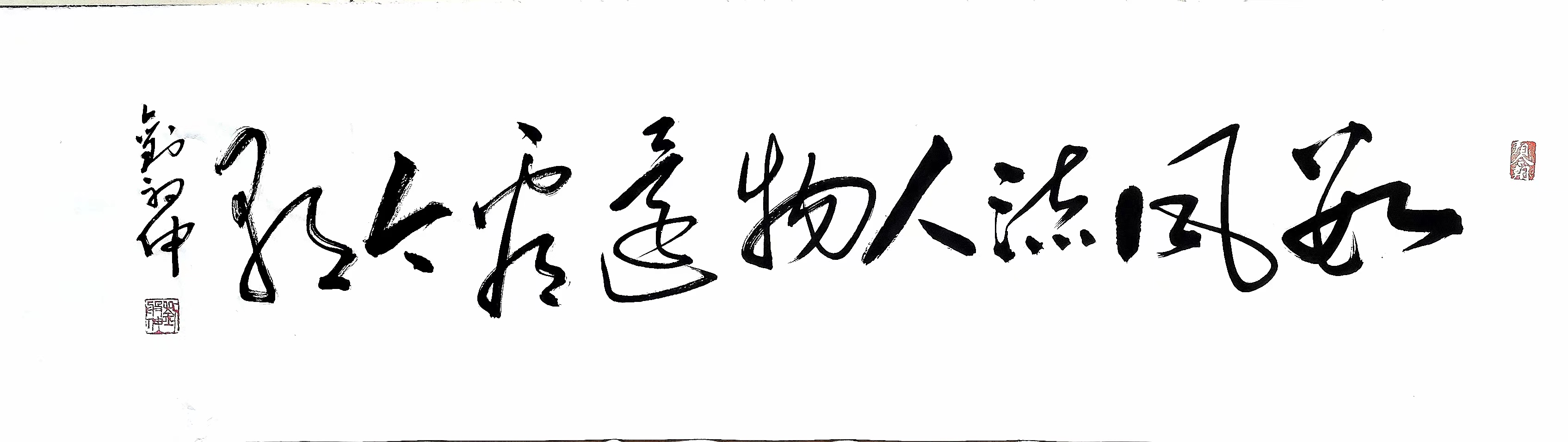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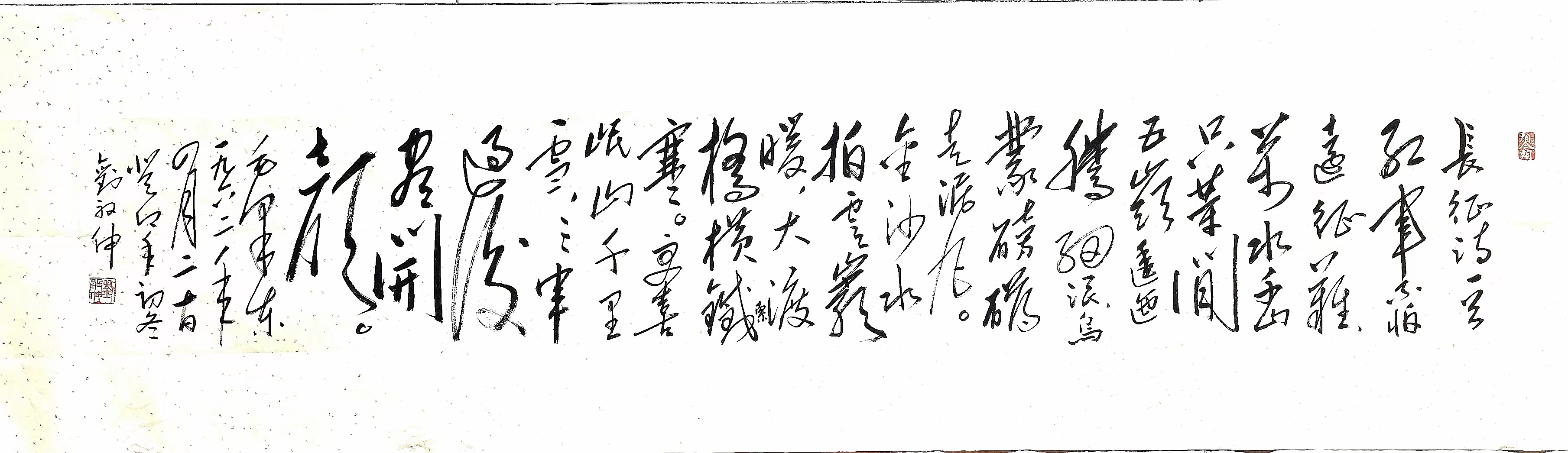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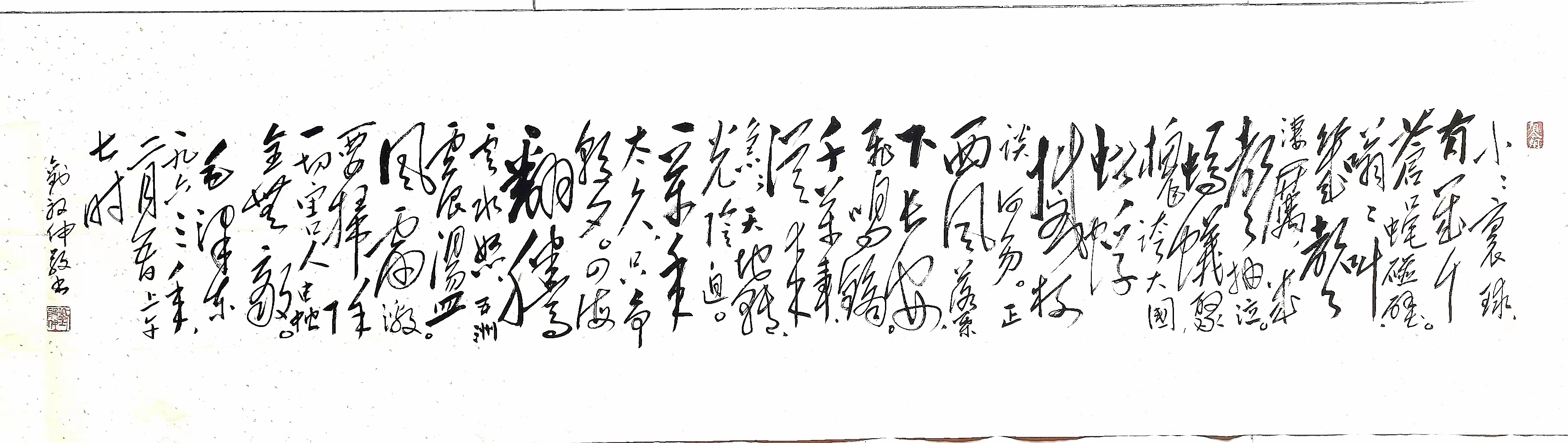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