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磊(吉林)
▌关于星期一的一课
星期一,大巴车又出发了,
从新竹路通往合心镇,
有一大批人的工作被定义在这里,包括我。
是如此肯定,这是关于星期一的一课,
只有蚯蚓一样的现实,
带着新冠病毒的尾巴,
让大巴车在一条公路上爬行,从来没有疲倦。
那是传说和事实的一种经过,
似乎是一个诗人的证明,结不清退休生活的账单,
依旧写下没有养老金的诗行,
外搭上一些小心,可以值一份早餐。
就像是一个犹太人,从其中考量自己甚少,
是少见的习以为常,
绕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却落入恐怖的罗网。
毫无疑问,也相当于我的判词,
罕见于罪恶中的无人赦免,
正如我坐在一把空椅子上,把身体塞给几何体的幽灵,
已经有四十五个月了,
充满了死寂的悲伤。
2024/9/9
▌远离黑夜大师
把两个世纪失踪的椎骨攥在手心,
和我的命运连接在一起,
好似是一个幽灵。
我看见享受死亡的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被红太阳的灰指甲撕烂了,
只留下一堆火,在照亮死亡帝国的黑夜——
此刻,幽灵的獠牙是白晃晃的,
又冲入红色城镇,又溅落了几滴血色斑点,
又把整个红民村洗劫一空。
而我却在红民村之外受伤了,
两个黑眼睛,看不见通往远方的一条公路。
现在,只有在喉咙中塞满猎人,
现在,只有从一个椎骨上跃过一座纪念碑,
现在,只有摧毁一场致命的加冕礼,
现在,只有活着穿越死亡——
就这样,在以另一种手势招呼自己,
从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失踪的地点开始流亡,
远离黑夜大师,不可停歇。
2024/9/13
▌启蒙手记
捂住受伤的额头,说起孤独的事儿,
那是增殖的邪恶,
在汉语中膨胀着,像从神秘中冒出来的气泡,
既是被羞辱的真理,又是被捅破的空灵光环。
这也是生成的启蒙手记,
超过希望的美德,即是美德的奴役,
在饱食着信仰的盅毒,一如进化论的惊叹号——
于是,我在凝视幽暗的午夜,
难道不是病态的时光浓重而又发霉,
犹如大祸临头的一次昏厥,
有如在预定活死人的一条出路。
天啊,我被罪恶隐蚀的前兆起源于童年,
离不开北中国的流放地,
在过着连神仙都不忍心再看下去的日子,
在问:“嗨,想去哪儿?”
我说:“我想纠正出生的过错,或走进流产诊所,
酷似冒犯一颗流星的一具婴尸,
想获得一次得救。”
2024/10/25
▌神在
我想怎样代替神在,就怎样代替神在,
因为神在就好,
可以不必用思想撒谎,不必诵读地藏经。
我不能让灵魂在身体里迷失,
哪怕是一具皮囊牵扯着毕生精力,
也要致力于此,
任由失败的人生经过胸怀,不必为自己哭泣。
也不必向占卜师占卜,
入冬时节的空茫幻影抓不到最后的天空,
如同我的双手抓不到十九层的语言高楼,
也无法重拾起身体的碎片,
逐渐死于欲望、贪婪和黎明——
是啊,只有骨灰瓮在闪现着远方的光芒,
可以遇见我尚未离开的一刻,
能够看见我正在返回某些值得回忆的事物,
比如:葵花、蓖麻和白杨树,
在被生物学定义着,包括我——
2024/11/14
▌今天是星期三
的确,我天真如诗,
正在治愈我的羞耻,在为真相赴死,
正是视觉边缘上的一点清寒 。
今天是星期三,
我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俯瞰着工厂的后花园,
有两个工人空手走在一起,
仿佛是被寒冬冻结着,没有了剩余价值。
在远方,有一大片荒芜的黑土地,
被一辆辆绿皮火车掩饰着,
并以烟和雾霾驱使它们,在完成盲目的火焰,
焚烧过谎言的田野。
而我仍在每天早晨上班,中午休息,晚上下班,
在营救自身,以及我那可怜的影子,
一直在问:“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再拉上百叶窗帘,
然后,写下这样一首诗。
如果我不写诗,那么就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
在把灵魂送到时间之外。
2024/12/4
▌枯燥之诗
差不多是用了一个上午,
我在读谢默斯·希尼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
听见了自然的神秘召唤,
于是,我在上午十点钟失语,
顾不上被管辖的舌头,再次把脸贴在一本书上,
在享受词语的物理时光。
是的,没有一个诗人的脸是草浆纸做的,
我却闻到了青草的味道,
而谁愿意描写它们呢?只有我在把脸挨上去,
挨得心跳,唯恐惊扰了所听到的声音,
那是关于植物的枯燥之诗。
可惜呀,这样的时光是短暂的,
几乎是被生锈的钟声打断了,
而我却总是想把钟锤从诗行上拿走,
并不顾忌恐惧,哪怕是幽灵的威胁是这样的,
让我失踪在短暂的诗意中。
2024/12/19

▌办公室笔记
我计划做半疯半癫的一个人,
已经完成一半,
使我处于忧郁,以敏感的语言诠释诸多事物,
几乎是胶结着细沙一般的恐惧,
但必须得控制住沙漏,
一定得这样,在用圆珠笔抄写荒唐的生活。
比如:在办公室里干着屎上雕花的工作,
活像是被面具人眉批着,
一定要从监视和告密的缝隙中挤过去,
试想一下,那是怎样的一个疯子。
虽然说是被遑以施舍什么,
我却在问自己:“我爱荒诞的生活吗?”
怪不得,我要把剩下的一半生活交给诗,
连看一眼工作现场也不看,
一个劲地命令自己,再为绝望提供备忘录,
就好像自己已经死去,同时我还活着一样,
真是一举两得。
2024/12/23
▌使人无法猜想
终于可以公开秘密,我如诗,
除了诗歌之外是一无所有,
没有我,也没有碑文。
别说雷同,被偏头痛埋藏的诗人不止我一个,
还有颤动一线的牧神午后,
何况,坏蛋的世界在故意抛弃我们。
嗯,我不是榜样诗人,
让每一个诗句都有出处,从不改变写诗的理由,
在太阳的白眼下划一条线,
以天际线划开星期二的混搭词语,
在蓝色的天空边缘归零,使人无法猜想,
像时光的骰子从不苟同于偏见……
有人说:“你像斯特凡•马拉美。”
我说:“是的,在我身后有他的影子,
宛若倒挂在我的身体上的一只蝙蝠,
在半睡半醒之中打盹,像在黑暗半空的消歇,
热爱半空,但并非永久。”
2024/12/31
▌世界怎么了
流行的病毒语言,
使我不想加入对病毒的讨论,
只有闭嘴,在把红太阳当成一种悬念,
看上去也不是彼得堡。
而红太阳在时间的皱褶中埋下病根,
凭着浑圆的信仰,
一直在划着思想的边界,只是头脑的创伤,
只是猜想,只是徒劳,
像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无形,
比精神病人更加讨厌彼得堡的冬天。
可以查看一下地图上南昌和彼得堡的对称,
南昌仍在像精神病那样看病,
却钝于历史的借口,以催眠术向人发难。
没错,李宜雪被冠以雪中花魁,
却一点面子也不给冬天,在问:“世界怎么了?
我只为了拨开眼睫毛上的霜寒。”
2025/1/3
▌日出的神话
在早晨,从北中国升起的金太阳,
要我认识日出的神话,
还要我认识谁是人,谁是野兽。
我已经预感到这一天,
要我把鱼尾纹化作纪念碑,
要我从眼睛里喷出蓝色火焰,在为一个人祈祷。
是啊,在水火之外父亲走进一面多棱镜,
那乃是我的贫穷和犯罪,
那乃是大疫三年必有妖,
而这两句高烧话,只是在为魔鬼辩护——
而在如今,我将加入凡人所得的运动,
让我在经受自己,
在推倒舌边的牙疼,用每一颗牙疼呼唤父亲,
像我在一堵墙上挖洞,
赎罪于内心的祠堂,在为得罪于父亲而赎罪,
并以一个金色隐喻扑向自己,
或仆倒在父亲面前。
2025/1/14
▌这样也好,让我知道就好
在寂寞中寻找自己,
有秩序的时间便是幽灵,在把我置于生活,
使我无法摆脱宿命。
就像是合心镇的裂痕,正在治愈遗忘,
并从一粒安眠药片中找到那一个,
那是赫尔曼•黑塞,
在证明诗歌提供不了庇护,
好比是二手时间,正在摸黑清洗一个表盘,
突然停止在凌晨两点钟,
在说:“哪里的工厂多,你就在哪里工作。”
谁也不知道,我在把心外意象视为事实,
像一个疯子总想杀死另外一个人,
那是一头荒原狼在鄙夷自己,
总是走上穷途末路,不会待自己好一点儿,
在克林索尔和合心镇死过两次,
一次死于黎明,一次死于黎明与落日的重逢,
这样也好,让我知道就好。
2025/1/22
▌再把一首诗当成骨灰瓮
谁会知道,我是诗的隐喻?
有人在不停地看我,却描摹不了我的人生,
也不等于灵魂一词,
仅存在于孤独之中。
唉,为什么要在地狱之上寻找鲜花?
一如狼藉的声名,扬名于出生的村落,
发生在龃龉之间,也发生在一枚苦杏仁当中,
却忽略了石头开花的声音。
此刻,保罗•策兰在向我走来,
比我还重,在苦难的天平上重新表白,
在说:“受苦和牺牲是我们的命运。”
嗯,我已经不可回头,
把满手时间编成手指,
把我的面貌塞给虚无主义的黑眼睛,
再把一首诗当成一个骨灰瓮,
那是记忆的坠毁与还原,错过了喋血的春天,
仿佛在为我的流逝而存在。
2025/2/10
▌蹩脚的汉语线索
十二月的夜晚是寒冷的,
是疲劳与忧虑的混合,只等于汉语的一张钞票,
已经被岁月花掉了,
空留下虚构的一个表情包。
这个夜晚也有风,
我却不适合于风的尺寸,越过了灵魂的疆界,
作为一个乡愁的主题,
仅留下一节蹩脚的汉语线索,
不让时间撒谎,把霉变的十二月抛出去,
偏爱上白昼的寒冷律令,
在说:“美在低温下也依然是美。”
我将在这里展示自己,
没有我的地址该有多好,让我从荒僻之地转身,
让我登上一列绿皮火车泊入一座火车站,
同样驶进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前世,
并以黑夜的命名术说起闻所未闻的一件事儿。
譬如:对合心镇的不文明叫法,
使我不像一个本地人,
也不像是列宁格勒人,
只是一个诗人。
2025/2/9

▌我被一个皮囊羁绊着
没有不朽的灵魂,只有不朽的诗。
而这句话在撕裂我,
我被破坏的真相吓坏了,
叫来一个人闯入内心和我聊聊天,
就像我的小心肝。
此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骂自己是白痴,
我却不以为然,仍在写诗,
在质疑虚构的时间,
在说:“时间是神恩馈赠的一种启示。”
可是,我们不能相处太久,
在一个小时之后,我要赶他走,
不想和任何人说话,谁也不是我的地狱。
别担心,那是在为灵魂和诗无法融入生命核心而羞愧,
此时,我被一个皮囊羁绊着,
比哲学清晰,一看就是一个人,
在说:“人是堕落的,不可救药。”
2025/2/18
▌为孤独正名
在至暗时刻过夜,
那是午夜零点使我睡不着,
在凌晨崩塌,连同我所仰望的星空和喧嚣时代,
好比是乌俄战争的疑云,
弥漫过三年记忆,也包括三年大疫。
此时,我的耳朵却是聋的,
被炮声和疫苗当成小厮,
在北中国的白夜写诗,记录下第聂伯河的忧郁,
也记录着黑龙江的涟漪,
是如此贴切在为孤独正名,
那是因为白银之光而与声光交织在一起。
按理来说,我只是安静生活的一个信号,
却不是,那么像被傀儡瘫痪在一张床上的僵尸,
横躺在黑暗的统治之中,
远不如一根枯树枝, 可以看见一只黑鸟结束白昼,
再将我粉碎成黑暗的两个齑粉,
完全是虚构的,完全是乌有的,
一个是空心的,
一个是灰色的。
2025/2/24
▌愿我被神定义为诗
现在,语言世界是黑暗的,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定义,
也是神的定义,
因为坏蛋的世界让语言失真,让我说不出真理。
而我并打算在黑暗中偷欢,
只想以第一人称说出真相,
把自己交给生活,把我留给合心镇。
是呀,我在以黑暗为敌,
正在合心镇过夜,压根就睡不着,
每到午夜零点,都要贴近繁密的星辰想事儿,
在说:“等着瞧吧,
那是我曾经的样子,已经是绰绰有余,
已经逸出语言世界。”
到那个时候,我要了却妄念,
愿我被神定义为诗,当然是记忆中的碧眼人,
当然是无暇顾及黑影子。
2025/2/26
▌我不打算再看它们一眼
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
看不懂拉丁语的人在看电影,只是看剧情。
不说看电影的人吧,
如果我懂英语,那么我就会把英语翻译过来,
把电影制作成配音,
用听得懂的汉语洗耳朵,洗心,
那样,就会有人为我送上一瓶红酒,
用威士忌包装一个高脚杯,
以思想的嘴巴啜饮。
可以幻想在一个酒吧,
神明的幽辉,一直弥漫在一个半敞开式的包间中,
怡然自乐于古希腊式的幸福。
这样,也会让我的诗歌变得淡泊,
把乌俄战争,欧盟以及美国总统搁置在一边,
就像是排列好红、黄、蓝的词语,
让它们装饰好瓦西里·康定斯基三角形的三个斜边,
我不打算再看它们一眼。
2025/2/28
▌被描述的自我
被描述的自我,又被春风吹散,
并没有在春天里发芽,无论是雪花,无论是玫瑰。
这是二月最后的一天,
有一个女生和我在餐厅里一起吃早餐,
不知道为什么,她像我的影子。
请注意,我们聊过的生活,
基本是苟活在生存边缘,没有什么两样,
如此,看透人生的车站。
听着,在我正午散步的时候她发来短消息,
告诉我暖阳在为我呈现,
那是旷野上的微光作用于精神事物,
仿佛是世界的盲目征兆,
根据山楂树、海棠果树、杏树的蔓生法则,
让我活在万物之间,
同时,也穿过如此多的形态,
在让我以诗回信,我是一个孤独的意象之和,
熟悉意象的萌生与缘起,
却依然是一个单数。
2025/2/28
▌给时间改一个名字
而今,乌鸦的叫声带着乌克兰的口音,
落在了莫斯科广场上,
那是人间失格的信号,
在要求狐狸和猎人友好相处,并不打算埋葬谁?
实际上,莫斯科广场并非是椭圆形的,
被一种红色在十分钟之内挤爆,
那么像商人的睡眠,
在一个椭圆形的会议室里被吵醒,
突然,冒出吵架的味道。
那么像语言世界在给人泼冷水,
而两个椭圆形并不等于一滴眼泪,
使我陷入沉思,那么知识分子的无奈,
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进入诗歌,给时间改一个名字。
再把2025年 3月3日当成偶数,
在比对语言的成色,在分辨着乌鸦的口音,
那么像一个没有抱负的诗人,
在以卑微的生命,试图模糊掉语言的边界,
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2025/3/3
▌哦,我正在到来
嗯,我是世界的惊鸿一瞥,
反倒以乌鸦作答:“为渴饮着银河水而来这儿。”
而带着失望的黑色幽默,
已经觉察到我在十指尖上的觉醒,
正在把我的双手变得漆黑,
远不如一个十字架,没有上帝,没有神——
我仍然是孤独的一个人,
头发灰白,脸上已经出现皱褶,
几乎是被填满已知的痛苦,
几乎是没有任何间隙,只有恍惚的内心,
再让疼痛深入骨髓。
忽然,在世界的另外一边出现一个人,
像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影子,
掠过恍惚的一刹那儿,哦,那是另外一个我,
在以时间之水打湿我,在以善之爱封存住一个土陶罐,
不论其中是亡灵,还是野兽,
哦,我正在到来——
2025/3/4
▌我成就我的语法
一场无关痛痒的春风,吹过来就散了,
落在了语言的嘴巴中,
却无法定义风声,也无法定义种子。
别惊讶,闭嘴吧,
要看到被炊烟熏黑的夜,像在春耕之上翻滚的云朵,
正在赞叹劳动的双手胜过于夜,
正在把春风破译成故事。
让我试着理解吧,像偏见从身体里跑出来,
厌倦了自己的额头。
此刻,时间在我的身体里偷偷放进一口大钟,
又在我的额头上雕刻皱纹,
几乎全都是屎上雕花的工作,使我处于焦虑状态——
此刻,我难以控制住抵抗的冲动,
要我善待好这一天,只允许一个意象倾向于一侧,
在给内心的词语松绑,在沉默中听惊雷,
再以悲悯之心释怀,
是啊,我成就我的语法。
2025/3/5
▌而为活着够不上正当理由
意识到时间在减少,正在加入流水,
我很痛心,要把它写成诗,
把恐怖、怜悯和愤怒变成白银,呼应一个时代。
从火烧李开始与一条市郊公路纠缠,
就在人们居住的时间边界,
以十年浩劫描述记忆,包括我的记忆。
咳,那是在寒冷的晨曦中学习的知识,
曾经被厚黑学命名,
比红民村红,被红太阳染红,
仿佛是征服了夜晚的红蜡烛。
当上班的大巴车即将到达合心镇的时候,
我的心情却在拐弯,
确定那些记忆并没有留存,
绕道进入今麦郎街,无疑是一个有效证明。
而奇怪的是我竟然闻到了皮革味,
竟然看见工厂的围墙和栅栏一样又不一样,
那是一座工厂连着一座工厂,像过去的日子仍在蔓延,
像被二手时间剥夺了什么,
而为活着够不上正当理由。
2025/3/6

在这里,我把一首诗蓄满泪水|钟磊:相似之书 (12首)
中国新诗荐读|钟磊诗选30首 (2016~2021)
我总是在拱形的天幕下失眠,看见黑暗在包藏自己
钟磊短诗选 (20首)
钟磊:我有太多的不能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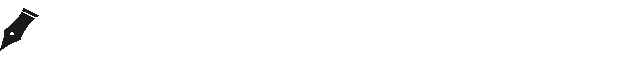
钟磊,独立写诗数十年。著有《钟磊诗选》《信天书》《圣灵之灵》《空城计》《失眠大师》《孤独大师》《意象大师》《活着有毒》等诗集,诗集被郑裕彤东亚图书馆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