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的故事》之二
树下遭责罚
李 皓

快活的日子里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日子的快乐,渐渐长大的吴伯箫,除了每天要按时聆听祖父的谆谆教诲外,其余的时间大都是自由支配。家里的一些小活计,母亲不舍得支使他,总是安排比自己只大几岁的姐姐去干。“女子无才便是德”,在母亲亓氏的心目中,这种老辈人传下来的认知是根深蒂固的。“女孩子将来是要嫁人的,不学会勤快,将来到了婆家会吃不开的。”每当有邻居嬉说亓氏偏向,亓氏总是一边笑着一边这样解释。实际上,姐姐打心里也喜欢自己的这个大弟弟,觉得他天生是个机灵鬼。母亲和姐姐的双重娇惯,再加上二弟吴熙功的出生所带来的忙碌,使得吴伯箫如鱼得水,基本上天天都可以出去与小朋友们一起,在疯玩中尽情地放飞自我。
倒是在小故事村小任教的父亲吴式圣,几次星期天回家小休时,无意中察觉了这个问题。“再让这孩子这么疯下去是不行的!”于是,征得老爷子的同意后,吴式圣把已近上学年龄的吴伯箫带到了大故事(也称尚故事)村小,让他在自己身边当起了“陪读生”。
大故事村地处莱城以东更远处,距吴家花园有十多里路远。初到此地,初入教室,初识那么多小哥哥小姐姐,吴伯箫还处处感到新鲜。可时间长了后,吴伯箫就觉得不好玩了。父亲看出了儿子的这种孤单,便给其介绍了个大朋友——在学校看门打更的尚二叔。
尚二叔是个光棍,也是个打猎的好把式。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他,每当兴致来时,便天南海北地给吴伯箫讲他打猎的故事,听着听着,吴伯箫就入迷了。
可尚二叔毕竟没上过学,更不认得字,肚子里就那么几根簧,久而久之,吴伯箫便觉得腻歪了。
只有每个星期天才能跟父亲回一次家,这是铁律。寄宿在校,起初吴伯箫也不觉得一周的时间有多么长。可腻歪了之后,这漫长的一周就难打发了。这不,一周的时间才刚刚过去四天,吴伯箫就开始想家了,他想爷爷想母亲,也想姐姐和弟弟,更想家中母亲做的好吃的。
小小年纪,吴伯箫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心了。于是,课间休息时他故意撒了个谎,骗尚二叔说父亲让自己回趟家。出了校门之后的吴伯箫,就像挣脱了牢笼束缚的小鸟一般,飞快地朝着吴家花园方向奔去。
当吴伯箫气喘吁吁地站在家门口时,母亲又惊又喜,可当得知他是逃学回来的时,喜悦瞬间又被担忧和无奈取代。
傍晚时分,父亲吴式圣也赶回了家中。撞见正在吃晚饭的吴伯箫,气不打一处来的吴式圣,铁青着脸,一把将坐在小板凳上的吴伯箫薅了起来,像拎小鸡似地提留到了庭院中的石榴树下。
“跪下!”父亲的声音异常严厉。吴伯箫心中一紧,怯怯地望着父亲严肃的面容,缓缓地跪在了石榴树下。
吴式圣站在一旁,目光凝视着吴伯箫,许久才开口说道:“熙成,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在这石榴树下罚跪吗?这棵石榴树,年年开花结果,无论风里雨里,它都坚守在这儿。人也一样,既然选择了一件事,就要有始有终,不能因为一点困难,就轻易放弃。”
吴伯箫低着头,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心里满是懊悔。他知道,自己逃学回家,让父亲失望了。看到儿子似乎明白了事理,父亲接着说:“你想家,这我能理解,但你要明白,求学之路本就充满艰辛,不能一有想家的念头,就当起了逃兵。只有学会克服困难,将来才能有出息。”
吴伯箫咬着嘴唇,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爹,我知道错了,我不该逃学,以后我一定好好上学,不再想家当逃兵。”父亲看着吴伯箫,眼中的严厉渐渐化为一丝欣慰,继而安慰说:“起来吧,知错能改就好,记住今天的教训,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面对。”
在石榴树下的这次罚跪,成为了吴伯箫童年记忆中刻骨铭心的一幕。父亲的教诲,如同石榴树的根须,深深地扎进了吴伯箫的心底,让他懂得了坚持与担当。从那以后,吴伯箫再也没有逃过学,无论求学之路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他都凭借着这份在石榴树下领悟到的坚毅,勇敢地走了下去。

作者简介:
李皓,笔名浩泉,山东平度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毕业,文学学士学位,新闻正高级职称,退休前供职于某地级新闻单位,担任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现社会兼职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副会长、济南市诚信建设促进会副会长、济南市莱芜区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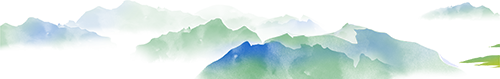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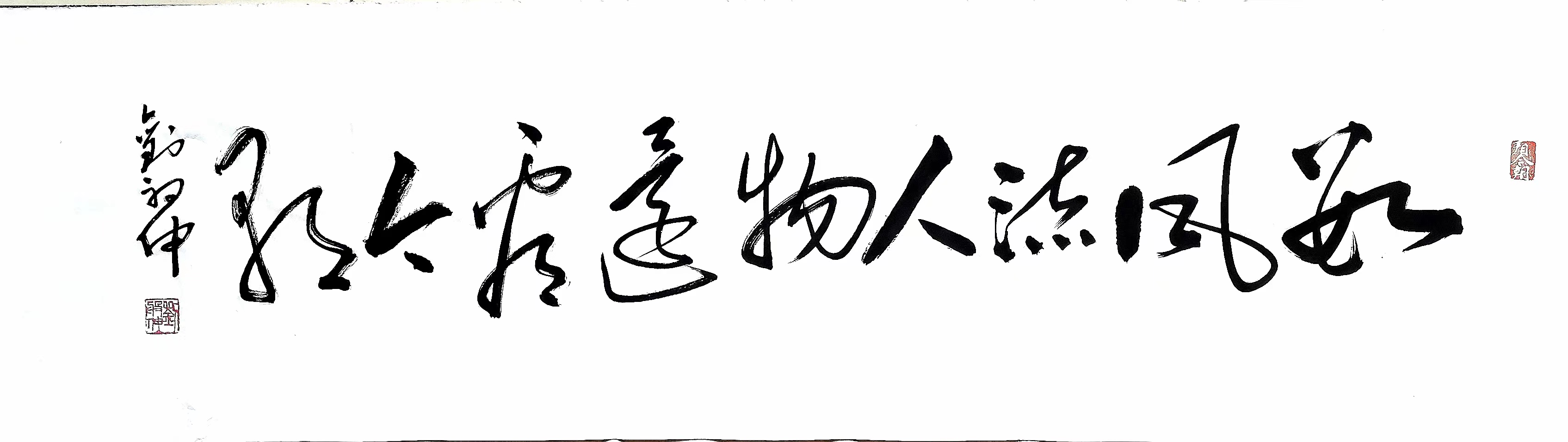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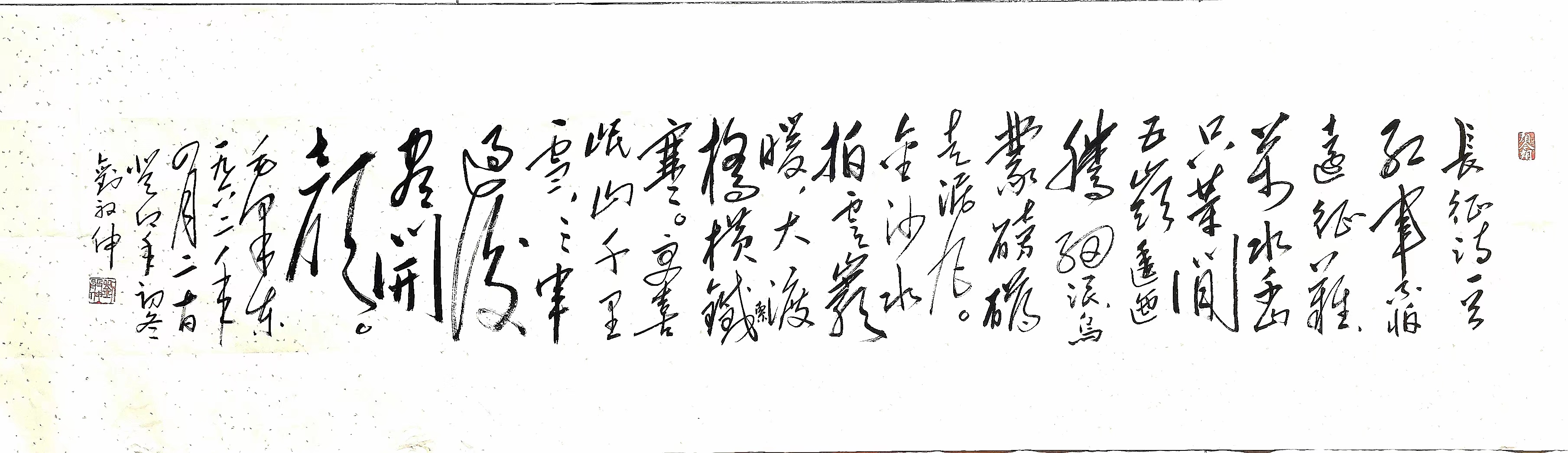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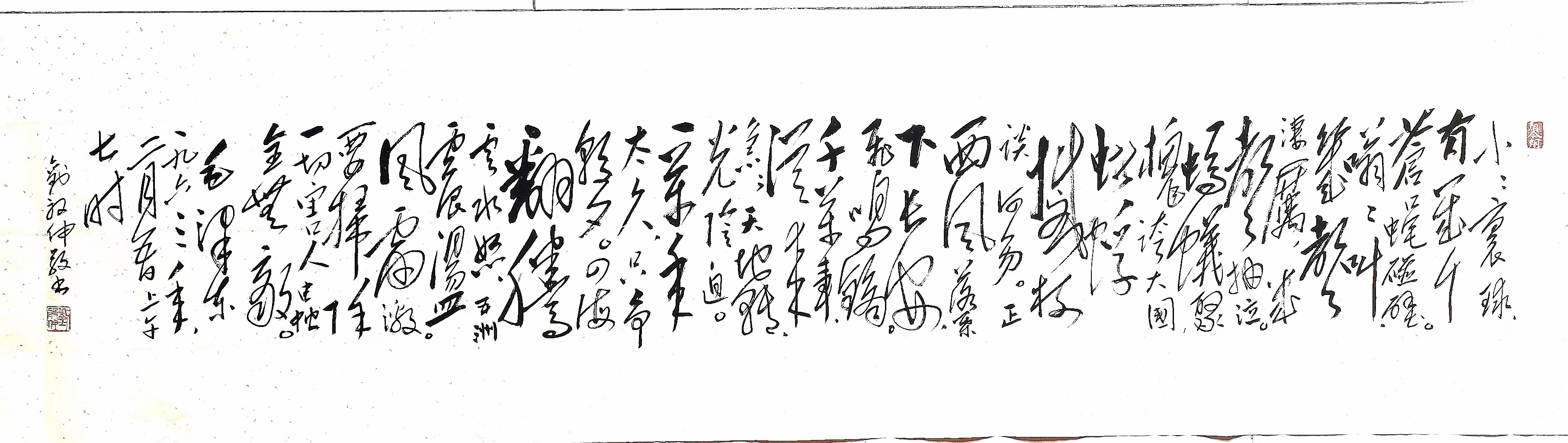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