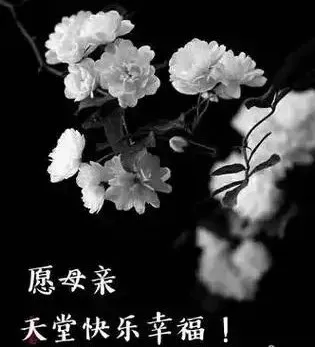
此生有你我真幸福
——忆母亲
文/刘俊巧
我的母亲在2015年去世,有时想写点纪念母亲的文字,可每次提笔便禁不住潸然泪下,悲痛不已,便作罢了。现在正值清明,母亲已去世八年多了,烧纸的路上人们都低着头神色黯然,让我不由得想起“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此情此景何尝不是让人望断天涯路呢?夜晚仰望天空,望着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我想那就是你-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生于1930年,那时正处于饥荒战乱年代,在她十几岁时我的姥爷去世了,两个舅舅都去当兵了,家里只有母亲、年幼的弟弟和体弱多病的姥姥,所以她就早早地挑起家里的重担,农活重活都离不开她,因此练就娘和男孩一样的体质和性格。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在缺吃少穿的苦日子里长大的。
母亲十八岁那年嫁给了我父亲,父亲是过继给别人家的,也是没人疼爱的穷孩子。听母亲讲生我大姐时,家里没得吃,父亲每天就是山药粥和高粱饼子让她做了月子。母亲竟还一口气生了我们姐妹七个,村里人都戏称是七仙女下凡,我排行老六,上边五个姐姐,下边一个妹妹。在那个日子窘迫的年代,父母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女孩而迁怒于我们,反而把我们几个当宝贝一样疼爱。
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母亲坐在灶前拉风箱做饭,我就坐在她前面,母亲拿些易燃的如玉米皮或玉米秸点着,猛拉一阵风箱,等火旺了再填煤屑,填煤块这期间要不停地拉动风箱。在大冬天,灶膛前坐着的我熏得脸身上暖烘烘的。她去擀面时,我时常在后面搂住她腰,脸贴在她的后背上,温暖而又舒服。有时想替她拉拉风箱,但实在是太沉了,拉不了几下就作罢了。现在想想她每天下地干活回来还用这么笨重的风箱做饭该有多累。饭做好了,她往灶膛的火堆里埋几块山药或姐姐们逮回来的蚂蚱,不一会儿,香味扑鼻,成了我们的美食。
晚上煤油灯下,我坐在她盘着的腿上听她讲故事,她的故事可多呢!在她有声有色的故事中我便渐渐入睡了。
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哪有现成的布料做衣服,都是自己织布、裁剪、缝制。母亲将摘下的棉花剥好,再去弹,然后把棉花搓成条,再用纺车纺穗子。在她纺棉花时,我拿上小板凳坐在她面前,随着她拉伸上线我也前俯起身。听着嗡嗡嘤嘤的纺棉花声,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就像听一首欢快的乐曲。
从棉花到织成布,很繁琐的程序,然后再染成各种颜色的布。晚上,在油灯下,母亲给我们做衣服,想一想七个孩子的衣服鞋袜都是她一针一线亲手缝制该是多么的辛苦和不易,但是在她脸上总是洋溢着欣喜与满足。我从未见过她苦恼和发脾气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姐妹几个也大多随她的个性,温和善良。
母亲喜欢唱歌,尤其喜欢京剧。得空了她就唱京剧《沙家浜》《红灯记》里的片断。直到晚年她还时常唱几句,歌喉不亚于当年。我想:母亲假若生在富贵人家,有机会上学读书,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那时村里都不富裕,而她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母亲白天永远是忙碌的,乐此不疲的。有时忙中偷闲地唱几句,我的玩伴经常说:"我要有你这
样的娘就好了。"我们家是村里第一个买的电视机、缝纫机,到了晚上把电视机搬在院子里,街坊邻居都在我家看电视,当时真让我们引以为豪。
我姐妹几个就我上学时间长,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想复读,但那时姐姐们都结婚了,母亲也得了病,没人照顾她,我只好放弃了,为此母亲偷偷哭了,她认为是她耽误了我。
从此我就陪着母亲到处寻医问药,去过好多大医院,最后确诊为颈锥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我娘怕做手术,而我只想让她早日康复就坚持做了,当时医学没现在先进,做了手术病情未好转,反而加重了,同时长达七寸的伤疤永远留在她的后背上。
我们都在长大,而父母在变老。在父亲走后的第四年,母亲得了脑梗,几次住院不但没好转,反而病情发展很快,变得没了意识,不说话,不吃饭,每天都是昏睡。当时我没有想到母亲快离开我们了,还以为母亲只是睡几天,醒来还和以前一样,我真傻。在她离开我们的前一天,已经昏睡了几天的她竟然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想娘最惦念的就是单纯的我吧。2015年9月10日母亲静静地走了,当时我没在她身边,娘啊,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那天我赶到家的时候,她的身体还是温的,我抱起她感觉天塌了,我成了无娘的孩子,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走了,最惦记我的那个人永远地离开了,我感受到了失去最亲的人的那种撕心裂肺般的痛。
我总想着:小时候下雨天那个领着我们上屋顶树底下躲雨避免在屋子里闷热、冬天把我们被子、褥子都在火炉上烤热、大冬天看电影散场了领着我们一路跑回家,让我们在屋地上烤火取暖、我们躺下就有煮熟的山药或萝卜吃的那个人哪去了呢?
过去,母亲在的时候,有不痛快的想不明白的事,都会到她跟前倾诉,她总是开导我把我的心结打开。娘啊,现在想对你诉说的时候只有在夜里仰望星空,最亮的那颗星在对我眨眼睛,娘那是你吗?我感觉一定是你。是你在对我微笑,在安慰我。母亲,此生你在世上陪我长大,结婚生子,我已很幸福,但愿下辈子我们还做母女。

作者简介:
刘俊巧,河北省石家庄人,爱好文学,始终以一颗青春激昂的心去感悟人生,抒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