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民俗与礼乐文明
——从年夜饭说起
胡春雨

有道是“民以食为天”,如果说吃饭是天大的事,那么天底下没有哪顿饭比年夜饭更大。抛开海外暂且不说,至少十四亿中国人围坐在这张饭桌上,在继往开来的日子里吃出了礼序乐和,吃出了家国同构,也就吃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如今伴随春节申遗成功,其影响力不仅超出了固有的中华文化圈,而且渡越重洋走向了全世界,诠释着安顿人类生命的东方智慧。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如何让人们吃好饭,由来是文明发展的大智慧。“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在中国文化史上,自古从朝堂的燕享之礼,到民间的乡饮酒之礼,中国人最擅长用摆在身边的餐桌拉近人的距离,融洽人的感情,构思协和万邦的大文章。从考古发掘来看,早在五帝开辟中华的龙山文化时代,早期中央政权就通过宴会调和各种政治关系,难怪留下了深厚的历史传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当中华先民以虔诚之心献祭天地神明,同样采取供奉祭品的方式,让超越的精神存在与生民的心灵相通。一顿年夜饭,拥有吸引东南西北中国人的“神力”,也就不难理解。至于那个吸引我们的原点,叫做家——男左女右,出生入死,画出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十字架”,安顿着完整的生命,从此生生不息。
这顿饭,一定要吃出仪式感。“仁者,人也,”人之为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在于高贵的文化精神,绝不是让口腹之欲主导人的意义世界。年夜饭一定要从祭祖开始,倘若没有了仪式感的年夜饭,只是停留在舌尖上,那就没有多少生命力了。在中国人看来,生命不仅是有限的存在,更是无限的传承,子孙一定要把还没动筷的美食,敬献逝去的祖先,荀子所谓“志意思慕之情,忠信爱敬之至”,连接起生命之流。生命之树只有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
《礼记》解释其中的道理,“天下之礼,致反始也”,其意义在于“以厚其本也”,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厚重的生命观与价值观——生命总是来自血脉的传承,无非客观世界大化流行的一部分,我之为我,不只是我,不是原子般的存在。于是,“夫祭者,非物自外而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寄托着人的情感活动,承载着人的敬畏之心,集中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特质。在岁月轮回的节点上,春节礼俗承载着丰厚的意义,教育子孙打理好自己的日子。“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蓄也,顺于道不逆于伦”,将核心价值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积蓄美德活出个样来。顺着这条大思路,我们看见,春节在欢天喜地间充满了神圣的仪式感:从送灶王爷上天到迎财神爷来家,将深邃的哲理具象到心灵世界中。用今天的话说,这不见得符合科技理性,但一定符合人文理性,来自人性的温度。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吃什么主要看暂时的境遇,但这个场一定是家。年夜大餐终于在迎来祖先后隆重开场,一家人也许是不远千里重新围坐在一起,回到奔波的原点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生命中最本真的东西。和现在不太一样的是,传统中国社会餐桌上规矩很大,大体是讲求少长有礼、男女有别,在天然差序中实现合理有序,维护家族共同体的生命力。比如座次要讲究,人多了还要分男席女席,至于敬酒的道道就更多了,目的是“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调和生活的不同方面。当然,长辈坐在上首也不是白坐的,免不了要给儿孙们包个大红包;儿孙们也不能白拿,得恭恭敬敬的磕头,相互授受之间把天然伦理梳理整齐,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齐家”吧。形式复杂了一点,有时难免让人心累,因为里面总有放不下的价值,需要人们掂量。
其实人再多、家再大,整个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只是在不同场景演绎出不同的版本。中华文化讲究“一阴一阳之谓道”,从阴阳平衡、和合共生的整体观把握世界的生成演化。因此,“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共同孕育了生命,演化为万有,人类生长其间与生俱来带着天道的基因。在《周易》的智慧里,“夫妇为人伦之始,造万化之端”,男人和他的女人结为夫妇,养儿育女,生生不息,从家庭到社会各种伦理关系次第展开,建构和谐有序的社会。循着这种文化思路,有了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论断,梁漱溟先生断言“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也就顺理成章。所谓家国同构,中华文化里家道之大由此可见,一顿礼敬和美的年夜饭,在无数齐家的实践中“化成天下”。而年夜饭只是个开场,从初一到十五,人们在送往迎来中打理着各方面的关系,让中国社会充满浓厚的人情味,向着新的岁月携手前行。
在先儒看来,“风俗者,天下之大事”,甚至“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历来强调“教化,国家之急务也”。社会风俗与国民精神、时代盛衰相表里,春节礼俗的形成不仅扎根深厚的生活实践,与自古国家治理密不可分,很多礼俗在朝野间腾挪转换。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门神,最初就是来自朝廷的“五祀”,逐渐下沉到民间。比较而言,西方文明依靠宗教维系人心,存在强大的教会组织,可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发展为政教分离原则;而我们的国家建构离不开“政教相维”,历来依靠文化共识凝聚政治共识,例如国家层面的天坛祭祀、宗庙供奉,加上独具功能的士绅阶层,引领着天下风俗与节日礼俗,这是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形态所不具备的。历尽周折,包括弘扬节日文化在内,现代中国正在为更新礼乐文明而努力。
在现代文明的剧烈转型中,源自西方哲学的个人主义伦理、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在中世纪出走时找到的民主科学精神,一百多年来重构着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五四以来国人在反传统的传统上走得很远,中华文化不绝如缕,家族精神濒于瓦解。加上从农耕社会到工业文明的急剧飞跃,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势必波及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礼俗,人们不由发出“年味淡了”的惊呼。
从春节礼俗的历史演变来看,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既需要结合时代条件重新解读其文化内核,也需要根据固有文化基因解读人类共同价值,做到守正创新。譬如,科技理性的发达与祭祀文化的传统真的冲突吗?人的平等自由就意味着泯灭人的天然差别吗?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不能凭着简单的信条一条路走到黑,恐怕要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才能筛选出较为成熟的答案,重构在国风民俗之中。
好在文化生命总是在成长中开枝散叶,在时光中新陈代谢,春节文化原本扎根于生活的热土。现代文明及其技术成果,让春节拥有了更新颖的内容,让国人拥有了更丰富的选项。譬如年夜饭上,就增加了一道文艺大餐:春节联欢晚会,在国人的嬉笑怒骂中一路走来,伴随着时代的成长。
据说古老的年戏是春晚的前身之一,那时候没有电视等现代传播工具,人们以各种热烈的文化娱乐活动,让春节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狂欢节。至今记得小时候走街串巷的踩高跷,锣鼓喧天的扭秧歌,像什么划旱船、舞狮子,那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人想起二千多年前孔子师徒说的“举国若狂”。如今一台春晚,让人们在餐桌上走进中国文艺的最高殿堂,在创新转化中回归中华文化底色:它可能是莺鸣百啭的戏曲,可能是令人捧腹的相声,可能是抒发诚挚的深情,可能是鼓舞奋斗的豪情。从剧目到舞美,从内容到妆容,让国人在美轮美奂的视听盛宴中,沉浸中国美、沐浴中国风、焕发中国情。
然而这一切,只是一个乐字,将礼敬消融于和乐之中。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所必不免也”,礼乐文明之乐无非欢乐之乐,根于人类天性,它可以“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以丰富的艺术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究其本质,程子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其根本意义“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贵在以形式之美承载精神之善,陶冶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华文化的终极追求在此岸不在彼岸,人心和顺、社会和睦、世界和平,便是最美的乐章,便是人间的乐土。
黄帝四七廿二年正月初十思农于山左鹊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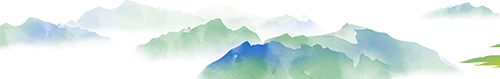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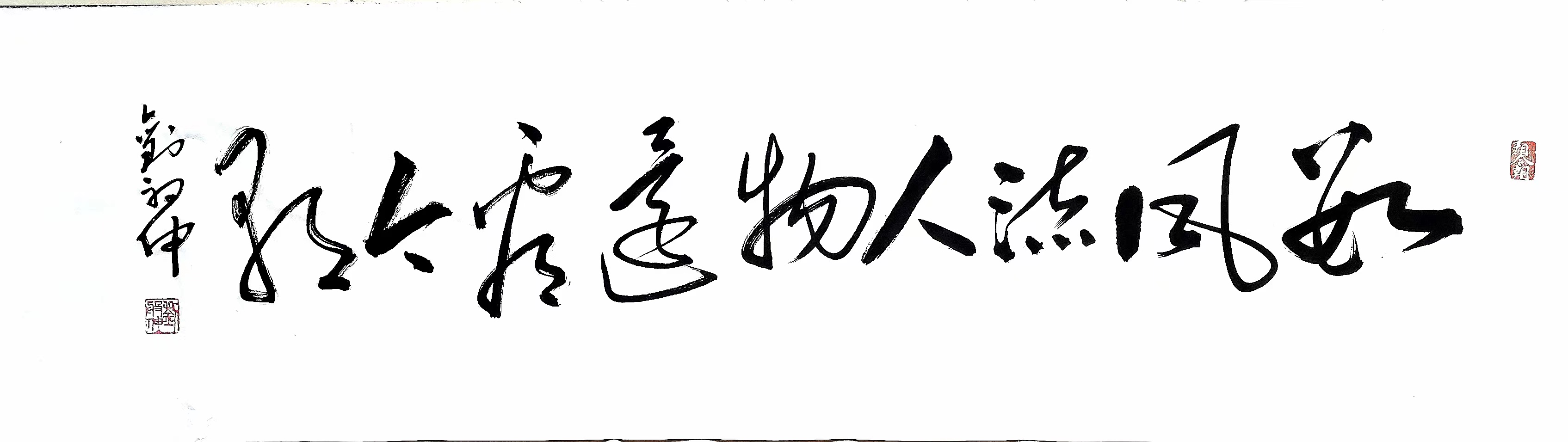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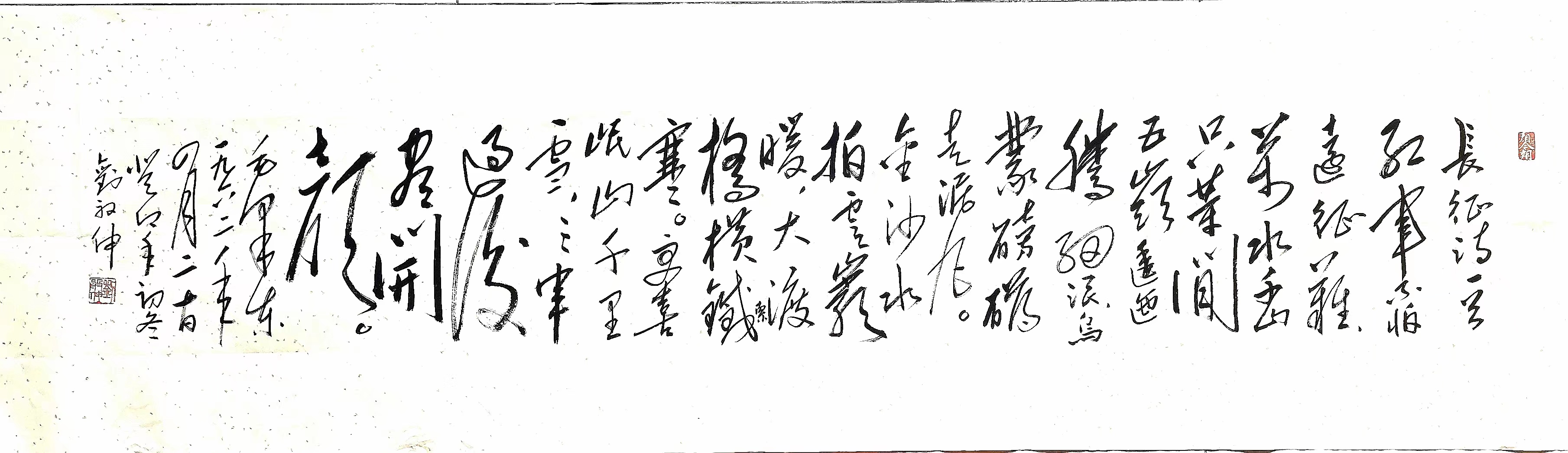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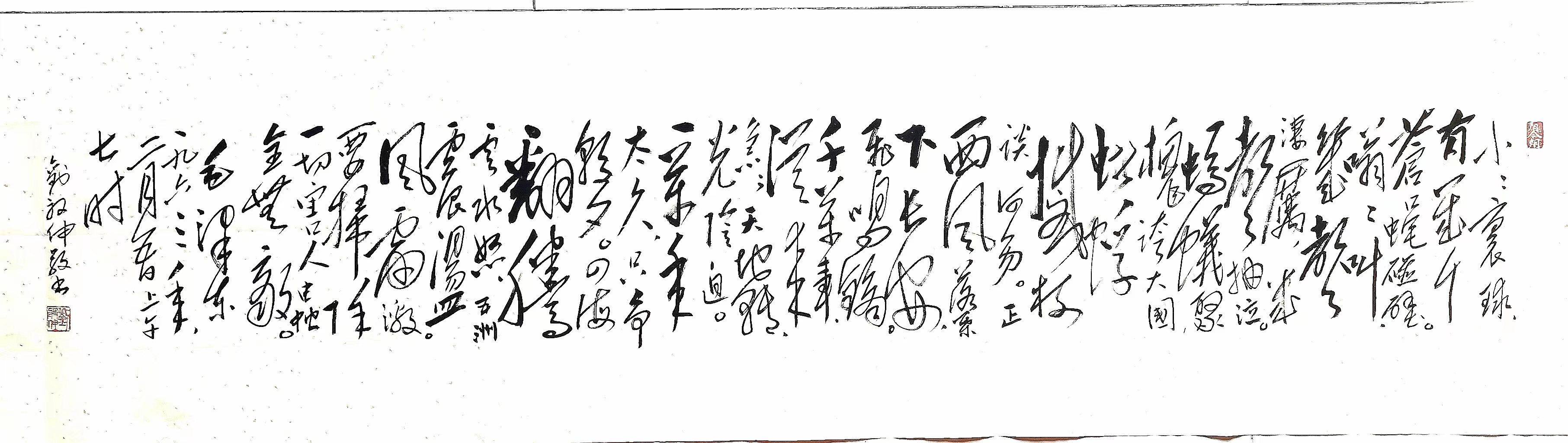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