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金銮殿”
宋文东
金銮殿是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俗称。太和殿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名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名皇极殿,直至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改为今名,是皇帝登基和举行大典的地方。太和殿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宫殿,也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三大殿之一。但我们今天要去爬的“金銮殿”不是太和殿,而是济南南山的一座叫作“金銮殿”的山。
12月8日8点,我们20位驴友拼车,从分水岭出发,直奔仲宫稻池村。半个小时后,我们的车队顺利抵达。在稻池村路边的水沟里,厚厚的冰层用登山杖都戳不破。书亭说,这里的气温有零下3°到4°,比济南市区至少低2°。我知道南山的夏天气温一直比市区低几度,因此冬天比市区冷一点也不奇怪。
众驴出了村子,沿着山峪里的一条大致南北走向的水泥路,渐渐入山。这时阳光普照山峪的西侧——牛鼻子山,那里金晃晃的一大片,煞是耀眼。而我们行走的山峪底却一点阳光也见不到,我虽然戴着半截子手套,手却仍然被冻得冰凉。牛鼻子山半山坡上有几座房屋,金灿灿的阳光洒在玻璃上反射出耀目的光芒,给人以温暖的感觉。自由哥玩笑道,我们这是图个啥,这么冷的天还出来爬山,不是自己找罪受吗?我说,村民也笑话我们是吃饱了撑的。众驴说说笑笑间徒步了20几分钟,大约有2公里的山峪公路,就到了露水岭的后山脚下。这时我感觉身上已经热乎乎的了,不像刚进山峪时那么冷了。好梦等几位驴友已经在脱外套,开始做爬山的准备。

我们开始爬山时已经9点了。这时阳光还照射不到露水岭的后山上,因此那阴影里的灌木上都还挂着一层银霜,玉树琼枝一般,也是冬日里的一道美景,煞是秀丽。

不觉间,辰桑与老丁俩已经率先登上了半山坡旁边的一处高高的山岬上。辰桑张开喉咙像老虎发威一般地吼了几声。群里的驴友都称他这独特的吼声为“辰桑叫”。那短促浑厚带点拖腔的声音响彻山谷,也督促着众驴奋勇向上攀登。

我们去年冬天曾经从这条驴道下过山。那次经过这座山岬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山岬之峻美,这次我爬到那处小垭口上,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山岬顶部。站在悬崖边上,只见山峪两侧半边阴暗,半边光明,那太阳光所到之处,黄草们、山岩们都金光灿灿的,那些柏林也像进入了冬眠季,绿得更为深沉,呈现出一种和谐的冬日之美。


接近山顶处,有座完好无损的石屋,是牧羊人建的遮挡风雨的地方。看那沧桑的样子至少也得有四五十年的房龄了吧,但依然坚固如初。在南山上,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石屋,不过多数的已经坍塌,或者残破不整,完好的已经不多见了。绿叶美女让我给她拍一张与石屋的合照,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她。

登上露水岭,远眺西北方向的济南城,虽然见不到高楼大厦,但在那遥远的天边上,一绺铅灰色的雾霾笼罩着城市的上空清晰可见。我们平时在城里大多感觉不到,但是当你站在数十公里之外的南山上就看得明明白白了。慢吞吞的蜗牛说,我们现在感觉济南冬天的雾霾天气比过去少多了,空气也不错了,但如果跟这这山上比就差得远了。看来我们每周来山上透透气就对了。

再眺东北方向,我们济南市民在南山的两个大水缸之一——锦绣川水库可见大半个库容。每当看到那一泓碧波在群山的怀抱里荡漾,我心里便顿时生出一种美美的情愫来。也不仅仅是视野里的湖光山色那般醉人的缘故,而是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暗含其中。尤其是今年,锦绣川和卧虎山两个大“水缸”都灌得满满的,我就觉得在南山上行走也有了充足的底气似的。这大概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一个理儿吧。

众驴都登上露水岭之后,穿过漫漫的黄草甸子,走到山岭的东南角山崖边上。只见最近处有座尖尖的高峰矗立在眼前,根据见过的图片,我判断这就是“金銮殿”三峰之西峰。但看那尖削的山峰,比上周我们刚刚攀登过的火龙寨还要险峻几分,我心里却一点底也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驴道可以登顶,但如果有的话,我可就作难了。下视脚下的山崖,见一条蜿蜒的驴道清晰地通往“金銮殿”西峰那里去了。众驴便沿着驴道慢慢下山,往那山峰渐渐地靠拢。
众驴爬上“金銮殿”半山腰,果然没有往山顶去的路了,我才松了一口气。细看山坡,近乎直立,陡峭如削,如果强行往上攀爬,不仅艰难,而且十分危险。我向来不赞成盲目地冒险,前面带路的驴友也自觉地沿着驴道绕往阳坡去了。

山腰间石壁直立,下面有个扁长的深不过一两米的浅洞,显然这是大自然多年风化的杰作。站在巨岩下面,给人一种颇为压抑的感觉。洞下面好像有驴友在此休憩过或者用过餐的痕迹。但我没有在此停留,逃也似地直接穿洞前而过。往前去的驴道比较狭窄,就在悬崖边上,我探身窥视,一眼难见谷底,令人汗毛直竖。好在悬崖边上有许多的灌木荆棘,给人以很大的安慰感。

众驴穿过石洞,上到“金銮殿”东西峰之间的一处垭口上,稍稍歇息,再往“金銮殿”东峰开始登攀。说起“金銮殿”之名,它们共有一组三峰,三峰相距很近,大致呈品字形排列,因远眺三座山峰都为馒头状,顶部较为圆满,阳光照在上面,像金銮殿一般熠熠生辉,故名。



东峰虽然也较为陡峭,但有条小路往山顶而去。驴友们登山都有个普遍的心理,别人敢上,我就敢上。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众驴手脚并用,依次登上山巅。
山顶上东西较长,南北稍短,但面积不大,估计站满20个人就会拥挤不堪。站在山巅,南眺群山,晶蓝的天幕下,淡淡的雾烟里,那层峦叠嶂,逶迤山势,像一幅水墨画似的迷人。近处层层的梯田里,黄草连绵,有几棵挂着黄柿子的树立在地边堰头分外醒目,呈现出一派冬日荒凉的景象。尤其是山下那一座座烟村静静地卧在山坳里,白杠似的弯弯村路把它们与外界联系了起来,令人看一眼都感觉是那么地亲切和放松。

也许是觉得山峰上过于狭窄、陡峻的缘故吧,我只是在山峰上逗留了一会儿,就赶紧给别的驴友腾地方。我前面的高哥、绿叶和琴姐已经开始下山了。我赶上他们,大家一起下到东、南峰之间的垭口上。见驴道并没有通往南峰上面去,而是拐个弯儿往东北方向的柏林里去了,我判断登峰的驴友不会太多。细瞅一眼南峰,我觉得它比前二峰要矮一点,北坡也较为和缓,登上去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却为什么上去的人少呢?其实驴友就是一种奇怪的群体,在野外,越是容易抵达的地方,他们到的却少,而越是那些艰险之处,驴友倒是趋之若鹜了。我向来对大自然都是抱着敬畏之心,我们今天也并不是瞧不上南峰,而是为了保存体力,再说南峰也不是必经之地,所以我们没有攀爬,因为前面还有多个山头尚在等待着我们呢。这时大部分的驴友都从东峰上下来了,众驴沿着驴道往东北方向的垭口缓缓而去。

我们爬上八里峪正南面的山顶上,远远地看见一蓝一红着装的两位驴友正在东北面一处山脊上休憩。二人一站一蹲,其中那位蹲者似乎在挖什么东西。到了近前,我才看清了蹲者是位中年女性。我问道,大姐这是在挖什么呢?男的抢着说,挖地耳。我听说过地耳,虽然经常在山上行走,却一直不认识,对不上号。山坡上的地皮都是黑乎乎的,那女驴友手里拿的地耳比较小,也看不大清楚什么样子。书亭找找身边山坡上的地耳对我说,这就是。我见地耳黑乎乎的一团一团的,样子十分难看。书亭说,这东西也叫地衣,还有好几个别名呢。你可不要小看它,这东西的钙、磷、铁、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高,尤其是蛋白质的含量能超过鸡蛋呢。打汤、凉拌、炖排骨都是难得的美食。另外还有治疗烫伤等方面的药用价值呢。

作别两位驴友,我们继续爬山。过了几座小山头,下到了去往八里峪的垭口上。这时已经12点了,好梦召集众驴在垭口上合影留念。

合完影,众驴开始下山。在路边的山林里,我又发现一种似曾相识的红豆,仔细看看,却不认识。冬季的南山上常见的红豆多为南蛇藤豆,但南蛇藤豆有个金黄的外壳,很容易辨认。这个却没有黄外壳,显然不是南蛇藤豆。也不是忍冬,忍冬豆似乎更红更小一点,树干竖向的白纹理格外清楚,更容易辨认。书亭已经走远了,我身边也没别的驴友可以请教,便查《形色》,竟然没有结果,也就罢了。回家后忽然想起一位研究林业的专家朋友,何不向他请教呢?专家朋友告诉我,这是扁担杠子,俗称孩儿拳。今日又在南山认识了一种红豆家族的成员,也算一大收获吧。

下到山根,经过那座木棚子山门,就进入了八里峪。远看八里峪西山,也就是露水岭东北面的那座山,有一段山体颇像一把巨大的太师椅似的,那靠背、扶手栩栩如生。驴友老头哥道,这山名就叫椅子山。

我在10多年前就知道八里峪了,也从这里走过多次,算是比较熟悉的一条驴行线路。据当地人说,八里峪从南到北有八里远,所以老辈人就起了这么个地名。我不以为然。虽然八里峪走起来觉得不近,其实根本就没有八里地,估计最多也就二三公里远吧。老百姓起地名,也喜欢个吉利数字,我想他们就把“八”用到这里了吧?也别太当真。
(本文照片借用了部分同行驴友的摄影作品,在此致谢!)
2024年12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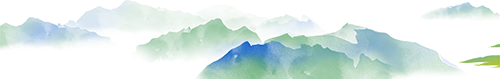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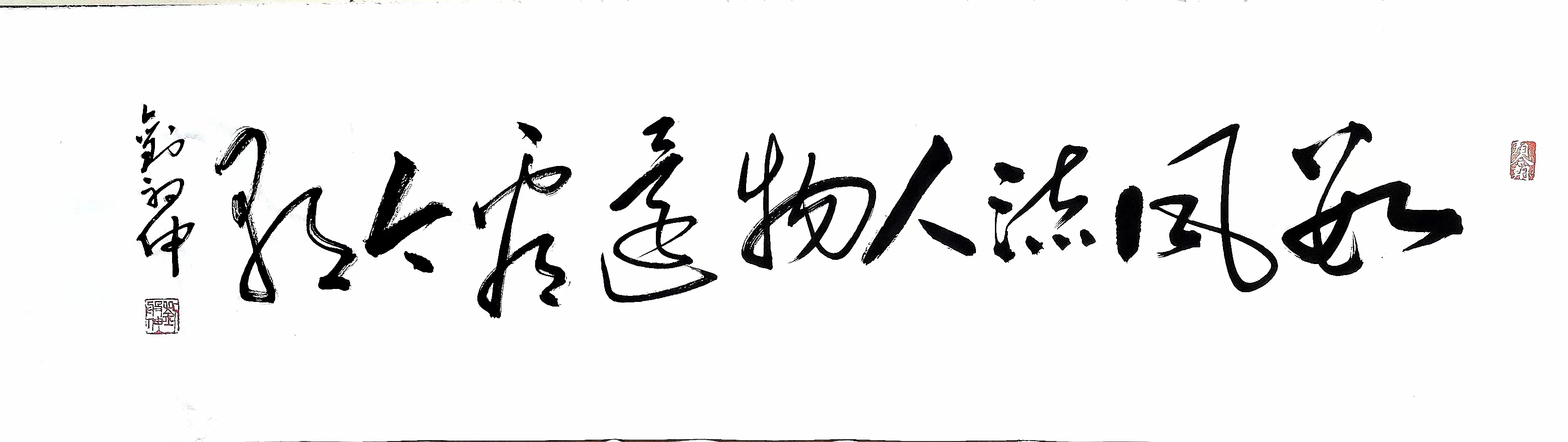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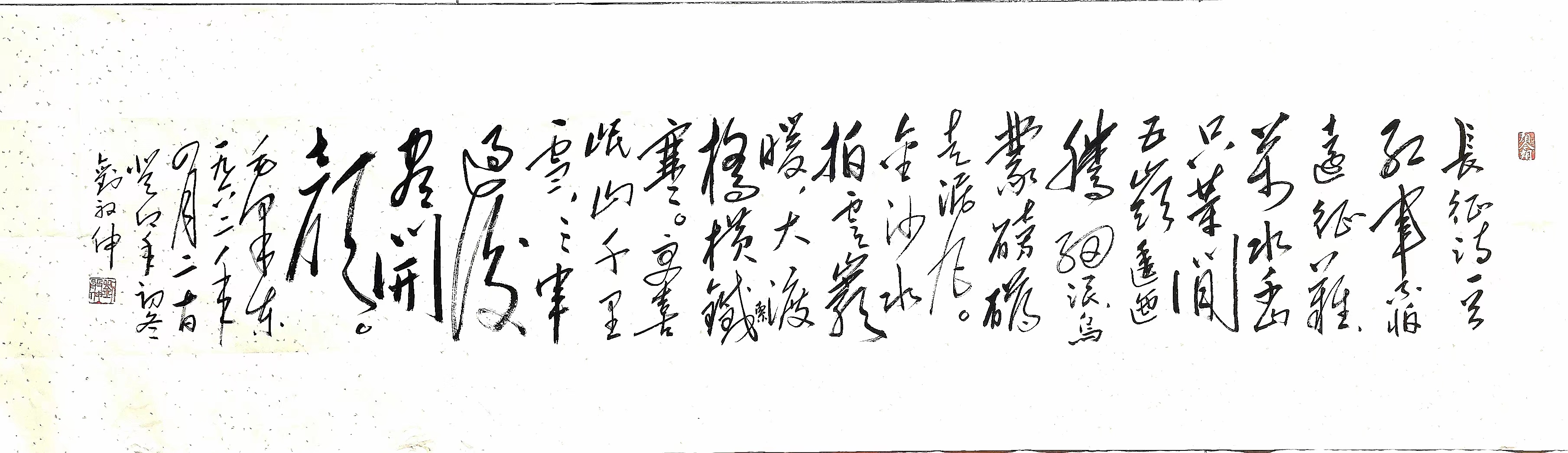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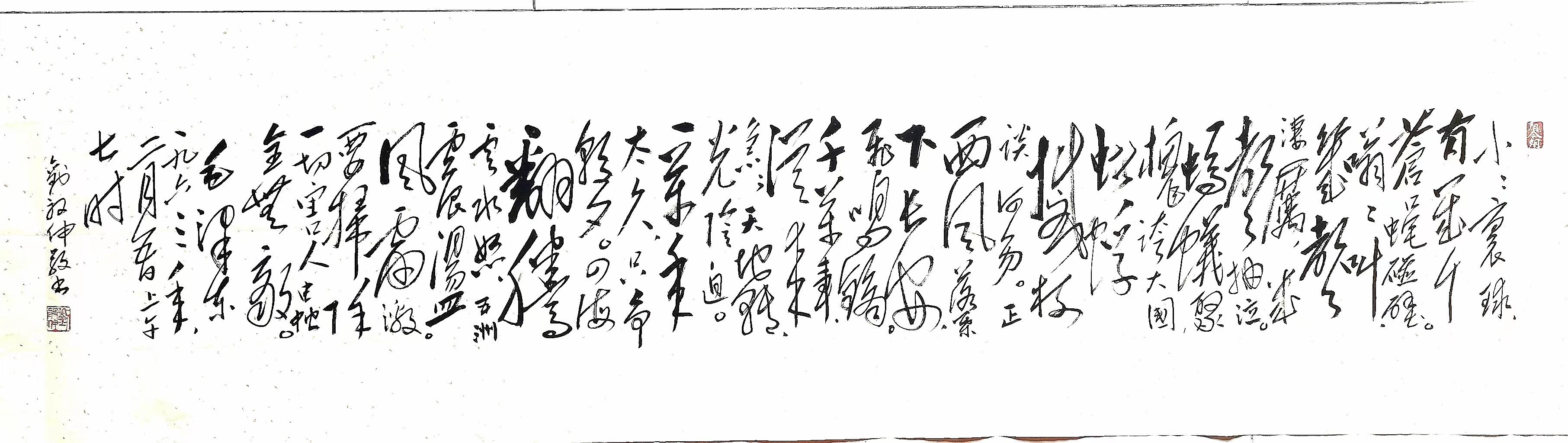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