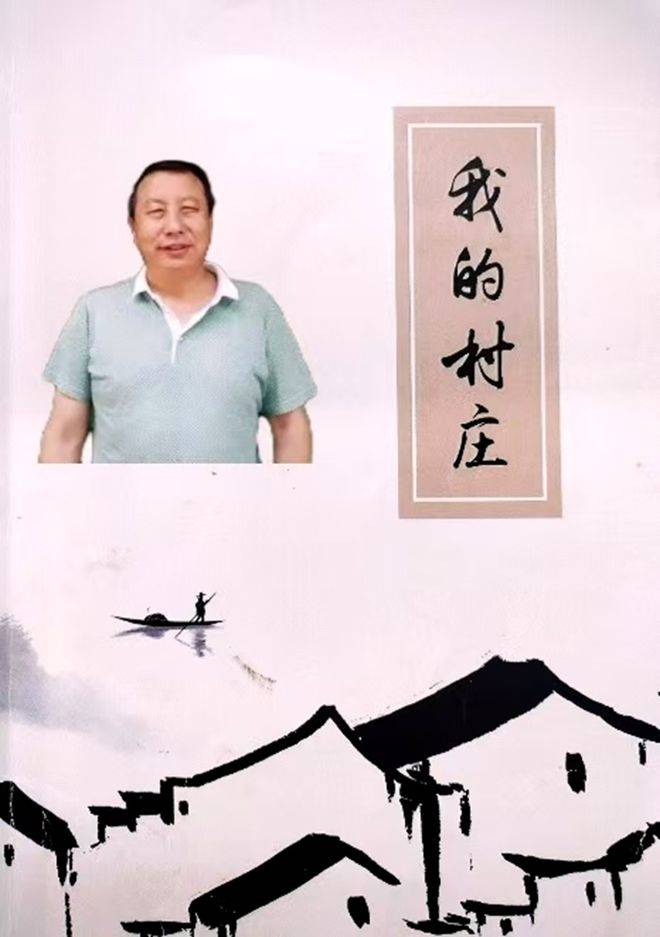
第五十章 老人与狗

一年一度的送温暖活动,一年一度的优秀分子的表彰会照常进行。过了年,正杰驻村将近三年,按文件规定,该换岗了。王局长参加村里的表彰会,有点心不在焉,开会中间就起了身,瞅着正杰摆摆手,两人来到住室。
“咱弟兄两个工作交点底。年后,旅游局要合到文广新局,大盘已定,人事调整还未完全到位,但也有点眉目。我调到其他局,你这几年扶贫成绩有目共睹,过渡到文广新旅局,是副局长,估计扶贫一回去,就退居二线了。十分怀念和伙计们共事的时光,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回去了,好好排,我还有事,得赶紧回。我走了,一会儿跟伙计们说一声。”
大年初一,吃过饺子,回村看望父亲。服侍父亲坐在椅上,母亲端来热腾腾的饺子,正杰接过来,喂父亲吃。
刚吃完,他的手机响了。
“傅局长,我是杨大山。新年好!新年好!几个伙计都在我这儿,大家聚聚,你快过来,OK了。”
杨大山是文广新局局长,刚从乡镇党委书记调过来,四十出头,工作上风风火火。正杰和杨大山没有任何交集,杨的一些情况他都是听别人说的。
看父亲,弟弟开车和他一块去的。弟弟把他送到祥瑞小区的门口,正杰按杨大山说的地址,边走边问,来到8号楼西门洞三楼东门门前,听到里面人语喧哗。门是虚掩的,他轻轻一推,浓重烟气酒味扑面直冲过来。
“贵客,贵客,驻村第一书记,傅书记……傅局长,请坐。”杨大山拉把椅子,让正杰坐在身边。他让人加双筷子、一个茶杯、一个酒杯。他斟了三杯让正杰喝,说是入场酒。两个副局长和办公室主任,脸上泛红,都说要给正杰敬酒。
杨大山说:“酒不能喝老猛,叫傅局给大家一人碰一杯!”
“一人两杯,两条腿好走路。”办公室主任老田说。
杨大山没吭声,其他三人都说好。
又是八杯酒下肚,正杰脸也红了。
老田说:“傅局来电显示真快。”
“伙计们先喝着,我和傅局说点事。”
他俩进了邻着厨房的小厅,杨大山沏了两杯茶。
“三年扶贫人员一轮岗,我这也够了,一过年就回来了。局里得提前安排人。”正杰说。
“我正想说这事。我刚到局里,事是千头万绪,也希望你回来,助我一臂之力。但叫谁去顶住你的工作,确实没有合适人选。我当书记时,去沟庙村参观过扶贫工作,你的工作扎实,老百姓口碑好……我希望再干一段……顶多一年吧!”
“主要是身体。对那里的老百姓有了感情,真心想为他们干点事。”
“谢谢老兄,我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初几上班?”
“初六。实际我初五都去了,欢送外出打工的。”
初五,送外出务工人员,面包车跑了四趟。
初六早上,一个老婆婆慌慌张张来找张医生,说老雷头恐怕不行了。张医生拿起药箱一路小跑出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回来了,说老雷头走了,正杰走到院门口,几个老婆婆在说老雷头,都说一个好人走了,还是两个月里走了两口。
正杰问:“老雷就一个人,咋是两口人?”一个老婆婆说:“他家那个小黑狗,也算一口人,我给你说道说道。我和老雷头是邻居,啥事我最清楚。”
十二年前,老雷头六十刚出头,腰板直直,头发白了一半。他养成一个习惯,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到村子里转悠。那年冬天冷呀,房檐下挂着长长的冻隆锥,人哈出的都是白气。
老雷头在村里转了一圈,没见一个人影。天麻麻亮了,当他走到村口一堆柴草下,猛地看到一处柴草在抖动。他一扒拉,一只小土狗露出来了,顶门上有撮白毛,其它通通都是黑的,两只小眼就像两颗黑葡萄。

他寻思着:赖好是条命,不能眼睁睁地看它被冻死。小狗估摸有一个多月大,冻得浑身簌簌发抖。老雪头解开棉袄,抓起小狗,塞进祆里,一只手在下面托着,一只手拉着祆,外面只露个狗头,肚子鼓鼓的,像个怀身婆娘。
老雷头赶紧把小狗抱回家,用小褥子把它裹得严严实实,在旁边笼了一堆火。小狗渐渐有了力气,慢慢从褥子里挣扎着出来,摇摇晃晃。老雷头把它托在掌上,小狗舔着他的手,老雷头说痒痒的感觉真好。他到村里的代销店里,买了牛奶、火腿肠,把牛奶包剪个口,倒进小碗里,把火腿肠揉碎撒在牛奶上。他把碗儿放在小狗的面前,它闻了闻,用粉嫩的舌头卷着喝。
他就像得了儿子,在床头铺上稻草,造个狗窝。这个家伙高兴地在此安了家。它吃了睡,睡了吃,胖了,小短腿难以撑起快要挨着地面的滚圆肚子,特别是一下台阶,身子乱翻个,可逗人了。
每天早上,小狗扒着稻草叽咛叽咛地叫着,老雷头意识到狗儿要排东西了。他抱起小狗,放到柴禾堆后,它开始翘腿尿尿,拱腰拉屎。一个月过去了,小狗在屋里四处乱嗅,撕咬着老雷头的臭袜子,在院里转圈撒尿,宣告这里是自己的领地。门口有人路过,他开始吠几下,很嫩很嫩的叫声。
人命名,狗也得有个名。小狗基本上通体黑,叫黑狗吧,没亲切感,就叫它“小黑”吧。小黑,小黑,叫时间长了,老雷头一叫,它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它最喜欢在老雷脚下打滚,或撑起四条腿儿,伸懒腰。
一日,隔壁刘老汉还没进门,小黑扑上去,狂叫不停。老雷头喝斥之后,小黑退到了一边。
“这狗叫啥名?”老汉问。
“小黑。”
“现在养狗,要办理养狗证。”
“我是拾的狗,流浪狗。不知咋办?”
“我给你问问。老雷头你这一辈爱小孩子,爱小猫小狗。你一个人,不会孤独的。咱们一茬一茬娃儿,叫你舅,时间长了,你成了“官舅”。咱这儿,叫舅本身有个损人的味道。给谁叫舅,自己的长辈睡了他的姐姐和妹妹。“娘亲舅大”,对你是亲啊!”
老雷头傻傻地笑。
老雷和小黑几乎形影不离。他去哪儿,小黑就跟到哪儿,去地里干活,小黑绕前跑后,或扒拉着荒草,或撒尿作记号,很忙的样子。到饭店吃饭,小黑老实地卧在桌下,眼巴巴地看着他的嘴,特别是他吃东西的时候。晚上,小黑成了最忠诚的保安,一有风吹草动,就汪汪叫着报信。
正杰记得,入户时,老雷头对正杰说,世上万物都有灵性。小黑成了朋友,成了家庭的一员。狗比人强,你对它好,它永远记着,从来不会跟你翻脸,你赶都赶不走。
你看我这个小板凳坐了几十年,还很牢固,漆明发亮,为什么?我坐时,周周正正,凳子很舒服。凳子一有点小毛病,我就及时修修补补……别家和我同时做的板凳,早坏完了,烧了。
他说,我是光棍一根,屁也不是,但我知道,我对别人好,别人对我不会差的。谁家有事,我都愿意出力帮忙,农忙时,地里场里,起屋造房,红白大事……凡能帮上忙的事我肯定做。特别喜欢带孩子,一院子孩子,热热闹闹。
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花果山上的齐天大圣。小黑被孩子们宠着,喂它吃这吃那,都爱摸他黑绸缎似的毛毛,它跑来跑去,上竖的大尾巴摇得欢。
老雷头坐着眯着眼打盹,小黑就趴在脚边,眯着眼瞌睡。老雷头醒了,喝斥一声,小黑连忙打滚,小黑喜欢用屁股蹭他的腿。小黑遇到了小黄、小白等族类,都喜欢先对对嘴,而后闻闻屁,看来狗往屁走,还是有道理的。
有次,夜里老雷头突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他一看,老年机欠费停机。第二天早上他难以起床。这可把小黑急坏了,它用嘴扯掉了顶门杠,见了路过的邻居,咬着裤角往院里拉。邻居进屋一看,老雷头正在床上呻吟,赶紧唤来人把他送到村卫生室。
小黑也有落魄的时候。有回,它被村里的两个大狗围攻,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回来,额头上被扯掉一块皮,露出红肉。老雷头心疼得直掉眼泪,他拿来紫药水,小黑一见他就躲进了柴禾棚里,舔着腿上的伤口。他眼含热泪对小黑说,你和我一样,都是穷命,就是别人说的那样,推着小车上台阶——一步一个坎呀!我有病,你找人;你有病,我照顾。唉!你快好起来!一会儿我去煮排骨,拆牛奶包。
随着时光流逝,老雷头真的成了老雷头,头发完全白了,满脸褶子皮,背弯成了一张弓。小黑也成了老黑,狗毛变得稀疏、暗淡,灰白色头皮显露出来;眼睛浑浊,淌着红液,引来了苍蝇。腿脚也不麻利,过个小坎都颤颤惊惊。
黄昏时分,老雷头在路上走着,小黑仍跟着,一个步履蹒跚,一个走得踉跄。无情的落叶簌然而下,飘落到很远的地方。
一天,小黑独自出了门,它是后半身子拖着地,拱着头,几乎用前肢力量爬着前行,老雷头很心疼,想上前帮助它,小黑怒吼着拒绝,这是罕见的。
老雷头看着它艰难地下了大坡,走进沟里。他赶紧赶过去,看到小黑侧卧在枯草丛中,嘴张得老大,肚皮剧烈地起伏着。“小黑,小黒。”老雷头叫着,小黑睁开眼睛,看着他,显得十分疲惫,眼里明显有液体流出来。过了几分钟,小黑闭上了眼睛,一切都平静下来。
在一髙崖下,老雷挖了一个洞穴。他把小黑送进去,放置牛奶、火腿肠,和泥把洞口封好。回到家,他精神状态很差,一天呆呆坐着,无心吃东西,夜里还失眠。别人看来就是死了一条狗,但对他来说,无疑失去了一位亲人。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翟柏坡,微信名般若,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教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思客》签约作者。百余篇作品见于《奔流》《牡丹》《洛阳日报》和微信平台,文集《我爱我土》由中国文化出版社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