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游赵岭、三王峪
宋文东
11月3日,距立冬还有几天,我与驴友们游览了章丘赵岭、三王峪,算是跟今年的红叶季作个别。
那天7点20分,众驴友拼车从燕山立交桥东出发。15公里后,抵达港沟高速公路收费站;再行25公里,到曹范,下高速;又跑20公里村路和盘山公路,于8点40分抵达赵岭村。也是奇怪,我们曾经几次从港沟到彩石或者埠村下高速公路,凡是用ETC的,都不收费,而在曹范下高速公路,比埠村离济南还近点,却要收费,虽然仅有几块钱,却让人难以理解。
赵岭村头上有一堵墙,上面写了“赵岭村”几个黑体大字,可见这个赵岭村才是正确的村名。驴友们在路上还争论究竟是赵家岭对,还是赵岭对,其实这俩村名都没错,以前赵岭村就叫赵家岭。现在高德地图上搜出来的赵岭村在章丘,而赵家岭则在莱芜了。我们的车到了赵岭后,我往驴友群里发了导航地址。我见驴友小手给我发的微信,说他们的车导航去了莱芜方向,不过已经掉头回来了。因此他们的车晚到了10几分钟。
一般的村庄多是建在平原上,或者山谷里,也有的建在小山包上。而赵岭村却是建于高山之上,像个悬崖村,比较少见。我们是沿着盘山公路进入村庄的。我就想不明白,在没有村村通公路之前,这个村庄的先人怎么会选择这个与世隔绝的大山上建村子呢?现在虽然通了公路,但是公路修得比较狭窄,两辆小车会车都比较困难,如果遇到大车就更麻烦了。好在我们运气好,一路顺利地进入了村子。
村口停车场边上有盘石磨和一盘碾。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见了感到很亲切。我知道石磨有磨面粉的干磨和磨豆浆的湿磨之分,这盘磨像是磨豆浆的湿磨,做小豆腐用的,也可以磨虾酱。我小的时候,乡下生活比较艰苦,我母亲经常磨豆浆做小豆腐给家人改善生活。

在村的东南角也有一处停车场,我们去年来赵岭就是在此偶遇的美女驴友么么2,从此以后,么么2就成了我们驴友群的常客了。可惜这次么么2家里有事,没有来。众驴从停车场西边拐了一道弯,向村外南面的山脊而去。去年来,我们曾在悬崖边一户人家门口遇到过一位94岁的老翁,老人还背着一小捆柴火,看了让人无语。今次来,大家希望能再次偶遇老人。又拐了个弯儿,猛然见到高处一堵墙下站着一位老翁,有点像去年遇到的那位老寿星,众驴有点喜出望外,真是缘分呀。好梦怕认错了人,便问,大爷高寿了?老人耳朵有点背,没理会。好梦又问了一遍,老人才说95了。好梦说,去年94岁,今年95,就对了。见老人精神状态比去年还好,一点也不像90多岁的样子,大家很高兴。今年君哥没有来,好梦与豌豆花一起与老人合个影,作为纪念。

出了村子,有村民在山地里种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蔬菜,我还怀疑这从哪里引水来浇地呢?抬眼见高处有一个不大的水泥建的蓄水池,里面还存有少量的水,大概是存储的雨水吧?一对老年夫妇正在菜地里劳动,他们种的章丘大葱长势很好。也是一方水土长一种植物,章丘大葱很有名气,这里虽然不是章丘大葱的正宗产地,但大葱长在这山上也比其他地方的长得高。见到我们,夫妇俩友善地给我们指路说,山顶上有条大路,好走一点。但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一伙专走野路驴道的驴友,不过夫妇俩的好意我们领情。山里人的古朴心肠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小路是在梯田里走出来的,很显然这梯田过去种过庄稼的,现在大部分都荒芜了。地里的黄草有半人高,但小路还比较清晰。众驴沿着小路来到南面山脊的大路上。站在山脊上,南眺群山,雾气氤氲之中,层峦轮廓依稀,犹如仙境一般。七星台方向的二郎山似乎离我们不是太远,那高高耸立的雄姿,诡奇壮观。东南方向的百丈崖水库就在山下不太远处,但在蒙蒙的雾气里只能看到一个大致轮廓儿,让人难以分清究竟是不是百丈崖水库。我起初认定这是垛庄水库,因为百丈崖水库似乎没有这么大。辰桑肯定地说不是垛庄水库。当时没有看地图,一时也弄不清楚,及至查了地图,才知道辰桑说得对。垛庄水库比百丈崖水库大得多,应该离得更远一些,藏在云雾里根本看不到一点影子。

继续东行,大路从山脊上的一大片芦苇荡中穿过,也算奇观。印象里的芦苇,多生在水边、沼泽里,现在在这大山的山脊上竟然生长了一大片,而且长势这么好,比较罕见。看来除了水芦苇,应该有旱芦苇这个品种吧。有驴友问我,芦苇与芦荻有什么区别?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二点:一是芦苇穗花呈刷子状,淡褐色,芦荻花呈尘尾状,洁白色;二是芦苇叶子较软,芦荻叶子较为锋利。

出了芦苇荡,大路竟然转弯通到山崖上一处荒村去了。远远望去,那荒村断垣残壁的,就像鬼子进村扫荡过了似的。显然这里曾经有人家居住过,但现在已经人去村空,可能是政府动员集体搬迁到山下去了吧?济南藏龙涧南面有个黑峪村,就是由于缺水缺电,村民生活不便,集体搬迁到矿(工音)村去了。

山脊上荒草连绵,能没了大腿,像一大片草原似的,怪不得这里叫黄草顶呢。走不远,我们又回到了山脊大路上。

渐渐地路边出现了少量的芦荻,洁白的荻花迎风摇曳,很美。梯子山顶也有一小片芦荻,也该到了扬花抽穗的时候了,我有几年晚秋没去梯子山了,还真有点想念她们了呢!女驴友小手掐了一把荻花,有驴友给拍了下来。轻柔的荻花洁白无暇,但与人相比还要逊色几分呢。

下山的小路上偶尔出现几棵色彩鲜艳一点的红叶树,或者黄叶树,爱美的女驴友们一棵也不放过,非得玩着花样拍几张照片才行,这大概是女人们的天性,可以理解。我们走在前面的驴友已经翻过一座山头有百米远了,她们还在山的那边没有玩够呢。

下到谷底的小村庄,却不知道是哪里,街道上也没有一个人影儿。我正在东张西望,忽见一跨村路的铁架子上有“公益牌村”几个大字,才知道村名。这个村子不大,我是第一次来。我们沿着村路往西行走了有一公里远,就到了三王峪。
路边有一棵银杏树,大约有几十年树龄了,此时满树黄叶一地金,正是银杏树最美的时候。见到满地的金叶没人要,我就想起老家门口的那棵古银杏是否黄叶了呢?记得也是晚秋,老家那棵古银杏也到了满树金黄的时候,但是落地的叶子是存不住的,都被居住在古树周边的村人弄家里做烧柴了。不过那时也没人关心银杏叶的美与不美,只知道银杏叶黄了天就开始冷了。那时候老师给小学生布置的家庭作业很少,甚至没有,因此我们放了学回家,不用母亲吩咐,自己就知道拿起笊蹼,擓起篮子去拾草。因为家里缺了烧草,就做不熟饭,烧不热炕,一家人就得挨冻。也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有一天深夜,北风呼啸了半夜,凌晨时分,我被三哥唤醒,他叫我跟他一起去划搂银杏叶。当时天还黑着,我睡眼惺忪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三哥,来到银杏树下。只见满地金黄的树叶像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似的。趁着月亮洒下的微光,三哥用笊蹼满地划搂树叶,弄成一小堆一小堆的,我跟在后面往网包里装。三哥搂了几堆的时候,银杏周边的邻人也来了几个搂树叶的。树下的黄叶很快地就被划搂一空了。借着熹微的晨光,我见树上的黄叶已经凋落的差不多了,但还有少量的金叶仍然在零星地飘落,如蝴蝶一般飞舞。三哥与几位邻居拉一会儿呱,就开始往家背树叶,一连背了几趟才背完。待我们回家,天色才渐渐能看清楚人的脸了。

到了已经废弃的三王峪景区门口,往山坡上有一条公路,正是通往赵岭村的。路边有两棵身姿虬曲的柿子树紧挨着,树干差不多粗,像一对情侣似的。树枝上挂了许多红彤彤的柿子,蓝天下愈加红艳。只可惜,这些柿子的命运也跟济南南山区许多地方的差不多,大概率也是自生自灭吧?

到了去年驴友们拍合影的地方,好梦再次把大家召集起来拍照留念,只是改变了一下背景地而已。

山谷两侧的山坡上火红色的黄栌尚存,只是时光不饶人,我们也就是晚来了七八天的时间,那火焰一般的色彩便顷刻苍老了容颜,减去了多半的精气神,这与人生何其相似啊!
山崖根有眼泉,叫老泉。泉水碧透,清澈见底,只是外砌的水泥池子有点丑陋,不然我非得尝尝不可。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与朋友曾来过这里,当时老泉被一块有机玻璃罩着,与人隔绝,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那块有机玻璃不在了,上面像破了一个洞,可知山泉已经还给自然了,这是一件好事。

与老泉相距不远,斜对过的北面山坡上曾有眼响泉,从乱石丛里涌出,流量颇大,令人惊奇。泉畔有座仿古长亭,我们坐在亭子里看泉。泉水汹涌,凉风扑面,甚为惬意。现在古亭尚在,那眼泉却不见了,也不知何故。当时泉旁边的梯田里农民种的谷子长势甚好,累累的谷穗弯着腰,耷着头,一片丰收景象。现在的梯田里也长了许多的植物,不过不是庄稼,倒像是野草,甚为荒凉。

离开古亭,众驴继续前行。路边种了许多不认识的一种树木,树上结满了红艳艳亮晶晶的红豆,已经形成了规模,远远望去,就像含苞待放的杏园似的。看样子,这红豆不是济南南山上常见的南蛇藤豆,也不是忍冬豆,我瞅了半天也不认识。有驴友告诉我,这可能是海棠。海棠花很美,我居住的小区里就有。那些海棠果虽然不大,但也没有这么小,我不大相信。查《形色》,还真的是海棠!可能是海棠的另一个品种也未可知。可见孔夫子所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非常正确。

这时已经下午1点了,驴友们也都饿了,有驴友提出从山谷公路拐弯处爬山回赵岭,能近不少路。我也有点累,不愿意再走盘山公路,毕竟有点远,再说那公路也比较陡峭。及至众驴爬到半山,我的腿就像绑了沙袋似的挪不动了。我知道这是早餐没吃饱的缘故。驻足稍歇,翻翻包,搜出一小袋烤花生仁子,便一把按在嘴里,也是立竿见影,身上立马觉得有力气了。
(本文部分图片借用了同行驴友之摄影作品,在此致谢!)
2024年11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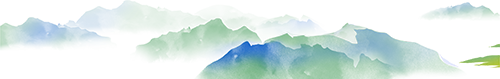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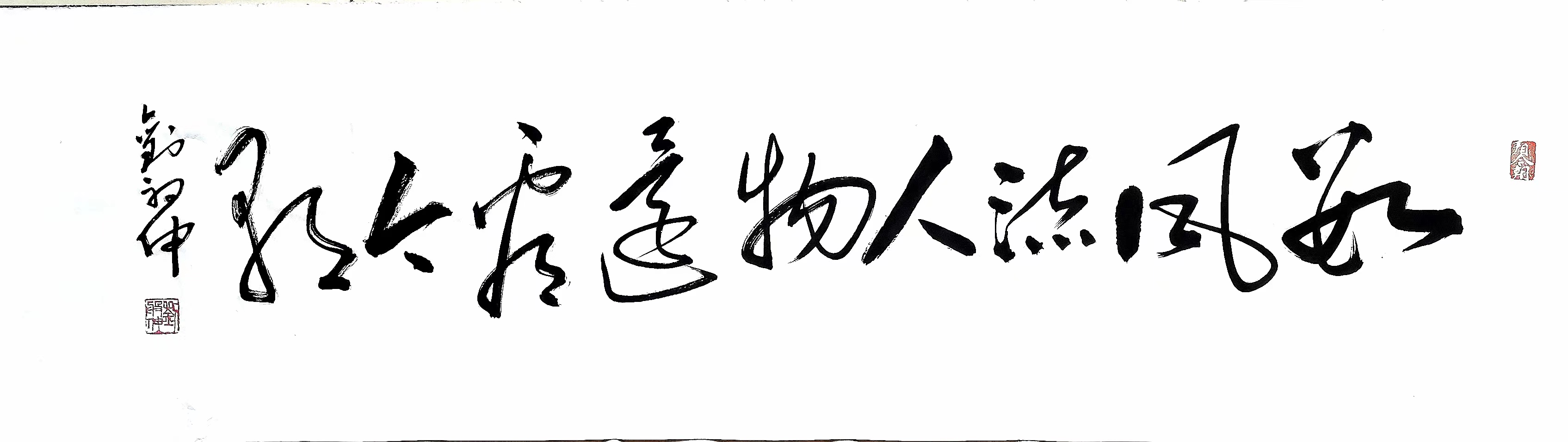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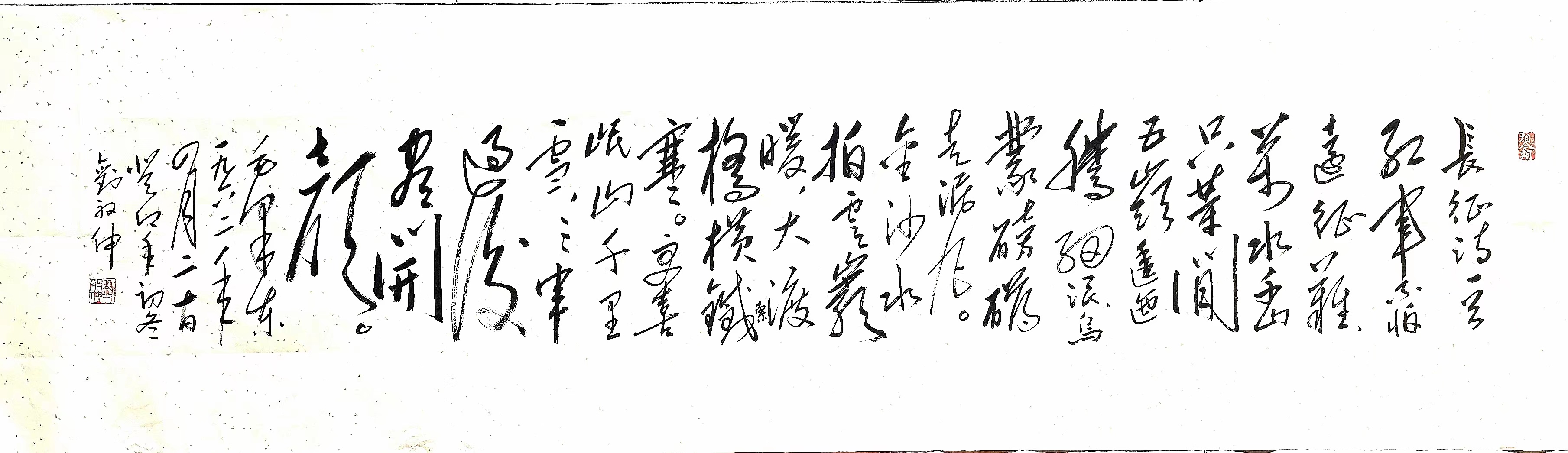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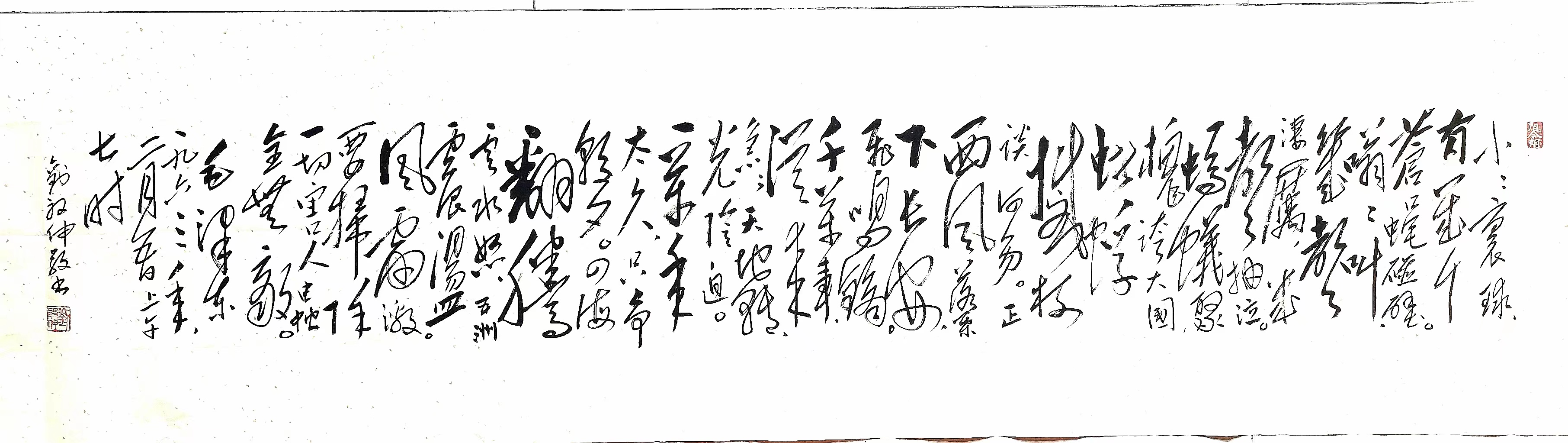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