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马延明

这篇文章,已经埋藏在心底很久了,可我一直没敢写,因为我一直整理不出思绪,怕自己的拙笔表达不出对父亲的那份情感,然而对父亲的怀念却越来越浓烈,心中萦绕,时时刻刻,挥之不去。
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著名歌唱家刘和刚演唱的《父亲》,“总是向您索取却不曾说谢谢您,直到长大后才懂得您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您温暖手掌……”听着这悠扬的歌声,不知怎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脑海中呈现出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的点点滴滴。
父亲叫马光义,济南市历城区东梁王一村人,生于1923年11月,2003年5月去世,享年80岁。父亲从我记事时,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子一米七二左右,不胖不瘦,身体匀称,干活灵活;可能是操劳过度的原因,很早就谢顶了;双眼皮,一双眼睛虽不大,但是炯炯有神,两道浓眉乌黑又很长;肤色古铜色,额头上有三道深深地皱纹,左右脸上也各有两道,这大概是坎坷的经历留下的印痕吧!
父亲一生被国民党抓过壮丁,当过国民党兵,干过装卸工,是个泥巴匠(瓦工),种过地,跟过马车,养过鸡,给厂子看过大门……..经历的事情不计其数。
我爷爷和奶奶共生育了六个儿女,也就是说父亲共有姊妹兄弟六人,父亲排行老小,大姑一出生就被奶奶送人了,大爷和二大爷英年早逝,奶奶五十一岁就去世了,这样就剩下了聋哑的爷爷、二姑和三大爷。父亲对爷爷非常孝敬,爷爷晚年病倒在床上好几年,都是父亲和母亲照顾(当时大爷有了家室孩子又小,在外面生活;二姑家里事很多也顾不上),父亲从不抱怨,给爷爷端屎端尿、喂药喂饭,直到爷爷86岁离开人世。
父亲对二姑和三大爷也特别好,我记得父亲在二姑晚年时经常将二姑接到我们家小住几日,虽然当时家境不是很好,可是父亲还是尽量的调整着花样让二姑吃好,二姑去世时,父亲好几天就像掉了魂似的,和谁都不愿说话。三大爷有三个儿子,我记得三大爷晚年,跟着三个儿子轮流过活,由于三个堂兄和嫂子经常在外面打工干活,三大爷经常到饭点吃不上饭,父亲就经常将三大爷叫到我们家来吃饭,特别是三大爷临去世时,父亲陪伴在身边进行照料。有一次,我去叫父亲回家吃饭,看到父亲正用手从三大爷的肛门里往外抠粪便,父亲给三大爷清理好粪便洗好手,我们一起回家,在路上我责怪父亲说:“您也不嫌脏?”父亲说:“你大爷上不下大便,那么难受,我能看着不管吗?”父亲的话让我无言以对。
父亲没上过几天学,据父亲讲,他小时候曾跟一个叫赵元波的私塾先生上过不到两个月的私塾,他当时学习很好,还代表村里出去参加过写字比赛,可惜的是由于家里困难供不起上学,就退学了。即使这样,父亲靠着自学,直到能够读书、看报、写信。记得我参加工作以后,由于工作忙,好长时间没有回家。父亲挂念我,曾给我写过两封信,虽然有几个错别字,但是语言简练,能让人看明白。
特别一提的是,父亲算盘打的好,记得小时候,哥哥在生产队里当记分员,每到年底,都要把生产队里每个社员的工分统计出来,根据工分总数来进行合理的分红。往往是几个晚上,父亲让哥哥念,他就用双手左右开弓打算盘,只要左手和右手的数据对起来,就算下一个的,我常常是听着“噼里啪啦”的算盘声进入梦乡。
父亲和母亲共生了五个儿女,老大是个女孩,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老四是个男孩,八岁时,在村里一个叫庙湾的池塘里洗澡给淹死了,这样一来,就剩下了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我,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父亲由于有点文化,比较开明,所以对子女教育很严格,经常教育我们,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的做人。大哥早年在生产队里干过记分员,二十几岁就当生产队长,清正廉洁,秉公办事,不搞特殊,受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一直干到改革开放,分产到户。
父亲努力地供姐姐上学,可是由于家境困难,姐姐上到初中二年级,由于路途太远,家里买不起自行车,姐姐愣是退学不上了,我记得姐姐的老师曾到家来做工作,可怎么也没有做通姐姐的工作,父亲后悔了好一阵子。即便这样,姐姐出嫁后,在他的婆家靠着这点文化水和人品撑起了她的家,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至于我,父亲更是疼爱有加,寄予厚望。我记得12岁那年冬天,天气很冷,父亲让我和他到坝子集上去卖芹菜,到那里以后,打好地摊,父亲让我守着地摊,他到集上转了一圈说是了解一下情况(卖芹菜的多少以及价格情况),回来时,只见他兴冲冲的双手捧着五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对我说:“天太冷了,赶紧吃,今天卖芹菜的不多,能卖个好价钱!”我看到肉包子,赶紧摸起来一个三下五除二就下肚了,一口气吃了三个,这时父亲只吃了一个,父亲对我说,“把那个吃掉”,我说:“我已经吃了三个,您吃了吧!”父亲说:“我不饿,你吃了吧!”于是我把剩下的那一个又吃了。现在想来,那时真的不懂事,父亲那是不饿吗?那是舍不得,那是疼爱自己的孩子啊!那天也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卖了个好价钱。再就是我上初.三时,经常晚上上晚自习,无论晚上回家多晚,父亲和母亲都等着我回来,从来没有早上床休息过一次。特别是冬天,上完晚自习回家,都看到父亲坐在炉子旁,在煤油灯的陪伴下给我热饭,热好后再给我盛到我的跟前。此情此景让我永远不能忘记。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父亲在我上初.三上学期时,给我说的一段话,他说:“孩子,我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你的哥哥和姐姐都没有上出学来,现在就看你的了,咱家里虽然困难,即使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上学…….。”也就是父亲的这段话,时时激励着我,在学习上从来不敢怠慢,也不敢偷懒,终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济南师范学校,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自豪的父亲脸上挂满了笑容。我永远忘不了1983年的十一月二日这一天(这一年的冷空气来得早一些),59岁的父亲害怕我冻着,上午从老家骑着自行车行了近30公里给我送来了棉被,下午又骑着自行车返回了老家。一个近六十岁的老人啊为了他的儿子竟然一天骑了近六十公里的自行车啊!这不就是父亲对儿子的那份爱吗?
1984年7月16日,早上,我准备离家到单位去报到,这时,父亲拿出一块泰山牌的手表对我说:“孩子,从今天起你开始工作了,给你买了一块手表,你用得着,上班千万别迟到,千万别让人指脊梁骨。另外,有句话送给你,咱们农村有句老话叫“骡子马大了值钱,人大了不值钱”,意思就是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或者当多大的官,千万别瞧不起人…….”
父亲的话时时地提醒着我,几十年过去了,让我还记忆犹新,成了我人生的的座右铭。

父亲一生好交友。在我的记忆中,他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
第一个叫聂荣信,黄河北人,父亲让我喊他聂爸爸。记得我们家盖第一个院落时,他带着三个儿子,赶着小驴车给我们家送来苇箔(过去农村房子都是草坯房,房顶是在檩条上面铺上苇箔,在苇箔上面摊上黄泥,黄泥上面在培上麦秸);还有一次是1975年大哥结婚前几日,他到王舍人庄赶大集,他听说大哥要结婚,便从商店里买了一大卷《红色娘子军》样板戏的张贴画送来,当时贴到墙上,别提多好看了。就是这一次,我问聂爸爸,他是怎么和我父亲认识的。他说,解放前,你父亲曾当过国民党兵,我当八路军,我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抓住,当时你父亲给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当警卫员,团长让你父亲和另外一名国民党兵去处决我,结果你父亲和那个国民党兵商量一下,把我给放了,我找到我们的人后,觉得有点不对劲,带着人返回,看到你父亲正在被五个国民党兵活埋,土已经到了胸口,我立即带人开枪打死两个国民党兵,其余三个跑掉,救出了你父亲。我和你父亲那是生死之交啊!
第二个叫王延明,家在王舍人庄,他比我父亲大几岁,父亲让我们喊他大爸爸。在我的记忆中,他和家里的大妈脾气特别好,他健在时,每逢过年父亲都让我或者哥哥姐姐去给他和大妈拜年,他们对我们非常的热情,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特别愿意去他们家。记得姐姐17岁那年冬天,突然阑尾炎发作,父亲用自行车带着姐姐到市立三院去,当时没有钱看病,父亲把姐姐放到三院(市立三院就在王舍人庄),立即骑车到大爸爸家,敲开门,说明情况,大爸爸和大妈一听,立即拿上钱,灌上热水袋,一起奔向医院,到医院后,大爸爸立即找到他的好友邵大夫,立刻挂号、诊断,然后推进手术室进行了手术,姐姐的病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姐姐出院后,大爸爸和大妈将姐姐接到他家疗养了几日,才让父亲将姐姐接回家。父亲生前给我讲,他和大爸爸的认识是父亲在济南铁厂干装卸时认识的,大爸爸是个瓦工,当时他看到父亲人厚道,机灵又肯干,就让父亲跟着他干了建筑,父亲慢慢的也就学会了瓦工活,据父亲讲,济南化肥厂的大烟筒有一段就是他和大爸爸修的。
第三个叫张文才,章灵丘人,和父亲同岁,但生日比父亲小几个月,父亲让我们叫他爸爸。张文才爸爸和他家的老伴都是老实的庄稼人,对人诚恳、厚道。我小时候经常随父亲到他家去玩,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同父亲去他们家,下午临走时,我执意要留下玩几天,父亲当时不让,害怕我给他们添麻烦,张文才爸爸说:“添什么麻烦?,孩子愿意在这里玩几天,就留下玩几天吧!”就这样我留下在他家里住了一周的时间,他的小儿子和我同龄,我们一起玩的特别开心,当时他家里盖房子,张文才爸爸很忙,但他对我一点也不厌烦,反而有好吃的都是先给我吃。
1973年,当时我们家5口人和三大爷家5口人(三大爷家从外面搬了回来)住在老院里,老院共有三小间北屋和三小间西屋,大哥也已经订了亲,实在住不开了,父亲决定出去盖房子。可是,之前由于爷爷多年有病再加上去世,随后哥哥得中耳炎住院做手术,再加上本来我们家就很穷,哪里有钱盖房子啊?即使这样父亲凭着自己的人脉和朋友的支援愣是盖起了五间草坯房(在当时能够盖起草坯房也是很不容易的了)。这当中就多亏了张文才爸爸,我记得盖房子用的修跟脚的石头全是张文才爸爸(当时张文才爸爸在一个石料厂干活)提供的,除此之外,父亲为了盖房子还向张文才爸爸借了200斤麦子,直到我1979年上初中时,才陪着父亲赶着小驴车给他送去。前几天,我回家时问母亲,父亲和张文才爸爸是怎么认识的?母亲讲,张文才爸爸的一个姐姐找到了我们庄,他年轻时经常到他姐姐家来,父亲也经常到她姐姐家去玩,一来二往它们就成了好朋友。
第四个叫杨风乙,路家庄人,比父亲小一岁,父亲也让我们叫他爸爸。杨爸爸和杨妈妈人也很好,杨爸爸是个木匠,他2021年去世,享年95岁了,他健在时,我每年春节都去看望他。在我的记忆中,杨爸爸木工手艺非常精湛,他门下有七、八个徒弟。记得1973年我们家修建第一个院落时,他带着他的徒弟们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就把门窗做好安上,而且没收取一分钱的工时费。当年,我的姐姐也是经他介绍嫁到路家庄的。杨爸爸和父亲是怎样成为朋友的哪?据母亲讲,杨爸爸年轻时经常到我们村里干活,逐渐的和父亲认识了。我们村北头有一位妇女,嫁到我们村不久其男人就去世了,杨爸爸看上了这位妇女,于是就委托父亲去说媒,经过父亲的撮合两人终成眷属,这个妇女就是后来我们的杨妈妈。由此,父亲和他也就成了至交(无话不拉的好朋友)。
父亲的情况除了上面这些,还有一些传奇和佳话。他活着的时候给我讲,解放前,曾被国民党抓过壮丁,当时用大卡车运到泰安后,晚上准备用火车将他们运到外地,父亲趁着天黑跳火车跑了,害怕再被抓回去,跑了一夜后,在坟坑里藏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再跑,就这样饿着肚子用了两夜一白天的时间才跑回了家。
父亲是个泥巴匠,垒墙的技术和培屋(在房顶上铺上麦秸)的技术比较好。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到村里盖房子的人家去帮忙,从来不收取工钱,盖房子和修房子的人家一看到父亲去帮忙都特别高兴,特别愿意让他给培房子,他培的房顶麦秸结实、整齐、平整,关键是不漏雨。我们家1981年修建第二个院落时,当时家里也是很穷,父亲考虑到我们弟兄两个,怎么样也要给两个儿子每人修建一个院落,于是和哥哥商量修建了一个新院落,盖好房子后,没有钱买整块的砖修院墙,父亲就到砖厂买了一些碎砖头,利用暑假让我当小工,连拼带凑硬是把院墙给垒了起来,记得垒东院墙时,有两个过路的,看到父亲垒墙不用吊线,用砖头拼的这么直,佩服的问父亲:“大爷,您是几级工啊?”父亲说:“没考过,以前在化肥厂干活时,人家说够八级工的水平。”

改革开放后,父亲为了给家里搞点副业,另外给刚做过手术(1977年我做过阑尾手术)的我和刚出生不久的大侄女补充营养,自己利用家中的一间小北屋养起了鸡,在我印象中,养了有二、三十只,除了每天我们吃的以外,每个梁王集他都到集上去卖上几斤,慢慢的由于父亲卖的足称足两,人家慕名来家里排队买,有的还提前预定,父亲也不用到集上去卖了,这样父亲大概养了两年的鸡,让家里的生活有所改变。再后来,哥哥承包了一片菜地,父亲不再养鸡,而是帮着哥哥种菜,父亲捆菜那是一绝,他捆的豆角、芹菜、芫荽等,每把大小一致,捆得结实、整齐,赶集特别好卖,因为我和哥哥以及嫂子去卖过菜,深有体会。再后来,土地重新分配,父亲年事已高,父亲就去给人家厂子看门,就是在上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断腿,那年73岁,自此,在家里休养,直到去世。
父亲一生,我无法用更多的词来形容,也无法用多美的文字去叙述,更无法用规范的章法来表达。只是想到哪,写到哪,我想,这才是真实的。
父亲啊!亲爱的父亲,您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但是,我时时想起您,想起您的一切!父亲啊!亲爱的父亲,面对您做的一切,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我只能说,您是我最可敬可爱的人,儿的心是记载您永远的碑!
2024.10.08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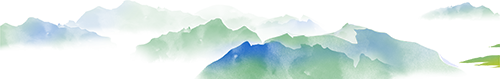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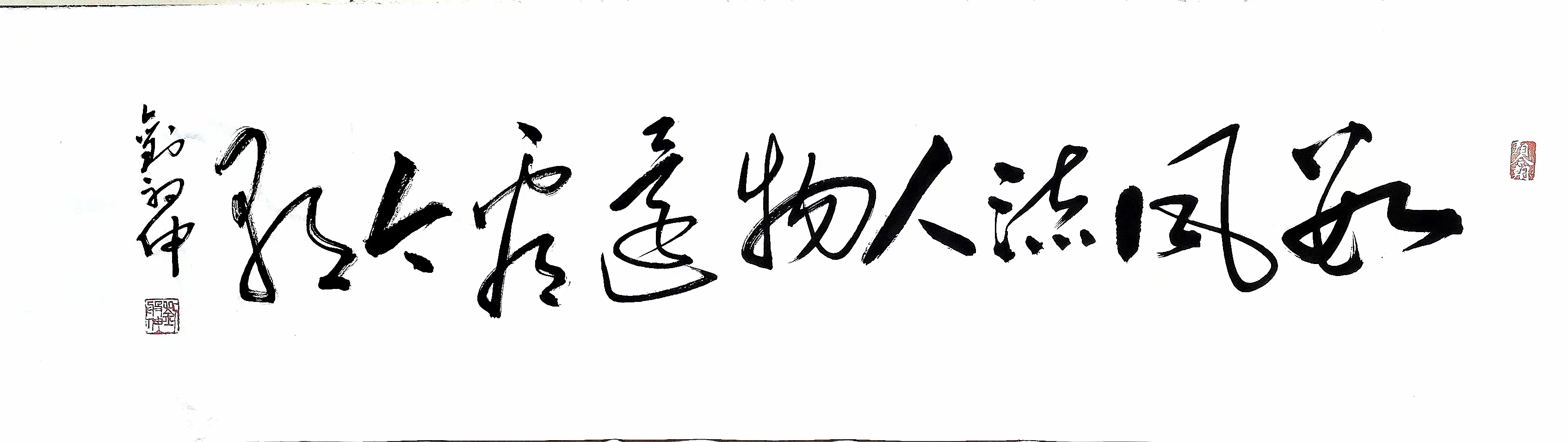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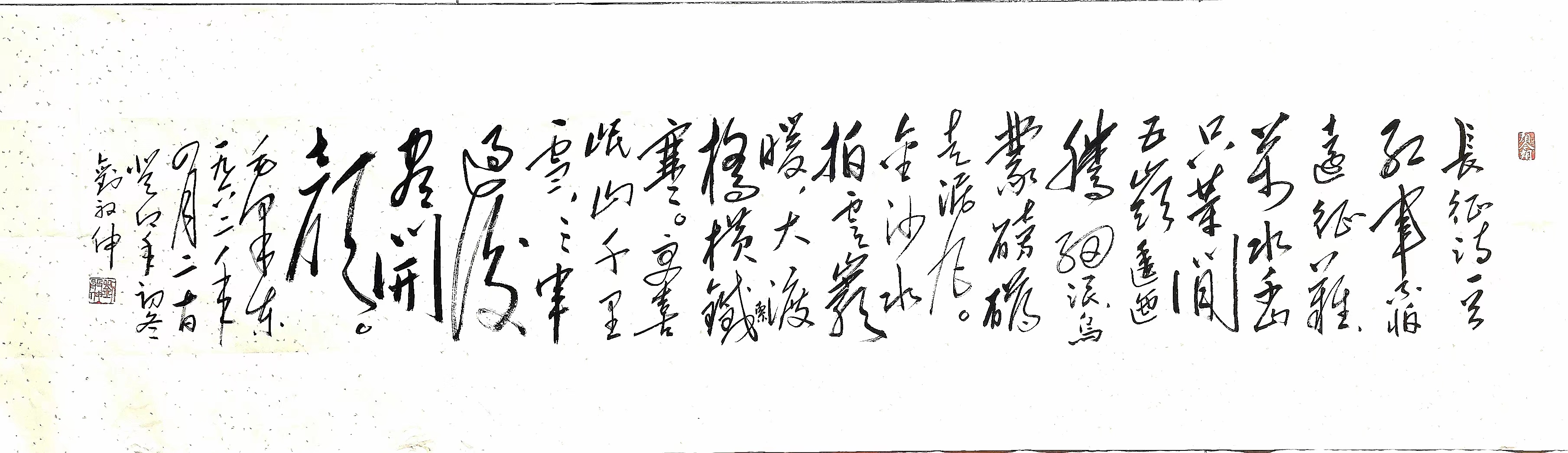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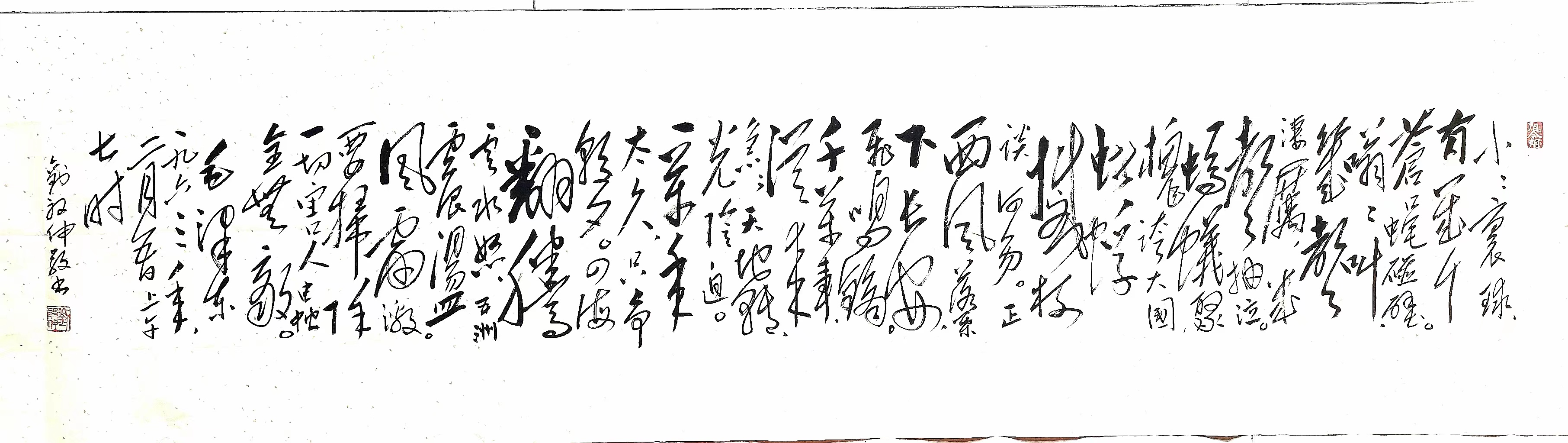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