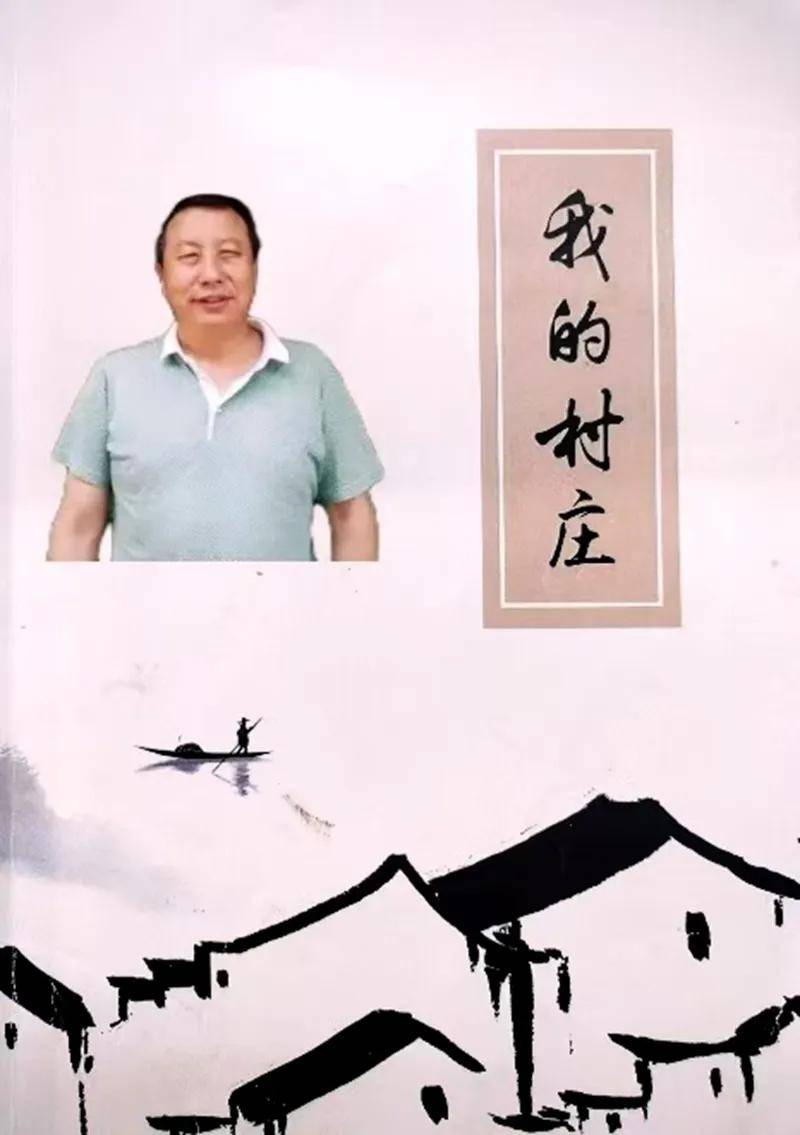
第十四章 拜访张局长

电话是大民打来的,说车已到门外的大路口,一起去拜访张局长,因为村里房屋拆迁的事。
正杰坐上车,问“哪个张局长?”
“张援朝,老局长。”
“啥事?”
“村里环境整治从老旧房屋拆迁入手,还差他一家没签字。老局长,在村里有一定影响,曾是个能甩动风的人物。今儿个咱得亲自登门拜访。”
张援朝,正杰和他谋过面。张曾当过乡镇书记、广电局局长、民政局局长、组织部副部长。正杰不知道他是沟庙人。
“人家是个实权人物,给村里修过路,架过桥,盖小学时捐过款。只要是给村里办过事,无论用啥手段办成,村里人会永远记着人家的好。你是清官,不给村里办事,落个‘白当官,不办事’的话头。张局长和张超武没出过五服(五服是指上下四代人),但他对张超武看不惯,说了两次,超武也不听,关系拧了。村里人说,他们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张局长那几年很少回村。”
张局长住在吉康小区。到小区门口,大民让司机停下车。他到附近超市提溜来“蒙牛”牛奶和“王老吉”饮料,还有两只烧鸡。
“咱要有诚意,不带礼,猫狗都不让进门。更不能‘烧香挠屁股’,大不敬。事先联系过,他应该在家。”
大民翻看手机,收藏里显示:A坐12楼东门。他俩走进电梯间,按下楼层键。
1201的门牌,两人端详了半天。大民上去敲门。
门开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一探头,大民说:“叔,是我。”他拉着老者的手,另一只手提着东西,正杰提起东西跟上。
大民放下东西,马上扶老者在沙发上坐下,递上香烟,老者摆手拒绝。大民把正杰介绍给老者,老者抓住正杰的手,握得紧紧得,说:“傅书记,肩上的担子重啊!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让老百姓满意,不容易呀!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扶贫?就是不忘初心,要得民心!”
“张叔,我把村里的工作给你汇报一下,”大民沏着茶说。
“我一个糟老头子,哪有资格听你汇报……不过,我喜欢听听村里的事儿。”
他们说话。正杰有了机会,一边品茶一边观察。
牛皮沙发,高档饮水机,木质地板,红木茶几,不俗的装修,显得高贵而雅致;窗台上葱郁的君子兰和“精气神”的挂毯,又透出主人高雅的生活情趣。
眼前老者,国字脸,剑眉朗目,不怒自威。
听完大民的一席话,张局长说“张超武把村里搞的乱七八糟,你们要拨乱反正,一定要团结,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去,我给村里办了点事,但现在想起来,有的是违反政策的,有的后怕……做事公道,还要自省……你们来看我,不只是来排排话吧……”
“张叔,咱村要整治环境,但老屋子太多,村里要统一拆除,牵扯的人也不少……还有你家的老院老屋,您得带个头。”
大民拿出《拆除老屋协议书》,张局长戴上老花镜扫视一下,签上了姓名。
“从感情说,老屋老院蓄满了自己的乡村情感,现在时髦的话,叫乡愁。现在晚上一作梦,都是儿时的事儿。……老屋三十多年没住人了,房顶塌个大洞,东山墙咧个大嘴,摇摇欲坠。那东间,曾是我的新房啊!院墙也塌的差不多了,唯有院里的那棵大榆树,顶日摩云,三搂多粗。树得留下,把根把魂留住。”
大民点点头。
“老屋前檐下搭了个简易棚,里面一个土台锅头,连着个风箱,现在耳边还不时萦绕着妈妈呼嗒呼嗒拉风箱的声响,那是童年最美妙的乐声。那时穷啊!吃了上顿没下顿,肚子天天闹革命。妈妈想方设法让我吃饱。野菜美,槐花香,那时候,吃啥都香甜。特别是糁汤下红薯,再撒些葛兰叶,呼噜呼噜喝着还带响呢!……不像现在,茶几上摆满水果,红的黄的紫的青的啥都有。孩子们愣是一眼都不看。有一回,我和大孙子一块看《长征》电视剧,当看到红军吃草根,吃树皮,吃皮带时,孙子问我:爷爷,这皮带能嚼动?还不如弄包方便面煮煮吃。我说,你不懂历史,爷爷给你讲讲。娃儿没吃过苦,哪知道今天生活的甜?哪知道去努力奋斗?”
张局长督促他们喝水,继续说道:“小时候过年,我印象最深刻。妈妈对过年很重视,准备得也早。腊八前就开始了,洗衣服,拆洗被褥,备柴草。院里,我和小伙伴们蹦蹦跳跳,唱着: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馋啥?就是想吃点白面馍。但是白面馍并不多,黑白两掺馍占的更多。豆馅馍甜,肉包馍香,布袋馍,麦秸垛馍最壮肚子。
蒸馍时,我绝对不出玩的,为了能在第一时间吃到年馍。我看着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看着笼屉里淌出了眼泪,闻着弥漫开来的香气,我卖力的拉着风箱,以致锅灰腾腾而起,受到妈妈的斥责。一揭锅,热馍还没泄气,我就抓起一个,用嘴吹吹,两手交换拿着就跑开了。妈妈还炸着果子、丸子,熬点皮冻。爹买肉买鞭炮等年货,常带上我。我把鞭炮当成个宝贝疙瘩,紧紧地揣在怀里。大年三十晚上,要吃年夜饭。鸡块炖粉条,一人一碗白米饭。为了看别人放二踢脚,我端着碗站在院里。
饭后,大人喝点酒,又分点糖给兄妹三人。我只尝一块,把其他的藏起来,——藏的要出其不意。一夜无眠,身上压着新衣新帽,一直在被窝里咕涌(蠕动),夜深才入睡。
夜还黑漆漆的,一阵阵密集的鞭炮声响起来,窗户上忽明忽暗。在屋外小伙伴的催促声里,我匆忙穿上新衣服,一开门,就闻到浓重的火药味。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过,一群人消失在无边的黑夜里。天亮,我兜里装着鞭炮儿,但大多是瞎火。爹早上在正屋的供桌上摆上祭品,待妈煮熟了饺子,盛上一碗也摆上。他带着三个儿女,烧纸,放鞭,一起磕头作揖。
初一拜年,长辈给一毛钱的压岁钱。小时候要给长辈磕头的;后来,不磕头了。‘文革”来了,年不让拜了。当时说是,破四旧立四新,公家不许卖点心。正月十五,去给先人送灯,遍野的红灯笼、白灯笼。那时的正月里,人们来院里的大树下烧香许愿,在树身上系红绳。村里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
“后来,我参加工作,成了家,但没离开过村。1977年,我买了台收音机,当时还是稀罕物。大榆树抽出了榆钱,就像串起的绿色铜钱,低处伸手可及,捋下来吃。老年人先聚到院里,来听收音机。当想听的地方戏和评书,还不到点上,有的排排闲话,有的做点针线活。节目一开始,院里立刻静下来。几个老太太对这个小盒子里发出的扣人心弦的声音,倍感惊奇:有人围着它转,有人拍拍看里边是不是窝着小人,有人挥舞着扫帚,看能不能阻断空中传来的‘仙电’。坐的,立的,盘腿的,搭肩的,都听得入了神。大树下人们送走了爷爷奶奶,送走了爹妈,一茬子一茬子地走了。”张局长说着眼睛有些湿润。
他再三叮嘱,一定要保护好大树……现在已成为古树名木,国家很重视。
大民说:“一定一定。没事,我们就走了。”
张局长说“我也该下楼了,一会儿得去实验小学接孙子。”
上了车,正杰说:“咱得商量点赶紧要干的事。”
“啥事?”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翟柏坡,微信名般若,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教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思客》签约作者。百余篇作品见于《奔流》《牡丹》《洛阳日报》和微信平台,文集《我爱我士》由中国文化出版社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