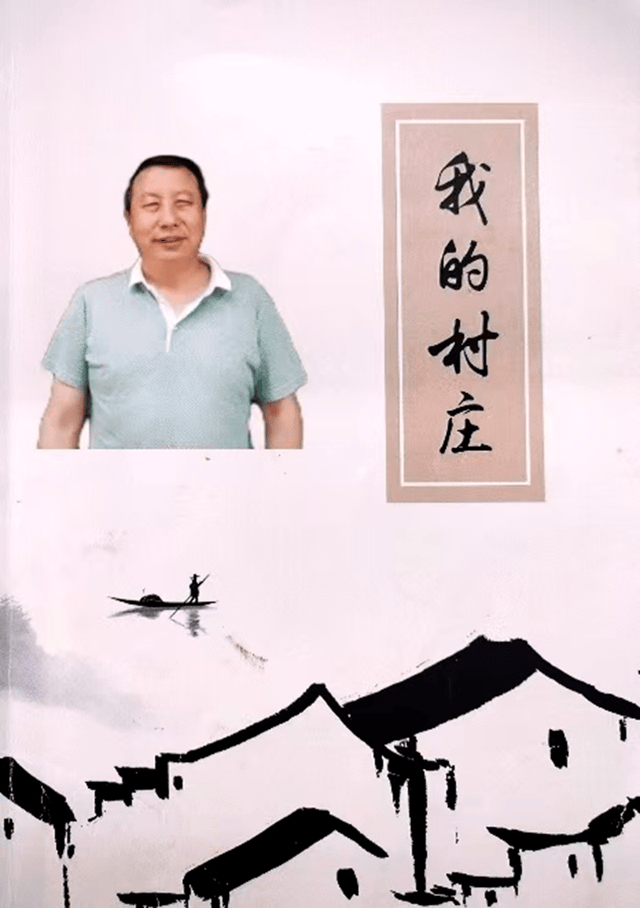
第十二章 刘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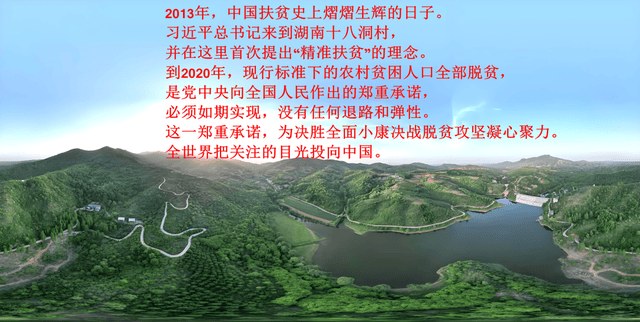
刘六生,四十五岁,枣刺沟村,八组。
六生家是村里唯一的户保。一家四口人都吃低保。
啥情况?张医生说,六生还算个劳力,基本农活都能干。一天骑个破自行车,在村里转悠。到人场听听别人排闲话,趁机说些他的独家新闻。譬如,有一天,他在村里看到拉着“灭害灵”、电风扇等降温品的小货车,从村里经过。六生开始奔走相告:帮扶单位来发降温品了,贫困户明早八点到村委院儿领东西。第二天,不少人去领东西,刚好是星期天,院儿都锁门,人们骂骂咧咧地走了。
大民对六生说,没影的事少出来放屁。六生“小喇叭”的外号传开了,他还很自豪,村里人很厌恶他,说他是一屁股白话,实事求是讲,十件里也有一两件是真的。一天跑跑腾腾,干活折折腾腾。媳妇兰菊,村里人都叫“懒菊”,从早到晚,爱在家睡懒觉。脑子少根弦,谁看她一眼,她就骂上了,村里人见她就躲着走。一见人,傻笑;正干活,说走就走,谁也不打招呼。
两个孩子,一个是严重脑瘫,一个是小儿麻痹。脑瘫是个男孩,胎里带的,自小就瘫在床上,蜷在被窝里,吃喝拉撒都在屋里,挺个个(时时刻刻之意)需要人伺候。越大越难伺候,吃的多了,屙的越多。那年,村里来了个治疗地方病的专家小组,看到这个孩子后,说,建议去大医院治疗,碰碰运气;不然,就当个医学研究样本。六生爸始终不同意。一年一年,现在大儿子快二十了;小儿子小儿麻痹,走路一撂一撂,跌跌撞撞。十四五岁,才上初中。村里照顾,四口人四个低保,大儿子还享受护理补贴,村里还准备给他家再解决一个公益岗位。扶贫好政策,六生得个遍,村里人总觉得他的家庭没啥后劲,一天天走向消亡。他家几乎被国家包了,扶也不用扶了,但再扶也扶不起。
正杰和张医生来到枣刺沟。六生家没大门,进出是房屋和院墙一个敞口。靠南墙下的旧衣服,风吹日晒,已沤烂一堆;尿盆、尿罐、破桌、破椅,站成一排。院里疙疙瘩瘩。这里飘着塑料袋,那里撒落几只破烂鞋子。院中斜立根绣管,水龙头滴着水。
院里闻到浓重的屎尿味,张医生指指西边的一个小屋。屋里一个胡子拉茬的大男孩,僵直身子往外“哇哇”喊叫,近乎歇斯底里。可能这孩子太孤独,一见有人来,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奋。
正堂是三间平房,上搭彩钢瓦。两间西厢房,青砖青瓦。东边是个红墙上面搭彩钢板的厨房。
正杰和张医生生刚要进房门,扑面而来的霉味、汗味,尿骚味,使他俩却步。
张医生唤了几声。六生和兰菊出来了。六生黑脸膛,深眼窝,灰白寸头,红球衣,黄军裤,黄军鞋。兰菊,剪发头,迷缝眼,翻着白眼看人。灰色夹克,蓝裤子,都沾满尘土。
张医生说:“要问他家的入,俩人谁也说不清楚。咱算也能给他算出来。”
“那咱就算算,再把卫生整整。”正杰说。
干了一会儿,六生说,去乡里打探点事,骑车跑了。兰菊见他走了,回房关上门,再也没出来。
耳边充斥着西屋里传来刺耳的喊叫声。
入户持续了两周时间。有二十多户,因家里没人,——有的老人常住在女儿家,有的在县城租房住,有的都出去打工,孩子了上寄宿学校,住在附近给孩子做饭。还有传言,某贫困户买了商品房,成了县城人……他归纳出贫困户是否精准问题,养老问题,环境整治问题,教育问题,产业发展问题,精神文明建设等十大问题。
村干部也都忙着。守在村里的,都种着地,大民和正年每人都流转了五六十亩烟田,忙着下烟苗;在县城忙着生意的村干部,只能当走读干部,有事回村,没事忙着挣钱。他们说,靠着每月几百块钱工资,要饿掉大牙的。
晚上闲了,大民到村委院儿坐坐。正杰问些村里的事,商量下一步需要干哪些事。大民太乏了,有时说着说着,竟扯起了呼噜。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翟柏坡,微信名般若,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教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思客》签约作者。百余篇作品见于《奔流》《牡丹》《洛阳日报》和微信平台,文集《我爱我士》由中国文化出版社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