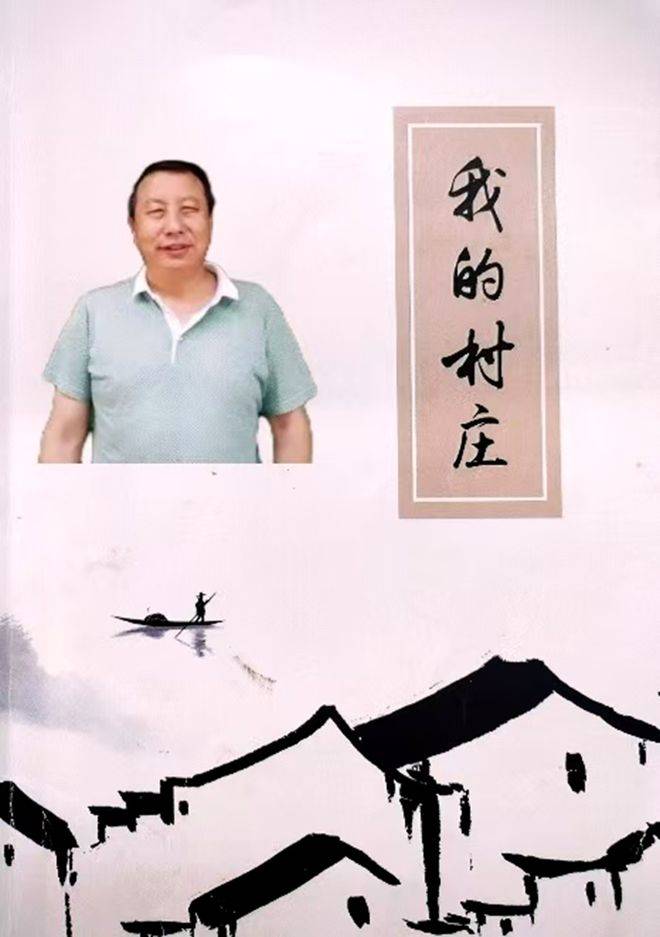
第二章 驻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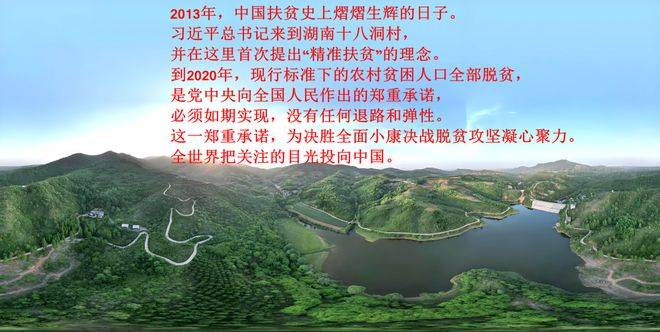
小静拉开拉链,说:“刚买了一根神功元气带,一个花镜,一个茶杯。你看看。”她头上沁出汗滴。
“想得周到!”正杰接过提包,“你一个人吃饭,也不能瞎对付…”
“你管住你,我的心就放进肚子里了。”小静说着走开了。
这时,局院儿正举行升国旗仪式。仪式后,王局长要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只要升旗,只要王局长参加,准要讲话,一讲至少半个小时。都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局来讲话。王局讲话,为了彰显口才和文才,有人说他是“三川县第一嘴”“三川县第一笔”,他觉得很受用。
办公室主任老秦开车,说,王局交代,讲完话来送送你。正杰坐在副驾驶座上等着。
他从后视镜里,看到王局端着茶杯走过来,就下了车。
王局紧握他的手,摇了好一会儿,说道:“辛苦了!辛苦了!等着第一书记扶贫济困,载誉归来!”
正杰苦笑。他知道,此时王局心里有一种快感,一种把他推出去的快感,至于提拔,王局比谁都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年龄是个坎儿呀!
经过繁华的复兴大道,下了一个大坡,穿过滨河公园。园里的柳树正吐出鸟喙状的新芽,在风中扭动着柔软的腰肢。过汶河大桥,碧青的河水,慢呑呑地淌,似乎还在畏惧着冬的寒冽。
河沿上大村多的去,说明先民逐水而居,文明因水而生,在这里也是成立的。屈曲的河流,就像条银线,把众多的村村寨寨串起来,连缀成一串珠子。
目的地是沟庙村。
沟庙村坐落于三川县西南部,东邻周庄村,以大堰沟为界沟;南毗南村,以公路为界路;西至东南村,以岭西水渠为分界线;北接姚凹村,以小河为界。南北约二公里半,东西和南北差不多。地势为“一岭一塬三条沟”。4个自然村,9个生产小组,252户,耕地2124亩。
南山的影子越来越清晰,它要以千钧一发之势压过来,汽车似乎有些惧怕,仓皇地爬上岭急驰,拐了几个弯,钻进了一个大院。面南的正楼上竖着“沟庙村党群服务中心”九个红色大字。从挑梁数目来看,2层12间。远处依墙的地方,植满了花花草草。
“来了,来了!”一干人喊着,从一楼会议室里涌出来。
“傅局长……不,傅书记,你好!”首先迎上来握手的是位身材敦实,面色赤红的中年人。他的手很有力。
“我叫刘大民。”
“刘支书!”正杰拍着他的肩。
大民把村长、副支书、副村长、监委委员、支委委员、村委委员六个人——介绍给正杰。村长张正年,瘦高个,两颊凹陷,牙齿发黄,嘴不离烟。副支书刘书生,是个干巴老头,眼光犀利,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以后咱们在一个锅里搅稀稠……”小嘴叭叭很能说。副村长兼会计张大庆,大眼睛,厚嘴唇,握手时只笑笑。支委委员曲红祥、监委委员刘小明、村委委员兼妇联主任杨妮也都一一见过。杨妮美丽健壮,和《人生》中的刘巧珍有几分相像。
会议室的门口竖着几块牌子。正杰被迎到里面,大家七手八脚把被褥等生活用品搬放到角落的椅子上。室内正中是张大方桌,由两个乒乓球台拼成,上面摆着水果。迎门的墙挂着奖牌锦旗。靠墙还有两个铁皮书柜,一个可能坏了,门敞着,里面立放着蒙尘的奖杯。
坐定后,正杰说:“老刘,你先给我介绍下村里的情况。”
“好。”
大民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介绍了村情户况,重点介绍了贫困户的情况。
正杰认真听着记着。
大民说完,正年瞧瞧刘书生,说“铁嘴哥,讲两句。”
“能的吃不住(特别能)。那壶不开掂那壶。”老刘白了他一眼。
几个人嘴里开始冒烟,屋内烟雾缭绕,杨妮忙去开窗户。
正杰说了些客套的话,让大家多谈谈扶贫的事。
大家七嘴八舌:有说国家投入再多些;有说帮扶单位多点实际支持;有说有的贫困户咋扶也扶不起,简直就是石狮子屁股——没门……”
有人开始剧烈咳嗽。正杰对大民说:“咱以后开会,不准再抽烟,咋样?”
“好。现在就开始。”
吸烟者开始揿烟,把烟屁股扔在地上,用脚拧。
十一点多,有人打哈欠,有人偷看手机,明显不在状态。
“中午去我那儿吃点算啦!”大民说着把住室的钥匙交给正杰。
“不用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馍、面条都带来了。”正杰指着两个大塑料袋说。
正杰送走村干部,从塑料袋里掏出两个番茄,一小把小白菜,择了择,到院子洗干净。倒油热锅,把切碎的番茄、白菜倒入锅里翻炒,熟了加水,等滚开了下面。
吃过饭,到院子里走了十分钟,弯弯食(消食)。他想看看村里的扶贫档案。文件柜里的档案盒横七竖八地躺着,有的少边缺页,有的“没心没肺”,是个空盒子,还有的正装倒装汇在一块,很混乱。他把盒子码好,费了些功夫。
他拿起一本《沟庙村村情概况》,顺手在笔记本上写道:沟庙村,252户,1256人,耕地2124亩。贫困户81户,外出务工124人,养牛户31户……
下午一点多,正杰有点犯困,他打开住室的门。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可能这里存放过蔬菜或水果。
室内一张电脑桌,一张旧长桌,还有几把椅子,东北靠着墙犄角放着一张床,——又高又窄,蒙着酱色的皮革;上面水印明显,像刚抹擦过。床上面墙上挂着一张大肚孕妇的侧面照,还有一张为孕期保健知识。噢!原来这里曾是村里的计生室。
过去人们是罚着生、抢着生,这张床上不知扼杀了多少个小生命;现在,计划生育放开了,鼔励人生,偏偏很多人不愿多生。正杰想着,摇摇头。
他把会议室的东西都搬过来,该铺的铺,该摆的摆,该挂的挂,该洗的洗,忙乎了近两个钟头。
他困了,骨碌上了床斜躺,拉过被子,想眯瞪一会儿。他刚一入梦,就被“嘣”的撞门声惊醒。他忽地坐起来,蓦地感到腰疼,急忙在地上找鞋,他看到一个约六十多岁的老嫂子已站在床头。
“嫂子,坐,坐。”
她靠着墙站。头发曾染过,时间长了,顶上开个“白花”。圆脸,高颧骨,抬头纹深不见底。上身着暗花的黑红丝棉祆,前胸布满饭痂子和油点。下身着黑色裤子,灰色运动鞋,鞋帮糊满泥糊,鞋带拖着泥蛋,刚从地里出来的样子。
“我叫张大娥,五组的,在张家家庙后住。我来问问:为啥我家条件恁差劲,咋评不上贫困户?比我好的都成了贫困户,村干部的眼被屎糊住了,还是装进裤裆了?”她连说带骂。她见正杰有些尴尬,忙说,我不是骂你的。
正杰站着问:“困难是啥?”
“俺都六七十岁了,浑身上下头晕目眩心口疼,血压高。老头子,去年脑梗,瘫痪在床,吃得多,拉得多,屙尿一床,我一身病,还得伺候他,真弄不动……”
“几个孩子?孩子们得管管。”
“三个孩,两男一女,都成家了。孩子们都要过光景,都忙。”
“有没有低保?”
“老头子有,他身体不好,该吃。低保都是红烧肉,都急着吃,弄虚做假的,气死人了!”
“你来驻村,我向你反映反映,给咱老百办点事儿。”
“吃低保、吃五保,国家都有政策和条件的,不是谁想吃就吃的。”
“还不是你们说了算。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村里有的吃撑死,有的被饿死。”
“都是谁?”
“村里人都知道。我说了,落个不是……”大娥欲言又止。
低保、五保,村里人想吃的人真不少。得到的,心安理得;得不到的,眼红,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咱上边没人,想吃上难呀!干部们眼瞎了。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别人作比较,总觉得不公平。吃不上,骂几句心里好受些。
正杰把大娥说的简单作以记录,说,问问村干部,调查实际情况后再答复。
“老天该开眼了。”她沉默一会儿走了。
上午约定下午三点,大民陪正杰到村里转转。
大民准时来了。他黑色短皮衣,浅蓝牛仔裤,白色运动鞋,很精神。
“刚才,有位叫大娥的,来问为啥她家条件差,困难多,不是贫困户,这是啥情况?”
“啥情况?两个儿子都有本事,一个搞装修,一个小包工头,家家小洋楼,都有小汽车。大娥老两口,随老大生活。她一天拿老伴有病和自己身体不好说事,也不看看两娃子啥光景,养老怕拖累孩子,想方设法让国家多负担。给了个低保还不行,非要当贫困户,她两个孩子有车,县城还有房,她当贫困户,村里还不闹翻天?当不上贫困户,她在村里走东串西,把村干部臭摆得一无是处。”
“原来如此。有空,见了她讲讲国家政策。”
“人家姓常,——叫常有理。”
俩人说着,走出了村委院儿。
一条宽敞的水泥道,横贯东西联系着几个自然村。东南两个方向是村民的主要居住地。气派的楼房和陈旧的瓦房错落在一块儿。树木繁杂,两棵高大的树冠犹显鹤立鸡群。绿油油的麦田里挺出几枝油菜花,灿黄灿黄。村边的小溪,犹如一把锋利的弯刀,一端深深嵌入田野之中,另一端则坚定地插入山岭之上。
“沟庙村很美啊!早听说这里有条渠,名声在外,还有一个人……”
正杰提到这个人关系复杂,难知深浅,话只说了一半。
“沟庙村地势上为一岭一塬三条沟。自然村是一庄三条沟。一庄是庙沟村,三条沟是北沟、蛇沟,枣刺沟。一庄5个组,北沟2个组,蛇沟、枣刺沟各1个组。张、刘是两大姓,村里小姓韩、曲、杨,北沟,蛇沟,枣刺沟,沟沟都不富。一庄也就那样,打工,养牛养羊为主要收入。”
此言不虚。越走,路上羊屎豆越多。
“你说的渠,村里叫‘小红旗渠’,近几年来看的人越来越多。你看,就在眼前了。”
“听说过‘小红旗渠’,不知在沟庙?”
“上去看看?”
“百闻不如一见。上去看看。”
“名叫的有点大,但修渠也确实不易。”
岭下如碉堡似的水塔,岭上的清泉通过一根胶皮水管注入其内。沟底一条清亮的溪流,从它旁边蜿蜒而过。
西岭一二百米高。拾级而上,到山腰见一水渠,深约一米,宽约1.5米,山石砌就。有些渠段,淹没在杂草里。
“进入新世纪,一些地方出现漏水,修补起来比较麻烦。村里利用国家水利扶持项目,在渠上铺设了一粗一细两条管道。粗的灌溉,细的饮水。”
岭上东望,村庄点缀着点点嫩绿,那是初发新叶的柳树,还蒙着薄薄的雾霭,宁静而祥和。与西岭相对的南山,立起一道坚固雄浑的屏障,山顶高高低低,如鼻如胸如乳如肚,都融入蓝蓝的天空中。
大民说;“山里最美的是深秋,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天空和白云就像洗过一样,一个蔚蓝,一个洁白。要是你们文化人看到如此美景,一定会诗兴大发!”
“说是说,看是看,得注意脚下的路,小心硌脚。”大民走在前面引路,正杰小心翼翼地走在尺把宽的凹凸不平的渠沿上,这样的路,注定不平凡,——有突起的石块,有阻挡前行的草木。
水渠依山而建,附在山上,就像悬在空中,更多的咬进山岭的肉里,你看那削平的石崖,和搭在渠上防止落石滚入的架棚,憾人心扉。渠道像条缠绕在山腰的大蟒蛇,相互紧紧依偎着,经受了岁月的洗礼和考验。
“渠多长?”
“六公里多,水是从龙潭水库引过来的。”
“不容易啊!当时人们缺吃少穿,又没有大机械,硬与山斗!”
“是啊。修渠的时候,我才五六岁。记得突然一天,村里带了许多人,搭棚,支锅头,很热闹。白花花的大蒸馍,勾得我口水直流!开饭的时候,我和小伙伴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希望能捞点吃的,狗也跟着乱窜。我爹那时是生产队长,早出晚归。”
“真想听听咱沟庙村的小红旗渠精神。过去人生活苦,改地换天,战天斗地,咋恁有精神;现在,人有吃有喝,躺着不干了,混成了贫困户……”
“晚上,我让我爹过去给你讲讲这事?”
“先谢了!”
俩人回到村时,太阳早已没入西岭,四野笼罩在暮霭的大幕里。
一碟凉拌包菜,一碗糁汤,一块烙馍,就是晚饭。一吃完饭,给母亲打电话,问问父亲的病情;给小静打电话,要按时参加孩子的家长会;给老秦打电话,抽空送个简易床,村里的床掉被子,硌身子。他和母亲通话时,母亲专意给他烙了两个锅盔馍,问他为什么没来取。正杰的鼻子有点发酸。
正杰正在整理档案,一个老者进来。七十岁上下,硬茬白发,大眼阔嘴。
“你是刘……?”
“我叫刘兴帮,是大民的爹。”
正杰忙给老者让座,寒暄了几句。
“刘、张是村里两大姓,村干部基本上不姓刘就姓张,小姓干部是少数。宗亲宗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大民是个实性娃子,你得帮帮他。前两年村里出了黑霸丑事,给村里抹了黑,给乡里抹了黑,给县里抹了黑。前面南村人是吃软不吃硬,后面姚凹是软硬不吃,沟庙人是吃硬不吃软,最终养了虎……不说了,不说了,抱歉,人老了,说话跑题了……你想听听咱西岭渠的事,现在有人叫‘小红旗渠’……今晚上,咱就唠唠修渠的事。”
“当年乡里一声令下,全乡十几个大队的劳力都来了。各路人马在南场安营扎寨:搭棚入住,支锅起火,人欢马叫,全村欢腾。当时人心齐啊,没人不服从,没人抱怨,更没人叫苦。村里人更是觉得外村的乡亲们受苦受累了。村里的菜,随便用;哪怕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从嘴里省一点,集中一下,送到工地的伙房。妇女们成立自愿服务队,做饭送汤送干粮,渠上劳动者挂破的衣服,她们用心缝缝补补,缀缀敹敹。”
“山上干活的也决不含乎。每村包一段。各村开展劳动竞赛,夺红旗,登龙榜,干活都是嗷嗷叫着往前冲。打眼放炮,荡起的烟尘一散去,人都冲上去开干。到处是叮叮当当,一片繁忙。虎口破了,脊椎扭了,手磨破皮挂点彩,是常事,那真是流汗又流血。一根钢钎打下去火星直冒;运水运水泥的,好多负重超过了一百斤,他们贴着山崖,扯着树木,到渠上,身上的衣裳都能拧出水。那时候,大家伙都一个思想:只要听党话,跟党走,出力流汗,心甘情愿,叫‘敢叫日月换新天’。看那红旗招展,热火朝天;听那号子阵阵,到处叮当。好多人都是轻伤不下火线。咱们村的贫困户张生民走路一瘸一拐,修渠时被滚下的石头砸折了腿,上不了山,他在南场修工具,谁不感动?”
刘大叔点着烟,继续说道:“一个劳力一天十个工分,村里一个工分值一毛多。每个人无牢骚无怨言。领导也朴实,实干。他们来到工地,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胳膊一挽,就下场干活了。”
“现在,娃们的肩膀都没压过磨过,嫩得很,挑不动担子。前两天,村里埋人,娃子们个儿一个比一个大,抬杠一上肩,没走多长,就呲牙咧嘴喊着疼。有些领导干部,习惯听汇报,隔玻璃看,不深入实际;衣裳笔挺崭崭的,头发油光铮亮,干活弯不下腰,拿住劳动工具,一拍照,走了。”
老刘端着茶杯,半天喝一口。他专注于回忆往事,抽出的烟又塞回去。
“村里的事,你慢慢会知道。我保证大民全力以赴支持你的工作。”老刘点着烟,起身说,“我走了。”
第一夜驻村,正杰躺在窄床上,就像被捆在上面。他望着窗外黑魆魆的山影,慢慢进入梦乡。
五点多,他醒了,因为被床折磨的滋味难以忍受。当天上午九点多,老秦送来了新床。还说,下周来装电脑。
早上,天蒙蒙,雾茫茫,田野、村庄还沉睡在灰色深沉的大梦里,透出渺茫的声声鸡啼。当太阳把金晖抹上树梢,这里一点点褪去神秘的面纱,推出一个清新亮丽的世界。
正杰站在院里,活动活动筋骨,大口呼吸带点泥士芬芳的空气。风还料峭,但已感受到来自大地深处的温意。“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南山近在眼前,青、蓝、绿,层次分明,闪光的玉带是山溪。
正杰想到在单位的尴尬角色,被人挤兑来挤兑去,干的活,总是些应付、琐碎、临时、空洞的活,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一个踏踏实实给老百姓做事的机会,自己一定要抓住。
早餐,酸汤面叶,再加块扇形烙馍。
要尽快熟悉村情户况,他拿出了贫困户信息采集表,一数81张,——贫困户应该是81户,是名符其实的贫困村。他一张一张仔细看,字体有蓝色的,黑色的,灰色的,字迹潦草,字体大小不一,歪歪扭扭的。他看着,在笔记本上记下每户的家庭基本状况、收入情况和致贫原因。
他一屁股坐下两三个小时都没动弹,感到腰椎酸痛了,才起身在屋里揉揉眼,伸伸腰,鼻翼被花镜腿儿压出了凹窝。
午饭和晚饭都是胡乱吃两口。晚上九点多,总算看完、总结完了,他把致贫原因挽个疙瘩:缺资金24户,缺技术23户,因病致贫8户,因残致贫10户,因学致贫6户;按地域,沟庙60户(1-6组),北沟10户(七组),蛇沟6户(8组),枣刺沟5户(九组)。
他紧锁眉头,在因病致贫户和因残致贫户前面打了个对号,他非常清楚这些户是脱贫最难啃的骨头;其他户能依靠国家的扶持政策,脱贫相对容易些。
正杰一手揉着腮帮,一手用笔敲着桌子。门一声轻响,探进一个人头,他扭头看,问:“谁?”
那人不认识,但正杰觉得有些眼熟。
“你是?……”
“我是村医张国清。中午在院给你打过招呼。”
“坐,坐。”
张医生在电脑前的椅子上坐下。“傅书记,新电脑?”
“嗯。我腰不对劲,靠在被子上,排排话。”
“想排啥?”
“…张超武,涉黑被打的事。”
张医生好像思考了一会儿,忙起身向门外探望一下,把门关紧,转动门后锁,绊好。
“张超武还叫我叔哩。我家是中门,超武呢西门。两家不近不远。超武最得意猖狂那阵,对我家也是人畜无害。有些活不能外传,今儿个我就实话实说了。”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翟柏坡,微信名般若,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教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思客》签约作者。百余篇作品见于《奔流》《牡丹》《洛阳日报》和微信平台,文集《我爱我士》由中国文化出版社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