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华诞看今朝文学作品征文103
黄河船工
齐建水
因为爱好摄影的缘故,我经常到葛店拍摄黄河。葛店是济阳黄河的一处险工,滔滔黄河水由西南方向直冲大坝而来,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转奔东去。也许是桀骜不驯的河水感觉受到了岸坝的约束,被限制了一泻千里的自由,于是翻起高浪,打起旋涡,发出轰轰的咆哮。每当汛期,水势浩大,汹涌澎湃,涛声就像憋足了气的壮牛在吼叫,激昂深沉,十几里地外都能听得见。因此,这里的“曲坝观涛”被评为“济阳新八景”之一。
去葛店的次数多了,便注意到有一位老人也常来岸边,他或扶杖独立,或静坐在杌撑子上,注视着奔腾喧嚣的波涛从脚下流过,目光笃定而平和。上前跟老人攀谈,老人的听力有些差,说话也有些气力不足,但从他略已佝偻的身材可以推知,他年轻时一定是个虎背熊腰的壮汉。通过交谈,得知老人已经九十二岁了。问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自己“喝了一辈子河水”。我不解其意,听一旁他的家人一解释,才知道他过去是一名黄河船工,之所以经常到岸边来,是因为“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来这里听涛念旧的。

说起当年做船工,老人的话就像绵延的黄河水,滔滔不绝,让我感佩不已。
老人说,9岁那年他没了娘,14岁跟爹一起来到船上当船工。一开始操弄的是条小船,一丈二长,八尺宽(旧尺,一尺八合现在1米),是村里四户人家合伙出资打造的,由于船小,抗风浪能力差,没到两年就在一次大风中“泼”了(“泼”就是翻,但船工们最忌讳“翻”字。比如吃鱼,吃完了一面,想再吃另一面,不能说“翻过来”,要说“展过来”)。事后,大家又筹资打了一条船,两丈三长,一丈六宽,这在当时黄河上算是比较大型的船了。船上有七八名船工,有出资人家的男丁,也有找来打工的,全是青壮年。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坐在船尾负责掌舵的,是全船的首领,大家都叫他“家长”(“长”字的方言发音很特别,不是汉语拼音的三声,而是介于一声和四声之间,后音还有些长)。担任“家长”的人通常体格强健,擅于水性,还要略识文字,对河道的水流特性了如指掌,有一定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重要的是,他还要有看风识水的丰富经验,譬如“南风看明,北风看红”,就是刮南风的时候,水面发白有亮光的地方水深;刮北风的时候,浑黄带红色的地方水深,以此来识别河水深浅。河槽中的水流因流速不同,分为“大溜”(也称“河洪”)、“二溜”(也称“二洪”)和“慢水”。行船要根据当时的风向、水势和运货时间要求来决定走哪条溜。下行一般走“大溜”或“二溜”,上行一般沿着“二溜”或“慢水”行船。“大溜”水急,行船快但相对危险,“二溜”或“慢水”比较平稳,相对安全但行船慢。船跑得快慢,是否安全,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家长”看风识水的本领。另外,他还要负责全体船工的分工以及吃喝拉撒等一应事务,甚至全船人的性命安全都掌握在他的手里;通常拿一根长杆站在船头的人称为“头脑”。行船时,他把一根涂有红漆杠杠的竹杆伸进水里,以此测量水的深浅,随时通报给“家长”,二人密切配合,以防止船偏离航道或搁浅。他还负责抛锚,船要停下来,他要及时准确地按“家长”的指示把锚抛入水中,如果靠岸,便把“弦子”(拴船用的绳索)甩上岸,让人系在碇上或树上,把船固定好。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避险,如果船突遇大风或误入旋流,船会猛然间冲向岸石、暗礁或树木,这时,“头脑”要当机立断,操起身边的槁杆,一头抵在肩膀上,另一头抵住障碍物,用尽全力调整船头,防止船撞上障碍物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其他的人称作“当腰”或“伙计”,主要负责划桨、撑槁、扯帆、拉纤、装卸货物等事务。他父亲当时在船上做“头脑”,是仅次于“家长”的人。
船上的“家长”姓赵,当时三十来岁,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目光炯炯,脸色在冷热间转换非常快,行船时说一不二,黑着脸,就像蒙块铁皮,稍不如意就厉声喝斥别人,甚至动手打骂,可等到船停下来,他又会腆着脸,敬酒递烟,跟大家笑骂在一起,风趣幽默,脾气软得很。
老人回忆说,他曾挨过“家长”的一回打。那是一年秋天,正值秋伏大汛,水深浪急,惊涛拍岸。早上起风了,“家长”让大家升帆启航,他正拽了一条帆索使劲拉,屁股上突然挨了一棍子,回头一看,只见“家长”怒目圆睁,厉声训斥道:“腚朝哪呢?要到河里去喂王八吗?”他一下子明白了,拉帆索时,屁股是不允许朝外的,以防一旦绳子断了,人会因为惯性而跌落到河里去。这时候,他爹正站在船头,分明看到了他挨打的经过,非但没过来安慰两句,还狠狠地说了一句“不长记性,该!”。他心里委屈了好几天,后来才想明白了,他们都是为了自己好呢,真要掉到凶险的河里去就没命了。
数九寒冬,大河冰封,自然没法行船。等到“七九河开,八九雁来”,船主和船工们会择吉日举行启航仪式。清晨,船工们在船前摆上供桌,桌上摆上鸡、鱼、肉、馍、水果、烟酒等供品,把一只红毛公鸡在船头上剁了头,把鸡血洒在船上,以示避邪。然后开始焚烧香纸,祈求河神保佑平安,在长长的鞭炮声中,船启航了,船工们开始了又一年闯荡风浪的生活。直到冬天,河水要上冻的时候,船才停下来,船工们把船拉到岸上进行检查维修,用斧头将蘸满桐油的麻纤维,砸进船体裂开的缝隙中,使之滴水不漏,然后通体用桐油刷一遍,封存好其它物品,以便来年春开航时再用。
老人介绍说,船分为跑横的渡船和长运的顺河船。
跑横是指横渡,也称摆渡。黄河自古为天堑,给两岸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人们常说:“隔山不算远,隔水不算近”,隔着黄河,两岸相望,人和物虽可见,但想到达彼岸却不容易。人们要过河就要坐船。人们上船或者下船的地方俗称道口或渡口,时间长了,渡口所在地有的便成了村名,如董家道口、邢家渡、史家坞等。与顺河船相比,渡船舱面平阔,便于载人、载物、载车辆,也便于人车上下。载人运货没有固定的价格,看人看货收费,可以讨价还价。一般情况下夜间不开航,俗称夜不渡河。本村人渡河不收费,说书唱戏的不收费,打卦算命的和乡间民医也不收费。跑横靠风帆和划桨,受水流的影响,船到对岸时通常要偏离道口半里地,河宽流急时,甚至要一二里,这样,到了对岸,就要通过拉纤,把船拉到上游的道口去。
老人说,他们“玩”的船是一条顺河帆船,主要是从济南洛口往黄河下游的利津、垦利等地运送货物,一船能装10来吨。船工们的吃喝拉撒全在船上解决,有时半月二十天都不能回家。忙的时候,一般由“头脑”负责做饭,跑风时就指定专人做饭。做饭用的水是直接取自河里稍加澄清的黄河水,也因此,船工们称自己是“喝河水的”。
傍晚,像鸟儿要归巢一样,船也要进“窝”。黄河岸边有许多挡水的坝头,时间长了就形成一些水流相对平稳的“坝窝”,这是天然的“避风港”。天要黑了,“家长”就让大家把船划进坝窝,抛下锚,在船上过宿。
船工们常说:“黄河里流淌的一半是黄河水,一半是船工泪。”黄河水流浑浊,水势复杂,旋涡暗流很多,遇到激流险滩,稍有不慎,就会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船上,通常都备有一袋面粉,不是供大家吃的,而是避险用的,一旦船不慎撞上障碍物,出现了裂缝或漏洞,河水往船仓里涌,紧急关头,船上的人便把这袋面粉塞上去,并用重物压住,或用东西抵住,因为面粉不容易被水浸透,能够给救险和逃生争取时间。
船上都备有民间自制救生工具,选一对大小相仿的葫芦,最好是呀腰葫芦,中间用绳子栓链起来,在水中把绳子勒在胸前,夹在两个胳肢窝里,让两个葫芦浮于肩下,这样,不会凫水的人也能浮出水面。一旦有人落水,船工们就会拿起救生葫芦下水救人。
船工吃的是力气饭。走下水时轻松,有风无风、挂不挂帆都无所谓。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要向前就要借助外力了。船工们最盼顺风。顺风的时候,“家长”会指挥大家挂起帆篷,并根据风的大小和方向决定帆篷的高度和角度,借助风力行船。船能“喝上风”,只需“家长”撑好舵就行了,船工们可轻松地站在船上看风景,或高声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要不然就坐在帆柱旁抽旱烟,在烟雾缭绕中闲拉呱。风快溜快时,船行似箭,岸边的村庄树木呼啸而过,从洛口到利津200多公里,大半天就能到达,沿黄百姓形象地称之为“大风溜河涯”。如果顺风逆流,则需要2-3天。可惜能张帆的时候并不多,要么没有风,要么风向不对。行船最怕顶头风。如果风大,轻则负重难行,重则把船掀翻。因此每遇大风,便要赶紧找“避风港”躲避。没有风或风小的时候,逆水行船就要人力撑篙或拉纤了。撑船用的篙,是一条7、8米长的柳树或腊条杆子,杆子的前端安装一个“篙纂”(带钩的铁套),用以接触河底。另一头安装一个横拐,俗称“船拐子”。撑篙时可以手握横拐,也可以把横拐夹在胳肢窝下,船工分别站在船甲板两侧,同时扎下一篙,然后一起向船头前面跑,利用脚下的反作用力推动船向前进,俗称“跑篙”。大船有两三丈长,扎一篙,船就能向前航行两三丈远。

做船工最苦的是拉纤。如果船“喝”不上风,又赶上溜大撑不住槁,船工们就只好上岸拉纤了。拉纤又称“拉套子”。每条船上都备有多块纤板,纤板多是用榆木、柏木等结实木头做成的,呈中部稍宽、两端略窄的长条形,长50厘米左右,最宽处6-7厘米,厚2厘米左右,两端各打一个孔,通过这两个孔,将40来米长的纤绳一端呈“丫”字形系在纤板上,另一端系在船梁上。心疼男人的女人,会用棉布和棉絮缝一条宽宽的棉垫子套在纤板和纤绳上。拉纤时,船工们把纤板套在胸前,弯下腰来,身体前倾,脚掌紧扣着布满碎砖碎石和荆棘的地面,跨开大步,一步一步往前挪。肩膀被勒得乌青红肿,肋部磨破皮,双脚被划出了血,都是家常便饭。农村的苦累活很多,打墙脱坯,挖河筑堤,收割挑担,但对比起来,没有哪样能像拉纤这样把生命的力张扬到如此极致。其他活再累,中间可以歇息、可以稍微松懈,可拉纤不行,拉纤需要一股坚韧不拔、不敢懈怠、一往无前的持续发力。为了做到心齐力齐,纤夫中会有人带头喊出粗犷的黄河号子,一人高歌领号,众人随声唱和。喊号子多由头脑灵活的人即兴编词,看到啥编啥,想到啥唱啥,其他人只管齐声接茬“嗨哟”,古老悠扬的腔调在河面上传得很远很远。号子一停,人们便沉闷无语了,一天下来,累得就像浑身抽去了筋骨。有时遇顶风较大,或落差大水流急,本船上的船工拉不动,就要等多条船走到一起后,大家合伙来拉,拉了一条再拉一条。
夏天,天上骄阳烤着,地下暑气蒸着,豆大的汗珠沿着船工们的脊背沟往下淌,顺着裤管滴落在地上,生出一些青烟。倘若在初冬,下雪冻凌,船锚在河中,船工们要背着纤绳下船涉水上岸,先把衣服脱光了,顶在头顶上,到岸上才能再穿上,冰冷的河水浸泡着他们的身体,上岸后被寒风一吹,裂开一道道小口子,真是苦不堪言。
如果船不慎搁浅了,大家就要下船,以减轻船的负重。要把船推到深水区,用手推力量小,就用肩膀扛,用脊背抵,有时双腿陷进泥里,费很大的劲才能拔出来。
拉纤累,装货卸货也不轻松。因为济南以下黄河沿岸没有山,下游修筑石坝就要从济南附近的山上运石头。为了装卸石头,船工们做一块L形的背板,背板长宽40厘米左右,下面做一个卡托板,后面拴两根背带。运石头时,船工们背好背板,蹲下来,让人把石头发到背上,然后弓着腰把石头背上或背下船,常常把背硌得伤痕累累。
黄河船工挣得是一份辛苦钱,但凡家里条件稍微好一点是绝对不会干的,没有坚强意志也是绝对干不成的。

当然,他们也有快乐,当他们绘声绘色地跟村民们讲起沿途的趣闻轶事,当他们把从济南买来的新款式的衣服交给家人,当他们把从海边捎回的纯味虾酱分给亲朋好友,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苦累换得了家人填饱肚子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就会升腾起满满的成就感,辛苦和危险的体验都抛到九天云外去了。
讲到这里的时候,老人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舒开了一些,他把目光投向远方,无比自豪地说:“我们的船还渡过解放军的骑兵连呢!那是1948年秋,解放军要渡黄河,征用了我们的船,我们冒着国民党兵的炮火,在惊涛骇浪中连续七个昼夜不停歇,每船渡三个士兵三匹马,渡了一船又一船,圆满完成了任务,部队还送我们一面锦旗呢!”
老人说,自己生来胆大,上船两三年就做起了“家长”,带领一船人在风头浪尖上讨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了黄河航运局,私船都归了公,自己跟着到了航运队。1959年,航运局配备了长11米、宽7米的机动船,船工们终于不用拉纤了。又过了几年,换成了大铁船,60多米长,10多米宽,安全系数也高了,自己经过培训学习当了船长。再后来,陆路运输快速发展,黄河航运渐渐停止了。20多年前,黄河上还有船跑横,随着一座座黄河大桥的修建和浮桥的连接,天堑变通途,危险性很高的渡船业也停止运营了。
太阳落到了黄河堤顶的树梢上,灿灿的阳光照下来,把黄河水染成了一河金汤。老人要回家了,我连忙向他道别。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中陡生感慨:黄河是有鲜明性格的,同时也造就了黄河船工豪爽勇毅的性格。雷奔电走,风赶流云,黄河船工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走进了历史,但他们那种面对艰难困苦,坚韧不拔,搏浪扬帆,一往无前的精神不会消亡,永远激励我们踔厉前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便没有跨不过的坎,没有闯不过的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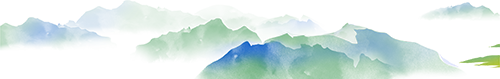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