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四十
白 水

“人过四十天过午。不能再没命的干活了,往后都要悠着点。”我刚上高中的那一年,爸爸这样对我说。那天我们俩下地干活,平整耕过的田地,用大镢头把耕不到的边角翻开来,等过几天种花生。那时已明显是春天了,田野上常有干活的农民,大地已经解冻,一片片麦苗开始焕发精神,空中传来悦耳的鸟鸣声,虽然看不到它们的影子。它们是从南方飞来的吧,几个星期前到处还只是呼呼的北风声,偶尔听到几声喜鹊的哀鸣,至于那些麻雀,大概早已冻得不能出声了。
干完活,日已偏西,我和爸爸扛着铁锨、大镢头和铁耙子回家去。已经十二点多了,可是如果不多干一会儿,就还得再跑一趟。我肚子有点饿,有时咕咕叫,不过把活干完的轻松感还是让我有一种好心情。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阳光变得更明亮鲜艳,周围的树木沐浴在这阳光中,静静的。其实它们一定很兴奋激动,都在鼓足力气,因为过不多久就要吐出嫩芽,绽放鲜艳的花朵了。我把棉衣上面的两个扣子解开,因为浑身觉得温暖舒坦。已经是春天,开始有些觉得热了,不再是冬天那样整天冻得缩手缩脚。
听人说,一天最热的时候不是正午十二点,而是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可是爸爸怎么说“人过四十天过午”呢?现在是刚过午的时候,多么明亮温暖。而整个上午都有些清冷,特别是早晨,还常犯困,没觉得有多好。也许爸爸觉得太累了吧,他是小学教师,平常在外村住校教学,只在周末和假期才能回到家里来。我们兄弟小,妈妈身体不大好,爸爸便成了种地的主力军,在我们承包的土地上不停地干活。自从承包到户以来,爸爸一直这样,我和弟弟也要跟着一块儿干活。好几年了都是这个样子,爸爸肯定是觉得累了吧。我也觉得辛苦,但不种地吃什么?爸爸妈妈比我们干得还多,我们能说什么呢?
不过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爸爸说这样的话。我们并排走,爸爸不经意地说着什么,我记住了这一句话。我记住了那天晴和的天气,温暖明媚的阳光,有小鸟在芽孢变得鼓胀的树枝上鸣叫,它们刚从南方飞回来,叫得那么高兴,一冬天都没听到过这样美妙的声音。那天天气很好,我也记住了爸爸的样子。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认真打量过他似的。爸爸依然很精神,眼睛明亮,脸上闪出光泽,话音沉着有力。以前也是这样,但仿佛总是忙得脚不沾地,或者光顾着自己玩,从没认真端详过爸爸的摸样。但也许是由于干了一上午有些疲惫,爸爸的动作有些迟缓,脚步有些沉重,身体微微晃动。我们一块走在回家的路上,从前我老是在爸爸身后紧赶慢赶地跟不上的。
太阳已经偏西了,走进家门,放下工具,院里地上洒着稀疏的树荫,我忽然觉得天色仿佛暗了下来,身上也觉得有些阴凉了。刚才在阳光下明亮温暖的爸爸的形象也一下子暗淡下来。我不记得那一刻爸爸的摸样,仿佛从那一刻起,爸爸一下子步入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一个“人过四十天过午”的阶段。
虽是这样,爸爸还是带领全家辛苦地干活,每个周末、假期都不闲着。我和弟弟渐渐长大,都能帮爸爸干活。也不是觉得怎么太累,有时觉得筋疲力尽,第二天一样有精神,而且力气不断增长,能自己独立完成某项工作了。比如推小车、翻地、收庄稼等。现在想起来,那时就是年轻啊,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真有使不完的劲。长大了,也开始和爸爸不断有矛盾,不断隔膜。不几年的时间竟觉得爸爸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经常腰酸腿痛什么的,仿佛一下子变老了。
后来我大学毕业也当了老师,和以前一样经常和爸爸一起干些农活。生活条件稍好一些,不用再和以前那样拼命费力了。再后来我家的地少了,就更轻松一些。慢慢的年岁增长,不记得“天增岁月人增寿”的春联换了多少次,有时竟忽然想起爸爸的“人过四十天过午”的话来,心里不知什么滋味。二十好几,几年就三十,三十离四十就更近了啊。那到底是怎么样子呢?自己会是怎么样呢?有时心里不自觉地泛起这样的一些念头。身边的人们都在忙,工作,学习,打牌,吃饭,喝酒,干农活,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我问一位同事:“人到了四十到底会怎么样?”他是位民办教师,教学生教得好,家里的地也种得好,两不耽误,日子过得挺不错。特别是他对什么都有一套道理,知道其中奥秘,会修自行车,配钥匙,会做菜缝衣服,也会打牌下棋,还曾教过体育。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得倒他。领导器重,同事们佩服,学生也尊敬他。闲聊时知道,那一天他刚过四十二周岁生日,我便问他“人过四十”的道理。
“也没什么,一天天过呗,没感觉什么不一样,还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多也不少。”他笑着说,我也笑了。“是啊,应当说一天天慢慢过去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是都说人过四十天过午,大概是有一些道理。过了四十到底会是怎么个样子?”我又问他。他见我认真的样子,沉吟了一会儿说:“其实也是真有区别的。就像干一个什么活吧,二三十岁的时候,咬咬牙,使使劲就能干完。过了四十吧,就好像不能这样了。心里想的是好,可力不从心,再咬牙也干不完了。”
我听了点点头,这是一个道理。想起年轻时比赛一般干活的劲头,是啊,自己也不是那个样子了。几年后是三十,然后四十,五十,六十就退休了,就成了小老头了。头昏眼花,弯腰驼背,整天如朽木枯草,慢慢耗尽最后的一点生命,油尽灯灭,一切都沉入无边黑暗,连那最后消散的青烟也看不到的。“说起来真快,还不曾觉得自己已长大似的。可就要三十了。”我叹口气说。“是啊,真想不到。慢慢过呗。等退休就能歇歇了。”同事说。“您真会说笑话,这么早就想到退休了。还早呢。”“早什么?”他笑着说,“能好好地熬到退休就不错了。谁知道会怎么样?能退休,能多拿几年退休钱,就不错了。你还想干什么?”
是啊,哪一天是容易呢?我们天不亮就起床来学校,晚上八点半下自习课才能回家,九点多才到家。中午时间短不能回家,就买俩馒头一碗大锅菜对付了,其实比学生好不了多少。有时在办公桌上趴一会儿就算午休了。如果能轻松一些,能按时领到工资就太好了。可是就这样吗?就这样一天天下去?可这样真的也应算好的,也是一种理想。最近有两个老师刚退休不久就去世了,一个老师还没退休呢,工作压力大,神经变得不大正常,真是让人惋惜。可是这竟能成为理想?一生竟是这个样子?
对“人过四十天过午”有了一个答案,却又产生了另外的更不好回答,甚至无从回答的问题。但又必须回答,刻不容缓,生死攸关,要用自己的行动,用每日每夜的光阴去回答。
现在我已离开那所中学,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但无从逃避人到中年的状况。回想自己十多年的艰辛,像梦境一样,颠沛流离,可曾有些安稳?可曾让我能轻松面对“人到中年”的问题?不是啊,十多年来的辛苦只是把自己真的带到了中年。还要面对一系列的艰难,承受多方面的压力,而且真的有些力不从心,感觉疲惫,连思考都觉得费力了。怎么办?怎么办?真的穷途末路,却一事无成;真的被远远甩在别人后面,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真的要被弃如敝屣,在体弱力衰、老病困苦中,在别人的轻蔑冷漠中忍受生命的煎熬?
不知道,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但这些一定是真实的,像脚下的大地一样坚硬,像头上的太阳一样明亮,像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怎么办呢?已经人到中年,可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准备,一点也没有,措手不及,心慌意乱。有一段时间甚至晚上睡不着觉,睁大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又觉得整个世界都堵在自己眼前。万分小心,又无从防备。想起原来自己工作的中学里患精神病的那位同事,很害怕也是这样的结局。
静一静吧,别想太多,过好每一天就很不错。自己对自己说。看看闲书,读丰子恺的散文,正好有一篇《不惑之礼》,他很在意地思量自己的人生进入四十岁阶段这个事情。他是艺术家,在绘画、文学方面走卓有成就,可以安然的面对自己的前程。他如何面对新的人生呢?艺术家热爱生命,讲究情趣,对人到中年也带着欣赏的态度,而且觉得又增加了人生的经验和能力,言语间流露出自信与从容。将来如何呢?丰子恺抄录了陶渊明的三首诗自勉,完成了他的“不惑之礼”。可我毕竟是一个平常人,没有逍遥自在的资本。丰子恺的文章并没有给我多少的安慰,愈觉得脚下无根,心中无底。
一日忽接到一位很亲密的同学的电话,心中非常高兴。他原来和我一样,在老家中学里教书。好久没联系了,才知道他已研究生毕业,现在一家人在北京谋生,也在大学里教书。我便问他那里待遇怎样。“兄弟,都四十不惑了,到这个年纪,应该什么都想开了。不再想发什么大财,穷了半辈子,不在乎这个事了。一天天过吧,只要自己努力就行。”他这样说。我顿时感到有些羞愧,同时心头仿佛猛然间闪现出些光明似的。
放下电话,我陷入沉思。人到中年,是岁月的流逝;四十不惑,是生命的澄明。我却只有恐慌,没有什么信心、智慧和力量。丰子恺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不惑之礼”, 表达出一种尊敬和赞美。其实这“四十不惑”正是孔子的人生总结,在两千多年前就解决了“人到中年”的思想问题,而后人只顾悲戚失望乃至绝望,真不应该。
既已“不惑”,那么对于生和死都已弄明白了的,但《论语》中又有“未知生,焉知死”的话,那么“生”又怎样?孔子可曾说明?孔子的一生和普通人的一生可以相提并论?我心里又有些犯嘀咕,不知怎么好。
这时妻子已摆好饭菜,招呼我去吃。我走出书房,窗外夕阳明艳,草木安静地沐浴在金色光辉中,别具风采。是啊,像草木一样,不是生长得很好?那草丛下不是有小虫子、小蚂蚁,也生活得很好?妻子精心准备的饭菜不也是很好?不要自我折磨,且看看这茂盛的草木,想想快乐的小虫子、小蚂蚁,不是很好?安静下来,和家人一起享用美味的饭菜,不是很好?道理太简单,太美好,自己却庸人自扰,走了邪门歪道。
决定每天都这样,好好活着,好好欣赏生命中的这一切。
作者简介:白水,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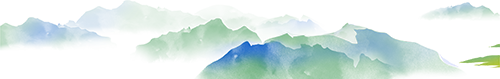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