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
李东川

萤火虫的梦幻飞舞,有种慑魂夺魄的感觉,让人如痴如醉不能自已。
最后一次见萤火虫,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是与几位好友去峨庄拍照片。
峨庄这地方与摄影人有缘,四十多年前曾毅初次来峨庄,拍了那张《条条致富路》,现在想想,峨庄后来之所以成为摄影人的采风基地,曾毅应该是开创者发掘者功不可没。
于是便有了陆玉鲁和孙其光刊于《大众摄影》封面的《送饭》,有了刘统爱刊于《中国摄影》封三的《山峦初醒》等等。
那里有我们太多的记忆——忘不了峨庄的早市上那可口的油条、豆浆,大概他们用的面都是自己种的自家磨的吧,油条的麦香味儿浓的醉人,那豆浆才真正称得上“浆”,很稠,豆香味十足,让人一辈子忘不了。
就是因为峨庄早市上的那碗豆浆,让我一下明白了这“豆浆"和“豆汁”是有区别——豆浆浓浓的,豆汁淡淡的;豆浆浆味儿十足,豆汁清汤寡水没滋没味。
另一件让人忘不了的是三十多年前,我们几个哥们儿拍照片归来,在峨庄公社院子里那一片桃树林下喝酒。
初春的夜晚,乡间的天空湛蓝湛蓝的,上面挂着数不清的星星,很亮。
夜间有几分寒意,酒是在小卖部买的“坊子白干”,很便宜,好像在一元左右。
我们四个人喝了两瓶,都有了些酒意,于是第三瓶直接没开,我提议就地挖个坑埋在地下,以后再来喝,获得大家一致同意。
于是我们在第三排的第三棵桃树下刨了个坑,把那瓶酒直接放在了坑里埋了起来。
第三排的第三棵树,很好记。
我早就听说把这酒埋在土里,那可是真正的窖藏,窖藏的酒香肯定很浓郁。
从那以后,每当春天到来时,我都心心念念的挂牵着那瓶埋在桃树地下的酒。
一晃几年过去了,直到第5年,我们才又来到这里,只不过我们四人当中有一个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记得那个夜晚天上的月亮很亮,照的整个桃树林白晃晃的,多亏“三三”这个数字顺口简单很好记。
我们很快刨开了土,取出了酒。
记得当时把那瓶酒取出来时,我心里生发了很多感慨:这时间太快了,一眨眼五年过去了;并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五年前的四个人,已经有一个离开了我们,那年他才41岁。
我们把第一杯酒洒在地上,那是对朋友的祭奠,当我抬头望向天空时,我看到了一颗很亮的星星在向我们眨眼。
已经在土里窖藏了五年的酒,醇香味儿很浓,我记得在那晚的酒里我喝出了一丝伤感;那杯中映出的月亮,让人感觉到了岁月的味道。
只记得那种感觉真好,在后来的酒中再也没有喝出这种味道来了。
搞摄影的几乎每年四月份都到峨庄来,那时坡野里阳光映照的桃花,杏花,梨花在暗褐色的坡地上耀眼的亮。
一晃又过去了很多年,在20多年前的那个初秋,我们来到峨庄才第一次领略到了它有别于春天的另一番风景。
满山遍野的金黄色庄稼,散发着秋玉米的清香,秋高气爽天空上的那些云,像一垛朵棉花般在滚动。
已经有十多年没来峨庄了,那天正赶上峨庄集,当我站在桥上看到河滩上那些熙熙攘攘的赶集人时,一下想起了在二十年前那个赶集的日子我拍的《播种人》和陆玉鲁那幅《五彩路》,想起了1988年市青年摄影家协会在这里举办的《峨庄风情展》。
那时才三十来岁的我们这帮人,风华正茂的真年轻。
转眼间工夫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进入“古稀之年”了。
公社的那个院子还在,只是公社已改为镇,搬到别的地方了。
当时的二楼招待所早已人去楼空,被废弃了。
那一院子的桃树已没有了踪影,杂草丛生散发出一股悲凉,其实我很享受这样的感觉,当机立断要在峨庄住一个晚上。
想看看这里的夜空,听听河水的流淌,早上一定要去早市上吃油条和豆浆。
于是在镇上找了家小宾馆住下。
太阳早早的落在山后面,夜色降临了。一轮金黄色的明月从山峦间升起,那轮明月好大,这么大的月亮,我曾经在梦里见过。
突然就想我应该去公社的院子里转转,桃树虽然没了,却有一种触动人心的苍凉。
于是我跟正在喝酒的同伴们打了个招呼,就独自朝老公社的院子走去。
在空旷的院子里仰望星空,别有一番滋味。这里有城市里看不到的繁星点点,刚才还是金黄色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幻成了银白色,一下想起了李白笔下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这“白玉盘”的比喻也真是太形象了。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萤火虫,已经有很多年不见这小精灵了,记得上一次见它还是在遥远的童年时代呢。
它们在夜空中摇曳飞舞,那萤火一闪一闪的,像极了天空中的流星。
触景生情,突然就蹦出了“夜空下,院落中,桃花早无影踪。冷冷清秋月,一天星子,几朵流云,荒苑飞流萤。"的词句。
很喜欢这样的月夜,很喜欢这样的空旷荒芜,很喜欢这样的冷清苍凉。
这样的夜,这样的景真是让人浮想联翩——
想起了苏轼的感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也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还有他的叹息:“客与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矣;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一只萤火虫居然落在了我的手臂上,我抬起胳膊,清晰看到了它腹部末端发光器随着蠕动一闪一闪的发光。
夜空中这些闪光的小精灵竟惹的我思绪飞扬:
“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我被它带进了周朝,沉缅在了西汉的《诗经》里;“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也被这小精灵吸引了;就连诗仙李白也忍不住《咏萤火》:“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
于是突发奇想:我此时看到的流萤应该是从《诗经》里、从杜牧李白的诗句里飞过来的吧?要不我怎么也会有“充耳琇莹,会弁如星”,“银烛秋光流萤”,“月边星”相同的感受。
穿越历史沧桑,古人与今人对物的认识及生发的感慨竟如此相似,可见数千年来唯有这人性和情怀没有多少改变。
突然领悟到在人的情感世界里,这时空都是相通相连的,我们同样有“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感怀,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感叹,有从“春江花月夜”直到这美丽“流萤”的遐思.....随着思绪的瞬移,我看到了那些走过了千秋岁月的历史印痕。

萤火虫,打灯笼,飞到西,飞到东,带着小小梦,飞上天,做个星星挂天空。
本文图片摘自网络

【云起图】 于受万画
2024年8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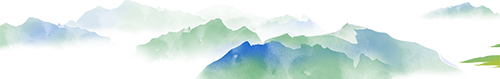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