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热线号如今众人皆知,可谁知道29年前是我首用
它引来记者深入南京市戒毒所采访,也使记者怀疑自己被“染”上毒瘾……
▓ 郝希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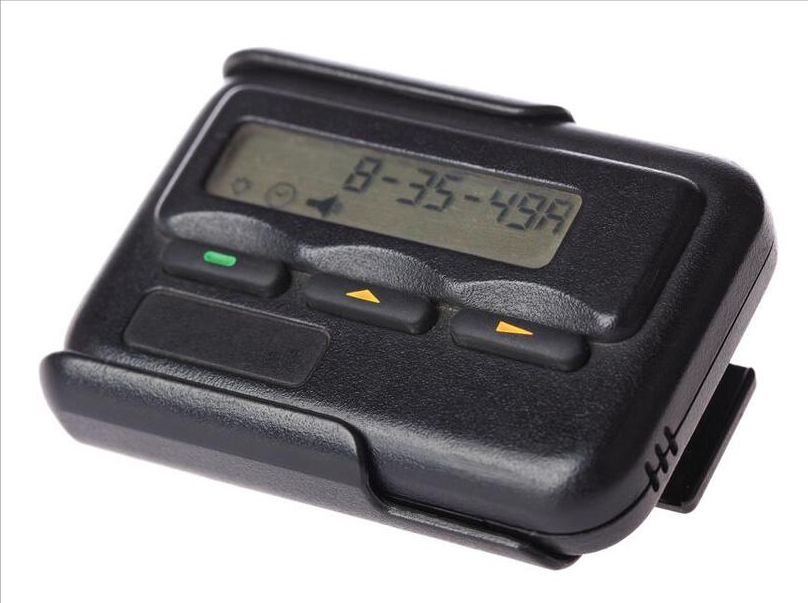 BP机 头条图库
BP机 头条图库
说起12345政务热线,南京人虽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但知道的人确实很多。这条热线于2010年12月28日正式开通。通过公开电话、网上信箱、公众号等接受投诉。受理内容包括房产、税务、医保、社保、人才、公安、交通、文旅、养老、就业、就学等等问题。工作人员7x24小时工作制,分类处理相关问题。他们主要是按投诉内容给有关部门派出工单,限时处理并回馈处理结果,直到诉求者满意为止。14年来,共处理各类诉求百万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然而,作为热线的12345这组号码,在南京最早是由哪家媒体首先使用的呢?第一位使用这个号码的记者又是谁呢?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告诉各位看官,最早使用这个号码的是:南京广播电视报(该报现改为《社区新报》),最早使用此号码的记者正是鄙人郝希洋。
说起这件事,还真是有些故事呢。
1994年,当时南京广播电视报和周末报名列南京报刊发行量前茅,达到每期40万份以上,广告效应也非常好。北京一家通讯公司在南广报投放了不少资金做广告,但时至1995年4月,该公司在支付广告费时资金出现了短缺,于是将一批中文寻呼机(当时基本上都是数字机)抵付给报社。我当时在编辑部属于“年轻、能干”的记者,又是仅有的能开轻摩车跑外勤的男性记者,于是我从中得到了一台中文(汉显)寻呼机,号码定为12345。
“五一”劳动节刚过,我们报纸将一版和16版打通,在眉头上打出了:本报寻呼热线:(海华)3311888 12345(汉显)一一欢迎提供报道线索。
一时间,寻呼热线异常火爆,我都来不及回办公室处理,自己一咬牙一跺脚,花了数千元买了一台摩托罗拉手机(第一代模拟机)来处理此事。
这条12345的热线开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使我们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根据这些线索,我采写了大量的“视野”大特写,如《南京戒毒所见闻》《中国钟表王》《欢乐祥和满石城》《当心别掉进合同陷阱》《房改牵动万人心》《让野菜走上餐桌》《艰苦卓绝的地道战》等,不少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
1995年10月底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我寻呼机收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郑和公园旁“大酒缸饭馆”的地址,并留言说,有重要的事情想面谈。当时我们报社在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旁的抄纸巷,离白下区〈现秦淮区)郑和公园不远。
下午两点多钟,我骑着玉河轻摩找到了这家饭馆。一进门,一位年轻貌美的女老板与我对接。她在看了我的记者证之后告诉我:她一个做服装生意的表妹一星期前突然失踪。后经多方打听,得知可能被公安机关送到了戒毒所。她问我戒毒所在哪里?能探视吗?能戒除毒瘾吗?我告诉她:戒毒所在江北石佛寺,至于后两个问题,暂时无可奉告。临走时,这位美女老板将她表妹的姓名、年龄和住址写给了我。

毒瘾发作 头条图库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苦思冥想,愁眉不展,后来突然眼前一亮:当时经济刚刚放开,政策比较宽松,生意好做,钱也比较好赚,不少人发了财,但也出现了不少“瘾君子”,令人担心。“他们是怎么想的,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他们对社会和家庭又有哪些危害呢?”这不正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吗?于是,我决定到南京市戒毒所一探究竟。
说干就干,第二天早晨,我就带上实习记者徐蔚和省广播电台主持人松腾赶赴江北石佛寺。
汽车穿过长江大桥,在浦珠公路上疾驶。二十多分钟后,一座庄园式的建筑群出现在我们面前。记者抬头望去,但见“”南京市戒毒所”六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跨进戒毒所大门,顿时被整洁优雅的环境所吸引,镶嵌着马赛克墙裙和琉璃瓦屋檐的办公室、办公楼、浴室和食堂、小卖部等综合服务楼错落有致。在医疗康复区院门的横幅上写着“严格执法,文明管理,工作创一流”的大字;医疗部门、护理部门、管教部门配置齐全,400张床位的戒毒楼房整洁明亮……
然而,人们不知是否知道,这座占地5400平方米的庄园式建筑群,在两个多月前还是一片荒地呢?戒毒所所长康华奇向我们介绍说,当年7月,南京市戒毒禁娼专项治理全面展开。打击、查禁、戒除,三位一体式反毒战略开始全面实施。
同月,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由南京市公安局为主筹建戒毒所,负责南京市戒毒康复工作。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大,但市公安局党委一班人还是形成共识,立下军令状:戒毒所到期,不盖“”帽子”,我们就摘“帽子”。
七月流火,一支建筑队伍开进了石佛寺。伴随着机器马达的轰鸣声,辛勤的建筑工人们挥汗如雨,日以继夜地紧张施工。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市公安局党委成员深入到施工现场,认真解决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全市公安部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持配合。经过方方面面的一致努力,这所江苏省第一家经人民政府批准的戒毒所,在不到70天的时间里竟奇迹般地在这里建成了。
1995年10月6日,这是南京市戒毒所投入使用的日子。上午10时许,一辆辆警车鱼贯驶入戒毒所大门,打开车门,一个个“”瘾君子”耷拉着脑袋从车上走下……
据介绍,从10月6日到记者采访时,该所已收治戒毒人员77名,其中男性55名,女性22名,本市70名,外省七名。这些戒毒者中,20到35岁的年轻人占9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居多,绝大部分为个体和无业人员,有前科受到处理或待处理的占半数。
在戒毒所办公室杜主任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治疗室。一名躺在床上正在接受治疗的男子主动成了我们的采访对象。这位33岁、来自河北唐山市的老板是三家小型煤矿的承包经营人,他的吸毒史始于当年5月。
他说——
在人们眼里,咱们属于那种志得意满、风流倜傥的“”大款”“大腕”一族,在灯红酒绿,极尽奢华之后,似乎吸毒才能满足那更大更刺激的欲望。起初还有点疑虑,哥们儿说你别老土了,这玩意儿只有咱们才能享受得起!我想也是,不就凑个热闹吗?开头我并没上瘾,然而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着了魔般的离不开它了。毒瘾一发作,莫名的恐惧感就牢牢控制住自己,哪还有精力去应付生意?曾经好几次在外应酬时,我不得不中途离席,躲进洗手间里悄悄吸上几口。
我开始后悔、自责,眼见几十万元转眼间没了踪影,我怎能不心疼?然而我最担心的是被妻子知道,怕他离我而去。在这样的煎熬中我最终决定离开唐山,到南方找一家戒毒所戒个彻底……
这位用药后的男子尽管身体虚弱,似乎连说话都很吃力,但可明显看得出来他的思维已经恢复正常,他不时支起身子,端着床边的水杯,大口喝上几口开水。
他告诉记者,虽然现在身体松松软软的,但是心里感到舒服多了,就像好不容易甩掉一个大包袱……
这是一位21岁的女子,原先在一家歌舞厅当经理,每月收入2万多元。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在这里她仍浓妆淡抹,刻意打扮。她说她是被“套头衫”套住的——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家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时,一个朋友来访,聊了一会儿后,这位朋友掏出半张香烟包装的锡纸片,卷成一个细细的小管子,又掏出一包白粉,倒在另半张锡纸皮上,用火点燃后,口含小管子吸了起来。她见我睡不着又胃疼,便对我说:吸几口,吸几口以后你感觉就不疼了……就这样,我染上了毒瘾。开始时这个朋友不收钱,等我上瘾了以后,她就开始收钱了,而且都是高价。
“你现在一定很懊悔吧?”记者问,“不懊悔才怪呢,你看我原来收入那么高。自从染上‘白魔’后,不仅吸光了所有的积蓄,而且连BP机、大哥大、金项链全都卖掉了……”
这正是:锡纸半张,未见冲天火光,但见理智、钱财一烧光。
时近中午,随同我去采访的女记者来到了康复区内,看到十多名女戒毒者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或许是同为女性且年龄相似的缘故吧,女记者很快与她们攀谈了起来,她们无一例外地流露出无比懊悔的心情。这时我留心观察到一张略带稚气的面孔,杜主任告诉我她是戒毒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今年18岁,两年前初中毕业时,父母为她在夫子庙某服装商场租了两节柜台,生意做得蛮好。一天,几个同做生意的小姊妹悄悄递给她一小包东西,告诉她吃了之后会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半信半疑的她照着小姊妹们教的方法尝试了一次,觉得怪新鲜。就这样走上了吸毒之路,被公安机关送到了戒毒所。记者询问起了她的姓名和做什么生意,得到回答后记者确认,她就是“大酒缸”老板的表妹。18岁,正是花季,却让“白魔”钻进了花蕊,怎能不令人腕惜呢?!
戒毒先戒“友”,在戒毒所康复区,一位年轻小伙子深有感触地这样说。小伙子今年25岁,在本市一家公司从事绘图工作。当年5月,他从朋友那里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后,曾多次试图自己把毒戒掉。毒瘾发作时,他大碗大碗地喝凉水,用冷水冲头、洗澡,强迫自己转移视线,忘掉“那种感觉”,如此稍稍有些缓解,可好景不长,毒友找上门,小伙子旧瘾发作。靠拿工资生活的姐姐听他说要戒毒,狠狠心将家里积攒的7000元钱全给了他,可他拿着姐姐的血汗钱却又买了毒品……经过在戒毒所一段时间的治疗,小伙子现在已基本脱瘾,他对记者打比方说:“就像戒香烟的人一样,你在这里戒,你周围的人都在抽,诱惑太大了,不脱离相应的环境,你能戒得了吗?”小伙子这次是下决心要与那些毒友一刀两断。
在戒毒所采访,我们看到戒毒者与管教干部们谈心、聊天,有说有笑,关系十分融洽,对医生的治疗,包括对我们的采访也都十分配合。
但事情往往不是绝对的,当一位男子被带到记者面前时,他说道:“我报纸、电视都上过了,问题都交代了,(其实并未交代)凭什么还要把我送到这里来?”这个留着小平头的吸毒男青年刚被送到戒毒所时,大声嚷嚷,并偷偷的吞下了一颗鞋钉。当时管教干部一面对其严厉地批评教育,一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会同医生们沉着应对,给他洗胃,“倒立”,吊瓶、输液……下午,终于将小平头那颗鞋钉弄了出来。
这时,记者和陪同采访的杜主任商量,能否让记者单独和他谈谈,杜主任同意了。记者和他一对一以后,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硬中华牌香烟,点燃了一支,又递了一支给他,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接过去抽了起来,我们也随之聊了起来。
交谈过程中,他竟然也拿出了不知如何收藏的石林牌香烟点燃起来,并递上一支给我。“烟过二巡”之后,他终于告诉我他是如何走上吸毒之路的,并且说:在此之前因为吸毒,妻子和他离了婚。被送到戒毒所后,因孩子无人管,思想不安定,经常发牢骚,不配合治疗,管教干部非常头疼。
和他谈过之后, 我将他的情况反馈给了杜主任。管教干部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他倾心长谈,另一方面会同其居住地居委会找到他分手的妻子,请她帮助照顾好小孩,解除了这位男子的一些后顾之忧。他很感动,表示一定要好好戒毒,服从管教。
“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南京市戒毒所自成立就坚持这个原则。我们见到了一位来自安徽马鞍山的戒毒者的母亲,他儿子和其女友都沾上了毒瘾。毒瘾发作时,儿子便发脾气、砸东西甚至自残,早在戒毒所筹备之际,焦心的母亲便赶到了南京市公安局探听有关情况。南京戒毒所“开张”后,父母当掉家里的电器,把儿子送了过来。缴不全费用的老两口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找到了所领导,所领导望着这两位普普通通尝尽心酸的老人,二话没说,把人收了下来。不久,他儿子脱瘾欲出院,儿子想回到家以后便想法借钱,让父母把他的女友也送过来戒毒。
环境优雅,景观和善,使来这里的戒毒者心中的戒惧打消了几分,他们感到这里的警察医生都是为他们好,消除了对立情绪。当然,在体现人道主义的同时,严格执法又是毫不含糊的。戒毒所先后制定的《南京市戒毒所管理规定》《戒毒人员行为规范》《戒毒人员守则》《戒毒所探访守则》等,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条不紊。
采访了管教干部后,我们又采访了医生,询问有关治疗情况。从戒毒所主治医生徐荣海那里我们得知,戒毒所吸食的毒品都是海洛因。当时,戒毒所主要使用“”茛拓类”药品进行戒毒治疗。“这种治疗方法疗效如何?”记者问道。“这是因人而异的。”徐医生说,“总的来说,无毒戒毒法见效快,痛苦少病人易接受,我们的工作量也相应减少了。”据观察,戒毒所生理脱瘾较快,一般用药后五到七天,病人便可转入康复区。而心理脱瘾却要困难许多,这牵涉到戒毒环境、戒毒者的文化修养、个人意志和社会监督等等。
询问病史是医生对症下药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有些戒毒者出于种种原因,在吸食毒品的名称、数量、方式和时间上往往不讲实话,这就给临床治疗带来了难度。懂行的人都说:宁管十个精神病人,不管一个戒毒病人。治疗戒毒者的困难由此亦可想而知。徐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原先在各自的单位里均为医疗技术过硬的骨干,来到这里后,他们不仅没了休息日,还常常值夜班,虽然如此辛苦,却毫无怨言。
 头条图库
头条图库
身临戒毒所,我们感到它既像医院和学校,也像管教所,兼具了三者的功能,正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所在,医护、管教人员齐心协作,倾心尽力的对每一个戒毒者进行从身体到心灵的医治和拯救。
吸毒是可怕的,吸毒是违法的,其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却偏偏有人染上了这个恶习,其中青年人的比例又占了绝对上风,由此映照出我们在禁毒教育中可怕的空白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深思。戒毒教育是社会工程,学校、单位场所、工作场所、家庭和社区都有防范毒品侵袭的责任和义务。“门户关得紧,苍蝇飞不进。”我们应该记住这句俗语,绝不能等到毒品已经泛滥到自己的孩子、学生、同事或者朋友身上后再进行教育,那时就晚了!
当天回到家里,吃过迟晚饭,睡了一会。凌晨一点多钟,我又像平时一样将两三包香烟放在写字台上(我是个老烟枪),摊开稿纸准备写稿。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天夜里,我的头脑昏昏沉沉想睡觉,眼水、鼻涕不断流出,我后悔白天采访时抽了戒毒者的香烟,担心自己是不是被“染”上了,稿件怎么也写不下去,只好作罢。
第二天到办公室我将此情况说给同事们听,引来了他们一阵阵的嘲讽。他们说:你想得美,在里面检查管理的那么严不说,即使他有那“”宝贝”也舍不得给你“享受”呀!也许是女同志心细,《坐看试听城》的编辑蒋春晓说:“你是不是感冒喽?”我一拍脑门:对呀,极有可能!因为当时正值冬季,温度较低,这些症状和感冒的症状差不多,怀疑染上毒瘾,肯定是心理作用。
我立即去药店买了一些治疗感冒的药。吃了药以后,感觉好多了。
第二天夜里,花了三个多小时,抽了两包香烟,一篇5000字的大特写《南京市戒毒所见闻》终于写成,11月22日整版刊登在了《南京广播电视报》一版。
【作者简介】郝希洋,从事新闻工作36年,2016年退休。曾在中央省市报刊发表作品数十万字,其作品多次获全国、华东地区和省市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