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行信记
大王叫我来巡山
信义庄
7月6日,小暑之日,众驴友事务缠身,皆难驴行。不得已,吾与老李二人只好结伴私奔,投靠泰安“帽檐“大哥,抓马尾、摸马腚、骑马背、抱马脖、瞅马脸……巡游泰山,快意人生。

雨后的泉城,晨光朗朗,空气清新通透,忐忑中老李如约而至。驶上高速,刚出济南,一座“馍馍”样的山体映入眼帘,老李说:那是“馍馍頂”?我说:不可能,看不到那么远。继续前行,一番的辩识,果然是“馍馍頂”。想不到,这雨后清晨,一双浑浊的老眼,竟能看的那么远。“连朝积雨快新晴,雨后青山眼倍明”,看来古人实不欺俺。
路西侧连绵起伏的青山,祥云朵朵,美不胜收;愈来愈近的泰山云雾缭绕,仙气飘飘。激动的心,恨不得一步跨进泰山。
7:12分,车近泰山西麓“小三峡山庄”,远远望见“帽檐大哥”、“玉芝大姐”正在路边等候。嘿嘿,看来今天的巡山小分队,绝对精干。
沿着寂静的环山路前行,透过稠密的树林仰望,咫尺之遥的泰山,笼罩着淡淡的轻纱薄雾,梦幻朦胧;雾随风起舞,忽聚忽散,缘来缘去,浓淡相宜。一道阳光洒过,大片湿漉漉的岩石银光闪闪,明亮刺眼。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银泰山”?“帽檐大哥”说:快看,快看,这泰山变成“银山”了!
惊叹、欣喜中,四人沿“上库公路”,大步向“巴山沟”方向走去。难道“帽檐大哥”又要带俺去“巴山沟”,看山、看水、走“革命路”?!7:22分,四人迫近“罗泉山庄”,忽见路旁松树下,有两老者正树下攀谈,其中一人身背登山包,看见我们的到来,远远招手致意。“帽檐大哥”笑着说:今天护林员带我们进山巡查,活动属公务,招手的大概就是护林员老程。近前相问果不其然,相互介绍后,随即开锁进山。

昨夜一场豪雨,让久旱的山林喝的酣畅淋漓,空气中透着湿润和清新,神清气爽。弯弯曲曲的小路,铺满了枯黄的落叶,令人恍惚,迷茫中,有些分不清当下是夏还是秋;如果不是踩上去悄无声息,真以为是在深秋里,携好友在树林中悠悠漫步。路旁不时出现枯黄的橡树、松树及杂草,前段的旱情真是触目惊心。
有了无人机巡山,以往护林员常走的小路,渐渐荒废,如果没有护林员带路,这路你非迷不可。护林员老程年近65岁,常年山里来、山里去,练就了一副好腿脚,从进山伊始,就一直脚底生风,健步如飞,一马当先,让“帽檐大哥”、“玉芝大姐”这样的强驴,都压力颇大;稍不留神就会望不见其踪影,不得不大声喊叫,以确认方向的正确。近来缺乏锻炼的俺,不知咋的,还没爬多少,就气喘吁吁,汗如雨下,落在了队伍最后,急的俺不停地喊“帽檐大哥”,让老程慢点,等等俺。

路在松林、岩石间蜿蜒上升,时而垂直攀爬, 时而跳跃前行;时而听风,时而赏泉,时而望云,时而观山,这其中的美妙,你不来,哪能懂。有人说:“仙”字是有人和山组成的,人进了山才能成仙。能不能成仙俺不知道,但每一次进山,总会让俺痴痴地望着那山,看着那云,听着那风,物我两忘,陶醉其中,不能自拔。
爬上一处陡坡回望,天空风云变幻,地上云影徘徊,眼前青山如黛,耳畔山泉悦耳,激动地老李,一步跳上一块巨石仰天长啸,一抒情怀。


继续前行,一块块或大或小,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美石不时映入眼帘,引众驴啧啧称赞,让驴行陡增了许多的欢乐。一块巨龟样的岩石横在面前,老李、帽檐大哥悠悠踏行其上,从下仰视,就像巨龟正驮着二人在林海中遨游;这场景,让俺一下就想到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巨龟驮行通天河的情景。抓着松树,攀上一处断崖,眼前一块高两米、长三四米的金黄色美石,令人眼前一亮。这石状若元宝,阳光下红光闪闪。倚在“元宝石”上眺望,山下太平湖波平如镜,天空白云漫卷,青山如黛,风光旖旎。依依不舍转身前行,忽闻水声潺潺,循声而去,只见四五米外,一片岩石莹莹闪着白光,近前查看,原来竟是沥沥清泉石上流淌。此情此景,除了没有明月,与那古诗《山居秋暝》的意境,有何二致。前方悬崖边几块叠在一起的高大岩石,像山神,又似隐在山林中的外星人,抬头仰视,令人敬畏。峡谷中忽然蛙声一片,此起彼伏,似乎在声声提醒,这里就是人间仙境。


循着马尾巴一路攀升,不知不觉中已达一个半小时,提升336米,来到海拔633米的山腰。原以为今天刚刚雨后,气温不高,登山应该十分舒畅,那曾想云蒸础润,闷不透风,一路挥汗如雨,到此体力消耗极大,看眼前山林秀美,岩石平坦,帽檐大哥提议休息。喝点水补充下能量,闲不住的帽檐大哥,便拉我等走向东侧悬崖。用手指着山上浓雾笼罩的一片片山体,一一告知那是“马腚”,那是“马背”,那是“马脖”;然后,又指着深谷,讲起了五十年代周总理指示,不准在“三叉五沟”打石头,保护山体的故事。这“帽檐大哥”泰山活字典的称呼,绝非浪的虚名。

继续上行,大片茂密的松林接踵而至,意外的是,不时发现一棵棵风吹倒伏,遭遇干旱或松线虫危害枯黄致死的松树,好生心疼。玉芝大姐是林场退休职工,见此,一脸的怅然,然后就是拿出手机,不停的拍照,此时此刻,仿佛自己又化身成了那个昔日满山飞奔的模范护林员。
就要接近马腚的位置了,山势愈发陡峭,护林员老程带领我们迂回登攀,既节省体力,又能观赏更多的美景。眼前最美的仍然是那一块块斑斓的石头,都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我想说,这些石头何止会唱歌,他还会说话,静静观察,他会悄悄告诉你很多很多。一棵松树下,一块巨石就像一尊随时出击的“望天吼”,正默默守护着祖国的国泰民安;悬崖边几块圆石,一派仙风道骨,此刻仿佛正悠闲地吐风纳气,汲取天地之精华;路旁穿着一身铠甲的石头机器人,俨然正精力集中,忙碌在生产线上……。各种奇石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不经意间回望,山下蓄能电站的一汪碧水,就似一块镶嵌在黛青色山峦中的碧玉,令人惊艳。


9:28分,耳听着“哞、哞”的羊叫声,在痛并快乐中,众驴提升428米,顺利上达海拔729米“马腚”的位置。喘一口粗气,众驴纷纷与老程合影留念,以感念这份相携登攀的美好。


越过“马腚”,就是“马背”,“马背”之上山势平坦,行走舒适惬意;松林稀疏,视野开阔,是游目骋怀的极佳位置。不巧的是,此刻天空阴云密布,周遭浓雾笼罩。无奈,众驴只好欣赏“马背”上的风光了。
刚刚踏上“马背“,一股刺鼻的羊粪味就远远传来,悠悠前行,这味道愈发的浓郁,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这高山之巅难道还有羊圈?!继续前行,岩石、草木之间,小路之上,一颗颗羊粪渐渐多了起来,行到马背中间一处较大的平地时,其羊粪的厚度,简直比那羊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不是什么羊圈,这山上能有多少只羊?这得多长时间才能累积这么厚的羊粪?看我疑惑不解的样子,一直少言寡语的程大哥,淡淡地说到:山上散养的羊少说也有几十只,这些羊,习惯吃饱了在此休息,冬天更是喜欢聚在这里晒太阳,时间久了,羊粪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原来如此,看来这些神仙般的羊,是很懂得享受生活的啊!
“马背”之上除了这奇特的天然羊圈外,那岩石间一棵棵的松树,总让人想到“坚韧、顽强、不屈”这些词语。你看这些松,几乎没一棵是笔直的,都或多或少倾斜、弯曲,但却棵棵坚挺向上。松几乎都长在岩石之间,贫瘠的石缝中,少有土壤,更谈不上多少的养分,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一点坚韧、顽强,怎能一天天成长。一棵被风吹倒的松树,俨然倒卧经年,但其树根仍然牢牢抓握着岩石和泥土,树冠依然青翠碧绿,大自然生命的顽强,着实令人敬佩。


继续前行就是“马脖”,攀上一段近乎垂直的崖壁,应是“马头”。护林员老程指着垂直的崖壁说:前段天旱,山上的树旱死很多,我还要到别处看看,就不陪各位前行了。上马头不建议攀崖而上,太危险!最好从“马脖”处下行迂回。帽檐大哥说:老程放心吧!下面的路我熟。对了,你们前行,也带我看看山上的树,有问题拍照给我啊。已经转身的老程,又回头郑重叮嘱着我们。
望着老程渐渐远去的背影,看看身边连绵的青山,繁茂的松林,突然感慨万千!让我们致敬像老程一样,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奉献的一个个平凡、普通的劳动者吧!
挥别护林员老程,四人小分队继续前行。帽檐大哥说:上“马头“,悬崖南侧有一条小路,几年前走过,今天雨后湿滑,攀爬有些危险,安全第一,我们还是从下面迂回吧。
沿“马脖“南侧小路贴崖壁下行,恰逢云开日出,湿漉漉巨大的崖壁,在阳光照射下银光闪闪,山下太平湖、新城与泰山浑然一体,分外妖娆。光滑圆润的崖壁旁,突遇一块一段高高翘起的船型巨石,刀切斧凿般的形状,几块碎石支撑不倒的样子,令人叹为观止又百思不得其解。泰山就是这样让人着迷,每次攀爬总会遇到一些神奇。下行十几分钟后,小路开始上行。狭窄的山谷,密不透风的灌木林,长满青苔的乱石,近乎垂直的坡度。让海拔700多米的山地,愣是走出了海拔4000米以上的感觉。一百多米的距离,用了半个多小时才爬到垭口。湿热难耐,汗流浃背,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步也不想走了;同时,嘴里不停地问帽檐大哥:下面的路还有爬升的吗?帽檐大哥笑着说:没有了,没有了,下面一路下行。本想在此歇息会再走,不想帽檐大哥接着说:我们最好不在此休息,前面离“寨顶”不远,到那休息最好。说罢,帽檐大哥率先向前走去。帽檐大哥、玉芝大姐走出十几米了,俺那好意思落后,背起包,咬咬牙,努力向前奔去。


说好了都是下行,谁知这一段仍是上行,还好景色优美,山风阵阵,距离不远,十几分钟后,终在10点到达了本次驴行的最高点,海拔810米的“寨顶”。
站在“寨定”标志的位置,帽檐大哥先拍照留念,然后指着刚刚走过的“马腚、马背……”说到:今天路滑的原因,我们没有爬上马头,马脸也只看到了半拉,以后有机会再来观赏。下面是泰山一处很有意思的人文景观,极少有人涉足。我们休息会再去探赏,相信各位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寨顶”,顾名思义,就是寨子顶端的意思,难道这深山密林中还有什么“寨子?”好奇心忍不住请教帽檐大哥。大哥笑着说:这真让你猜对了,这“寨顶”下面还真有个废弃的“寨子”,至于这“寨顶”称呼是不是与“寨子”有关,实在无从考证,但从明清时期,当地百姓就一直称呼这里为“寨顶”。

从“寨顶”下行,先是一片密密的松林,穿行其间,踏在落满厚厚松针的小路上,十分舒适,颇有“快活三里”的感觉。但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路就被一棵棵倒伏的松树阻断了,前行你不得不“绕、钻、滚”,艰难前行。即便如此,帽檐大哥、玉芝大姐一边行走,一边还不忘护林员老侯的嘱托,把松林损害的状况一一拍照,发给护林员老侯。

10:30分,转过一个山坡,来到海拔757米处,眼前突现许多或大或小的石头房基。帽檐大哥说:我说的寨子到了。这寨子,据说源于汉赤眉军,以后捻军、躲避战乱的百姓均曾在此聚集, 鼎盛时传有房屋300余间。但俺四人数来数去,能够看得出的房基,连20间也不到。不知是以讹传讹,还是被历史的烟云湮灭了,反正这房基与传说差距太大了。沉思中悠悠前行,路旁忽见一处山泉,清清泉水从一块岩石下沥沥流出,让人顿感清凉。帽檐大哥见状,似乎特别激动,一步跨上,急迫地就近观察拍照。过后问帽檐大哥,大哥笑着说;这山寨,地处山巅顶部,没有水源是无法生存的;水源所在,询查史界、户外、山民、林场等多年未果,此次巡查得见,着实有些激动。


兴奋中穿过一道一米宽左右残存的寨墙,四人沿山腰小路继续下行。此刻,小路平坦,视野开阔,鸟鸣啾啾,十分惬意。透过松林,隐约看见右前方有一“博山炉”样的山体,愈走愈近,愈近愈加的清晰,这巨大的山体太像一尊汉代“博山炉”了。泰山,你给我的惊喜总是这样出人意料,难以想象。追上帽檐大哥,问大哥,这山叫什么名字?大哥笑着说:这叫“火焰山”,一会下面我们还会看见“牛魔王洞”。闻此,不禁心头暗喜,那“博山炉”熏起香来,与这“火焰山”是何等的相似啊!


听闻这“火焰山”上有很多奇石,爬上山顶,还能欣赏到周遭许多独特的风光,近在咫尺何不登上看看?!想法还未讲出,帽檐大哥就指着“火焰山”说到:今天由于时间和天气的关系,“火焰山”就不亲近了,留点想头,我们下次再来。
转过一处山坡,前方出现一处群山环抱的凹地,一条小溪,从几块荒芜的梯田前静静流过,山坡上茂密的松林前,几处房舍似乎刚刚废弃。帽檐大哥笑着说:前面就是“松棚”了,过去林场松棚工队就驻扎于此。依山傍水,群山环抱,聚风纳气,好一处世外桃源般的风水宝地。帽檐大哥说:这里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很长时间这里曾有一座称为“剪刀庵”的尼姑庵。有意思的是,这尼姑庵的尼姑与那山寨的土匪、流民,竟能和谐共处,真不知靠的是什么本事?
走进小溪,掬一捧溪水扑在脸上,浑身清凉;用相机变幻着各种模式,不停地记录着溪水欢唱的身姿,久久不愿离去。不知是景色的诱惑,还是触景生情的缘故,还在我等溪水旁徘徊的时候,玉芝大姐早已沿着工队当年修筑的石板路,急切地向工队旧址奔去。

工队旧址的房舍,屋顶均已坍塌,但石垒的房基仍然坚固;房前一台碎木机近乎完好,依稀仍能听见其轰鸣的声响;一棵高大的杉树,默默守望着这块热土,让人感觉昔日工队的辉煌,就在昨天。石阶旁四人席地而坐,喝水聊天,好不开心。但仔细观察,那玉芝大姐好像总是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我想,她一定是想起了当年泰山热火朝天,植树造林的场景;一定想起了为守护这片山林,满山奔跑的岁月;一定想起了那一个个默默奉献的同事、好友……

起步前行,大片茂盛的松林连绵不断,整齐挺拔,令人注目,心中对“松棚”名称的由来,也一下豁然开朗。老李说:下次来,争取在此露营;帽檐大哥说:不露营,也要带个吊床,在松林中好好享受一番。进入松林,一块纹理、形状独特的泰山石,孤零零静卧,引大家十分好奇,纷纷拍照留念。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这路上、林间,怎么竟是一坨一坨的牛粪?赶紧求教帽檐大哥。大哥笑着说:这山上除了羊,牛也很多,看见左侧那山了吗?那是麦秸垛山,那山就是个牛的世界,上面到处都是牛粪。用相机拉近拍一张照片,细细观察,那山体好有韵味。一块高大的岩石,就像是一位古代的将军,威武雄壮,其后一只小黄鸭,正在怯怯窥视,惟妙惟肖。说话间,四人来到一处垭口,帽檐大哥说:下面是浪荡沟 (莨菪沟),美景、传说众多,有空我们也一起走走;今天,时间的原因,只能擦肩而过了。

沿山侧惬意前行,眺望一眼“中天门、黄溪河水库”的秀丽风光,瞅一眼“龙角山”的雄姿,四人迅速下行,搜寻着从石屏(碑)峪出山的入口。

眼前的树木,不知不觉由松树变成了高大茂密的橡树,一棵连着一棵,树下经年的落叶,有的厚近半尺。11.30分左右,四人进入了一片似电影《阿凡达》中一样的秘境,让人恍惚踏入了另一个星球。树下长满了各类的杂草、灌木, 树上缠满了一层层的藤蔓,触目皆是一样的场景,一样的绿色,本就不太明显的小路已经彻底辨不清东西南北了。帽檐大哥说,该向左走,老李说,该向右走,前行的方向一度迷茫。听溪水哗哗,石屏峪就在下方,帽檐大哥说:右边是一处高高的断崖,以前去过,硬下危险,还是选择从左边下合适。一番纠结评判,四人中最年轻的老李,立即折回,率先从左边开始探索下行。

什么是小心翼翼,什么是如履薄冰,什么是提心吊胆,什么是杯弓蛇影,这一路下行,把这些词彻底整透了。下行的坡度怎么也有60多度,厚厚的落叶,稠密的藤蔓,让你每一步,从起脚到落下,都得万般地小心再小心,唯恐没有踏实摔倒,唯恐让藤蔓扯住拉倒。下行的路上有一处著名的“牛魔王洞”(观音洞),费劲九牛二虎之力,俺才得看一眼;传说中当年土匪设置的隐秘哨位及土匪窝,权衡再三,俺也没敢前去探寻。水声越来越响,感觉离沟底已经不远,高声喊问帽檐大哥、老李,都说:快了、快了,但却怎么也望不到底。一处湿滑的路段,玉芝大姐一不小心重重滑倒在地,手都破了;抓着藤条越过一堆乱石的时候,弹起的一根藤条狠狠地抽在了俺的腿上,一道血印瞬时鼓起;前行的老李,拽着树干下行,稍有分心,胳膊扭的疼痛难忍。树林中密不透风,耳畔中除了水声几乎没有任何的响声,高度的紧张、担忧,湿热,体力、精力几乎消失殆尽,让俺一度恍惚,感觉有点撑不下去了。
大概12:20左右,就在快要绝望之际,远远传来了老李“找到正路”的声音,此时,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浑身不知那来的气力,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向下奔去,终在12:46分左右,站在了沟底溪水之边的小路上。过后想来,人,最怕的是失去方向和目标,只要方向目标明确,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这沟底小路,沿小溪蜿蜒向前,看得出,应该是当年林场职工硬化过的,眼前路段宽阔平坦,令人非常开心。终于可以走人走的路了!这样的道路用不了半个小时肯定出山。溪水中洗把脸,稍事休息,四人高兴的大步向前走去。
意料不到的是,刚刚走了不到几分钟,这路就因洪水冲击、年久失修断掉了。前行,进入了一种在溪流两岸来回穿梭,溪水中卵石上跳跃行走的模式。刚开始,蹦蹦跳跳,扭来扭去,四人感觉颇为好玩,很是开心,但时间一长,那老腿、老腰,很快就承受不了了。最先败下阵来的肯定是俺,先是以拍照赏景为由,不停地喝水休息,到后来干脆不管不顾,坐在路旁树下赖着不走了。玉芝大姐看俺承受不住,又怕面子上过不去的样子,主动陪俺休息,鼓励俺坚持前行,令人好生感动。

路是你选择的,无人替代,唯有勇毅前行。忍着正午的酷暑,一遍遍在心中默念,你能行,坚持就是胜利!
沟底的路实在难行,经过一片山体崩塌堆积的乱石时,疲劳、炎热、难行,差点让俺晕倒。但不得不说,这沟底的景色却是少见的壮美。除了清澈见底,哗哗流淌的溪水外,那巨大的岩岩峭壁,那从天而降的飞瀑,无不令人震撼。快出沟时,一片巨岩,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但那宏大的气势,壮观的英姿,又一次让俺读懂了“泰山岩岩”的词句;那近千米飞流而下,勇往直前的瀑布,让俺对“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诗句,有了更深的理解……
下午2:30分,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拼搏,四人终于安全出沟。回望的那刻,豪情满怀。



每次去泰山,回来后总是絮絮叨叨,说不尽道不完。泰山,就是一本书,一本穷尽一生也读不完的书,一本千变万变也读不倦的书。让我用一首小诗,来结束本次的驴行吧!
闲的时候,只想去山野里
安静地,走一走,
沿着一条小径,
慢慢散步,遇见万物,
云朵,虫鸟,草木……
不去刻意等待每一朵花的盛开
只希望能在自然的怀抱中,
让沉寂的心,活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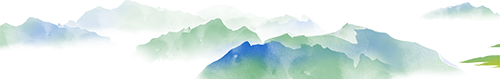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