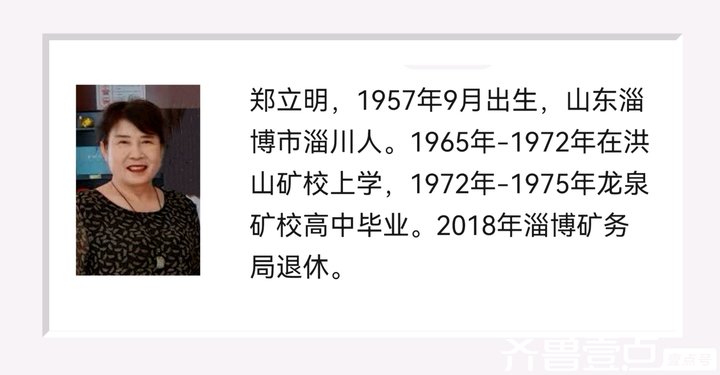郑立明:我的父母亲

(父母亲的留影)
我的父母亲
郑立明
我的父亲,郑良杰,于1930年出生于黑旺镇井筒村,家中姊妹九个,他排行第二。
父亲为人忠诚厚道,言语不多,乐于助人,只要他能帮的从不推辞他人的任何请求。这样的品性,让他赢得了亲朋好友的深厚敬意和信赖。
回想起那些峥嵘岁月,父亲曾在洪山煤矿一立井"五一"采煤队干矿工。尽管工作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他从不言弃。他的坚韧与毅力,使他在艰难中脱颖而出,荣获市劳动模范的殊荣。
母亲曾提及,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家中经济紧张,但父亲慷慨解囊,总是毫不犹豫地借给那些急需帮助的同事。他们大多是农村出身,家庭负担沉重。父亲的行为,简单而纯粹,只问耕耘,不计收获。然而,这也让母亲颇为焦虑,因为工资往往还未到手,就已经所剩无几。
在那个自行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父亲总是乐意借出自己的爱车,并不忘配上手套和裤腿角的夹子。这点滴细节,足以说明父亲对他人的关怀的细致入微。
1964年,因一次意外,父亲不得不告别熟悉的岗位,转至龙泉煤矿的技术质量检查科,后来又调至保卫处,得到了组织的特别关照。
2022年11月26日,九十二岁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年,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充满挑战与磨难的一年,新冠疫情肆虐,无数家庭遭受重创。
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刻,社会上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街道空旷,社区封闭。那时,多亏了我女儿在医院坚守岗位,提供了治疗、生活等方面的方便。
父亲在世时,一直是我弟弟悉心照料,我和妹妹则尽绵薄之力协助。
他的离去,给我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弟弟和我丈夫生病之事,母亲决定不告诉父亲真相,那时父亲已无法言语,仅能以眼神和微笑与我们交流。我们怕他身体受影响才决定这样做。让我后悔的是父亲看不到始终陪伴在身边的儿子,也见不到许久未露面的女婿,身边还多了一个陌生的保姆。我悔恨自己没有及时拨打电话,让他听到我们的声音,也没有让母亲坦白真相。这一切的愧疚,都源于我的疏忽。
父亲的一生,对工作的热忱和负责,对他人的尽心竭力,是我们家风传承的榜样。我们因此感到无比荣耀和自豪。
我的母亲,张玉敏,生于1935年的安丘,作为家中六姊妹中的长女,她的童年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每当回想起那段岁月,母亲总是带着一丝微笑,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她曾向我倾诉,小时候因家境贫寒而无法入学,只能透过窗户偷听邻家孩子的读书声,那声音如同遥远的星辰,让她既向往又无奈。每当夜深人静,她的眼泪悄悄滑落,心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改变命运的执着。祖母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上学不能耽误做活,只要答应才能上学。" 母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条件,因为她深知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是多么珍贵。因此,每一次考试,她总能名列前茅,从未有过第三名的成绩,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成就。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仿佛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女超人。那个年代的交通极为不便,父亲远在龙泉矿工作,无法常回家,于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都落在了她的肩上。她在罗村被服厂的工作,她的岗位是流水线上的一环,专门负责制作袖子。下班后,当同事们纷纷离去,她却留在车间,默默地向其他工人学习,渴望掌握更多的技能,只为能为我们亲手制作衣物。
经过几年的努力,她终于能够独立完成全家人的衣服。每逢佳节,她不仅要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要为我们四个孩子以及自己和父亲准备新衣,常常忙到深夜。她那一直忙碌疲惫的身影,在睡眼朦胧里晃来晃去。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没有成品衣服,母亲的手工缝制成了我们唯一的依靠。她的手艺不仅限于此,她甚至自学了用塑料制作美丽的干枝梅来装饰家居,还学会了理发,邻里们都争相来找她剪发。就连矿上的食堂需要帮忙包饺子时,她也毫不犹豫地积极参与,而我则成了她的得力助手。
1970年,我们一家迁往龙泉矿。我清楚的记得,母亲亲手为我精心制作的花布小褂,黑底白花,紫底小花的图案设计,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过朝鲜电影后,我迷上了影片中美貌女子的V字领裙装,尽管难度重重,母亲还是凭借她的巧手将那梦想变成了现实,让我欣喜若狂。她的手艺似乎总能超越时代,当我还在摸索如何织围巾时,她已经驾轻就熟,甚至在那个年代,她就已经懂得如何织出时髦的毛衣、毛裤,让我惊叹不已。
母亲常说,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用她每天喝的茶水轻轻喷洒在我的发丝上,再细心梳理,然后戴上她早已准备好的小花夹子,走在街上,总能得到邻居们的赞美。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是母亲的爱与陪伴伴随着我。
母亲,您一生辛勤,默默承受了无数艰辛,却从未有过一声抱怨。您的坚韧和智慧,是我们永远的骄傲。您的每一份付出,都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