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人的故事(八十五)
邹星枢‖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那束光】 李东川摄
只要是有人在的地方,再黑暗的天空也有北极光一样的光亮闪现。再邪恶的环境,人性的美也不会完全泯灭。再漫长的冬季,也挡不住对春的思念。
——摘录本篇语句
八十年代初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与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我印象最深的小说。今天我的生活真的步入了“晚霞消失的时候”,不由得又想起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的清平湾里有头他久久挂牵的红犍牛。我的清平湾里有我至今都能清清楚楚想起的那匹看到就开心的枣红马。
我到园艺场的第二天就注意到它了。不,可不仅是注意到,也不仅是喜欢,而是眼睛都舍不得离开的简直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喜欢!它浑身油光放亮没有一根杂毛,四腿是细长的身子也是细长的,它站在那里好看,走起路来样子更是好看,四腿协调得那真叫一个帅啊!这种体型的马是我在电影和照片画报上看到过的最漂亮的那种。
出于喜爱,我经常溜到马棚里去看它,一拉溜好多匹骡子马。我走到枣红马跟前,开始稍远地看它,后来就试图接近它。
马是有灵性的。从它的眼睛里我也慢慢看出它知道了我对它的亲近。后来我就试探着慢慢伸出手摸它的脸。它眨眨眼没有躲开。它接受了!
以后再去我一进马棚它就提起前提跺跺地,分明是在和我打招呼。我高兴极了。我胆子越来越大,后来竟敢搂搂它的头,有时甚至还将我的脸贴到它脸上,它也不躲开。
后来我发现它的肚子变大了,体型不再像过去那么苗条。我为它的变化很失望,但没过多久才知道它是怀孕了。我就暗暗期盼并且问饲养员,它生出来的小马是不是也像它?饲养员说有八成吧。果然不假,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了它的孩子,它没有让我失望,紧贴着它身边的也是匹很漂亮的小红马。
我自己觉得我已经是它最好的朋友,而且也自信它也早拿我是它的好朋友。
有一天我正在十六方(离场部很远的一个地方)干活,枣红马拉着车化肥来了。卸完车赶车师傅坐下来休息一会,我就提出能不能让我骑一下?赶车师傅也知道我喜欢这匹马,当场就缷下马套说你骑吧,只要它让你骑。
我接过缰绳牵着它走了几步。枣红马很听话地跟着我走。我觉得没问题了,轻轻拍了它几下,按着它的腰跳到了它背上。它好像很吃惊我要骑它,我学着电影上骑马的样子双腿夹紧,嘴里喊着“驾!驾!”用手拍它的屁股。枣红马开始了走动。这怎么能过瘾呢,我就使劲拍它屁股,双腿也使劲夹紧它肚子,“驾!驾!”的喊声也更高。枣红马开始了奔跑。开始我还有点紧张,双手紧抓住马鬃竭力稳住自己的身子,很快就跟上了它奔跑时一巅一巅的节奏。当时我得意极了。自豪地大声喊叫。
可惜我得意的时间并不长,枣红马开始给我开玩笑了,它放着一马平川空旷地方不走,偏偏在那已经有差不多一米高的柳条棵子里跑。分明是故意让那柳条枝子打我的双腿。我咬着牙任它打。
枣红马大概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它又一拐弯紧靠着一排防风林跑,我终于草鸡了,我的腿可扛不住树干的磨碰,弄不好一下就给弄残了,只好一片腿自己将自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远远看着的驾车师傅和我的同伴们都被枣红马的调皮与聪明逗得哈哈大笑。气得我对枣红马大叫:“你这个家伙真不够朋友!”
史铁生没有谈他与其他知青的故事。我的清平湾里有很多知青们之间的笑话。
刚到园艺场的那年冬天,领导抓阶级斗争教育特别紧,一时我们每个年轻人对阶级敌人搞破坏的警惕心都特别特别的强,还几次被半夜紧急集合抓特务,说是哪里哪里发现了特务联系放出的信号弹。
于是每晚都有两人在场里值班巡逻。这晚我与张希楹值班。因为初冬的夜又长又冷,我们两人就事先准备好了蔬菜(好像是西红柿)、油盐、面粉、花生米和锅、柴。巡逻到半夜肚子饿了,便点火里做出一锅疙瘩汤。
做熟了后觉得汤太热了,就又在附近转了几分钟,回来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每人盛了一碗狼吞虎咽地喝下。不料待盛第二碗的时候,张希楹突然惊叫疙瘩汤怎么是红的?!我是色弱本来对红绿不敏感,让他这一说也觉得汤是红的了。
怎么回事?是不是刚才有坏人下毒?要不为什么会是红的?于是我们越想越觉得可疑。小心不为过最后毅然把大半锅汤给倒掉了。接下来我们两人都开始心里犯嘀咕;刚才喝下的那碗汤可是有毒的。这可怎么办!想到这里张希楹开始说他肚子痛!他这一说我觉得肚子也痛了!
可这深更半夜地找谁去?只寄希望幸亏我们只喝了一碗,估计还不至于被毒死。决定坚持到天亮再找医生。巡逻是没有力气了,我们俩就捂着肚子倚着树蹲在那里,然后埋怨自己为什么喝汤前不仔细检查检查再喝。
就这样蹲了大概一个小时,渐渐肚子也不觉得那么痛了,开始分析坏人下毒的可能性有多大?分析来分析去觉得即便有坏人,就我们两个破知青也没有下毒的价值啊,是不是我们自己神经过敏了?想到这里肚子也一点都不痛了,开始为倒掉的那半锅疙瘩汤惋惜了。
最后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的判断占了上风。
哇塞!准备了一阵子忙活了老半天好容易熬出来的一锅疙瘩汤,就因为我们自己的瞎怀疑给白白倒掉了!还跟真的一样闹了半天肚子痛!
以现在的话说那真是一对XX!
为了弄清到底怎么回事,第二天张希楹问有做饭经验的已婚妇女,回答是:
花生米煮熟了就是发红,再说西红柿本来就是红的啊!
我的知青生活里的一个侯老头,没有史铁生笔下人生那么丰富多彩和正直善良可爱的“破老头”,却正是他甚至只是他的一句话却激活了我对某种人性的思考和怜悯之情。
老侯是园艺场马车队的饲养员。也就五十多的年纪却像六十大多的苍老。身材矮瘦皮肤黝黑,浑身上下永远是脏兮兮的,无论坐着还是站着总是弯曲着腰。平日无话好像也没几个人搭理他。我爱没事到马棚里看马吃草,我不主动说话他就像根本没看到有人进来一样。
有一天一个什么会,我们队与马车队少有的在一起开会。开会前照例是先一阵胡说八道热闹一番,互相取笑逗着玩。有一个被取笑者下不来台,就冲着也跟着笑的老侯说“你还笑,咱再不济也不像你老侯没出息:一辈子狗x猫x没见过!”引来一阵大笑。有人就接着逗:你咋知道人家老侯没出息,明的没有夜里跳墙的事就没干过?是吧老侯?”又一阵大笑。
大家哄笑着自然眼睛都转向老侯。不料平日都是嘿嘿一笑并不答话的老侯今天不但没笑,反而摇着头苦叹一声:
“哎,我这辈子还真是连狗X猫X都没见过!”
那时候我才十七岁,也跟着哄笑,只是觉得他混得是挺惨的,并没有多少感慨。所以过后也就忘了。
几年后我结了婚,有一天突然想起了那天老侯苦涩的摇头与叹息,顿觉一个人打一辈子光棍是多么大的人生失败,是对人性的多大的长时间的巨大折磨啊!老侯也是人啊,却连狗啊猫啊的正常权利都没能得到过!
后来我有了儿子,产假结束爱人必须上班,没办法就托人在村里找了个老太太来看孩子,管吃每月只花三块钱。
闲谈时听老太太说老伴早已故去,我立即想到何不将两位老人撮合一下。但那时候的我最讨厌电影里媒婆的形象,这怎么办?于是就装作无意中说场里一个单身的侯老头,同时捎信将老太太的事也告诉了老侯,心想接下来就看她们自己的了。
事情比我想得还快,不几天老太太说有事不干了。又不几天传出老侯要娶媳妇了,要娶的就是这个老太太。
据说那晚很多人挤着去听房。
第二天上午我肚子不舒服去场部医务室拿药。场医是出了名的好说笑话,曾对妇女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谁屁股最白我最清楚”,气得女人们都骂他王八蛋,但也并不真生气。
他人缘很好平日医务室里总是有人去说笑。我去时他正活灵活现地讲着“刚关上门老侯就要上,老太太拿拿捏捏推却,说‘算了我正牙疼’,老侯说了声‘牙疼吃药’就饿虎扑食压了上去了”。
天下的事就那么巧。场医这句话刚刚落音,老侯领着老太太就一脚迈进来了。场医问怎么了老侯?刚娶了媳妇一晚上就累病了?老太太捂着红肿的半边脸说“我牙痛”。在场的所有人竟比部队官兵喊口号还齐整地脱口喊出同四个字:
“牙痛吃药!”
然后就是一阵捧腹大笑。而老侯夫人还摸不到头脑地看着众人说“真的,你看我脸都肿了。
“所以才要牙痛吃药嘛!”
又是一阵开心地大笑。
场医在那里一本正经装模作样地拿药给她说:“给,咱昨天晚上就给你准备好了。”
此后好长时间人们一见到老侯就说:
“牙痛吃药!”
这些颇有意思的美好记忆可是发生在那个最最不可思议的年代啊,现在会有哪个思维正常的老人想让自己的子孙,再回到那个贫穷险恶的时代呢?
可从那里走过来的人每当回忆起来,总感觉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老糊涂了?包括身体受到终生伤害的史铁生。
我想我们都不糊涂。正在打出以上文字的此刻,我想这可能是一种人本身自带的自我保护机制,即:
“自愈”功能。
不是“自娱”也不是“自慰”更不是“自欺”。
是“自愈”即“自我疗愈”。
即大脑或精神方面的器官会自我本能地分泌一种物质,可以不惜矫枉过正地抚平、修复或消解乃至美化曾经历过的、并不美好的东西或心理创伤,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或者有选择性地拆解了记忆的全部。
“自愈”只对心地善良者或者追求善和爱的人有效。
而那些不相信善和爱的人与此无缘。他们只记住仇恨。
同时从事物的客观上来说,只要是有人在的地方,再黑暗的天空也有北极光一样的光亮闪现。再邪恶的环境,人性的美也不会完全泯灭。再漫长的冬季,也挡不住对春的思念。
只是时间问题。
周八百汉四百,都不过弹指一挥间。
在这里的十三年里我曾扛着整口袋粪肥深一脚浅一脚的跟在牲畜后头耩地的漏斗撒粪,风一吹满脸满嘴里都是粪沫。
我曾经一天挖几十个树坑种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二十年之后我终于选择了写作,但我没像王开岭先生所说的那样“凡特别尊重生命与自我的人,在开始一项长期劳作前是需要匹配一个强大的理由的。他必须坚强,饱满,须有不俗的精神魅力和荣誉性,符合主题的审美心理和价值需求——唯此方能与事业牢固悠久的支撑推动力。”
我只是为了逃遁,最多加一点爱好。我是选择写作为谋生手段的。
然而,令我自己也想不到的是,也正是这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让我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后半生的追求和态度:
那天我回到园艺场怀旧,突然发现这一望无际的黄河故道,当年除了一种叫茅草的东西什么都不长的沙漠,竟然变成为各色花草茂密的绿洲,俯身抓一把土,发现土质也已经开始变黑变肥!
我的热泪顿时夺眶而出一滴滴砸在地上,这就是说过去我在这里种下的上万棵树起了作用,这作用对子孙后代已经可以肯定不是“负数”,我已经可以完全放心的为此而骄傲和自豪了!
但几乎同时突然又想:我今天或者后天所要写的每一个汉字,是不是也像这些树一样对后人肯定是“正数”呢?我不知道。我不敢保证。
那万一要是“负数”怎么办?这教训可是既多见又惨痛的:“批胡风”,“反右派”,“全民大炼钢”铁,“大跃进”……这些“负数”的教训还不惨痛吗!
就在那一霎间蓦然惊醒:
必须对今后写下的每一个方块字格外小心了!对每一件作品都要问一声百年之后对子孙对人类“正数”还是“负数”!我知道这是多么不易啊。
这要舍弃好多。这要付出代价。但是必须如此。为了鼓励自己鞭策自己义无反顾,我跪了下去,手捧黄土以大地的名义起誓:
从这一天起必须对自己的“职业”进行认真的人文理性思考,做好最难最坏的精神准备。

【晨曦】 李东川摄
从善良的本性出发,永远不明白邪恶能至如此地步,就和邪恶永远不相信善的存在一样。
——编者的话

邹星枢
1946年生于济南故郡黑虎泉畔,性喜清涟而不耐浊浑。曾上山下乡、进工厂多年,创作的二十几部大戏在国家中心期刊及省级专业期刊发表或剧院演出,三次搬上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教学舞台;《绿帽子》由五十年代著名导演张琪宏和北京人艺、中戏及国家话剧院等艺术家在北京公演;中、短篇小说散见于《钟山》、《雨花》、《清明》、《百花洲》等文学期刊,晚年致力于随笔及诗歌探索。拍摄电视剧几十部集。 作者刻意追求的,无不是尽力摆脱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定式,努力探索共同人性中爱与善的张扬和恶与恨的批判、以及人的尊严以及生命权利的普世价值,至今致力于人的灵性和精神探索。斗争或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定式,努力探索共同人性中爱与善的张扬和恶与恨的批判、以及人的尊严以及生命权利的普世价值,至今致力于人的灵性和精神探索。

【聊斋志异.小翠】 于受万画
编辑:李东川
2024年7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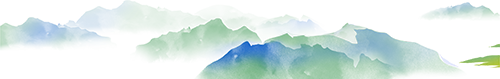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