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学工、学农、学军
陈殷山
当年大讲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开始了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
学农是最早最经常性的活动,分夏秋两季,夏收拾麦穗、秋收拉秫秸。当麦浪滚滚,天象下火一样的时候,农民伯伯们开镰了,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开始了所谓的学农。
出发前,首先买上二分钱的山楂片塞进酒瓶子里,再买一包糖精放上少许,倒满热水后瓶口塞上软塞子,戴上五角形的斗笠,就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六月季夏天,身热汗如浆。
每年的麦收时节天特别的热,骄阳似火,仿佛空气在燃烧,往往没有一丝的风,同学们热的汗流浃背,小小的脸庞上汗流的就像一条条小泥沟。田埂之间没有树,休息时想找点荫凉实在困难。幸运的时候,田埂上会有少量的蓖麻树,这种草本植物的叶子呈多角阔叶状,叶梗是空芯的,从枝干上折断后拿在手里就像打着小伞一样,多少有点荫凉,即有趣又实用。
劳动时常常盼着快来点云彩,刮点凉爽的风,好容易盼着来了一块云彩转眼就眼巴巴地看着它又飘了过去,此时会感觉到更加的热,热得同学们连一点逮蚂蚱、捉蝈蝈的兴趣都没有了。
瓶装的山楂水很快就喝没了,正口干舌燥之时,突然农民伯伯挑来了绿豆汤,同学们便一哄而上,转眼间桶底就朝天了。
拣麦穗最大的感受是快乐并痛着。
学工时的年龄就稍大些了,从初中才开始,主要是在校办工厂里做胶垫,单人和几人围着一个手动转盘式的压模机(大概叫这个名称),用力地转动,将模具里未成型的橡胶原料加热挤压成管道垫圈。气味大,劳动强度也不小,时间一长弄得晕晕呼呼,下班后能把鼻头熏得黑乎乎的。
同学们都喜欢到矿上去学工,为什么呢?学技能是一方面,能够吃矿上的大食堂是诱惑之一,可以像大人们一样,到饭点的时候拿着饭票、缸子、饭盒叮叮当当地去大食堂,想吃什么买什么。矿上的食堂在全矿的所有食堂里规模最大,二立井、三立井、煤台的食堂次之,规模也不小。矿上的食堂因矿机关、一立井在这里,人多、菜的花样也多,全用大脸盆盛着,最多十几种菜。馒头、花卷、油饼、稀饭、玉米粥轮番着上来。当矿上开展夺高产活动和春节时,还会组织家属们去食堂有偿的集体包水饺。全矿各食堂二十四小时开放(煤台食堂除外)啥时候都有饭,只不过饭点时品种多,菜、稀饭热一些,平时品种少饭凉点。普通菜的价格是五分到二毛,三毛钱就可以单独炒小炒。五分一碗菠菜汤、油菜汤,一毛钱买一个过油的竖着切成四瓣的大茄子,二毛钱买块广东肉。
想学点本领的最喜欢去的是机厂,因为那里车、钳、铆、电、焊都有,最受青睐的是钳工和电工。
印象中我们班没有人去过机厂学过工,学工总的次数也很少,印象颇深的是1976年秋天去西临洪山铝土矿学工。
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同学午饭后偷偷去一个叫磁石湾的水塘里洗澡、游泳。那时没有什么泳衣泳裤的,大家脱得光溜溜的非常痛快地跳到水里。这水湾是挖铝矿石形成的乱石坑,由雨水汇积成湾,到处都是有角有棱的石块,稍不小心就会划破脚底。正当大家玩得高兴,突然有人喊:“王老师来了!”只见班主任王世利老师脸色铁青地从东边匆匆赶来。北岸的同学见状慌忙上岸用衣弊体,扑腾到南岸的一位同学因衣服在北岸,水性不好无法游回北岸上来,顿时在南边浅水处慌了手脚,上来也不行下去也不是,正焦灼之间,只听王老师大喝一声:“上来!回来!”这位同学没了办法,只能悻悻地从水里爬上来,一览无余的赤条条、光溜溜围着狭长的大湾走了好长时间,转了大半圈才回来。我们看着想笑又不敢笑,只能死憋着。
这件事让一向斯文、很少发牌气的王老师大发雷霆,事情捅了天,校领导很快就知道了此事,董书记把几个同学弄到了校长室训话,声色俱厉、严加痛斥。大家惶恐的不行,紧张的六神无主,知道捅了大蒌子。 事情为什么如此严重呢?是因为那时是领导人逝世的治丧期,大概还有二、三天未过去,这期间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好歹下水湾洗澡不同于唱歌跳舞,性质不太严重,加上当时政治气氛有点放松,我们躲过了一劫。
到军营里去学军并在营房里住下,亲身体验部队的军人生活,是我们这个年级的荣幸,这次学军活动在我们职工子弟学校里是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这样的机遇在全校的历史中只有这一次。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环境下能去军营那是高兴地不得了的事。
打好背包,带上行囊,徒步十几里路,来到了地处杨寨王母山上的炮兵营地。一进营地的场地上,整齐地摆着数门大炮煞是震撼,不知是加农炮还是榴弹炮,第一次看到真大炮,同学们倍感兴奋,欣喜不已。
军营里的生活严肃而紧张,处处有严格的纪律和制度。我们和军人一样,当“滴滴哒哒”地起床号响起时便迅速地起床,熄灯号吹起马上熄灯。但熄灯以后,同学之间的恶作剧就开始上演了,你扔袜子我扔鞋互相打闹,还有人将臭球鞋愉愉地放在睡着同学的鼻子边上。
我们睡的是地铺,在房间的中间东西向用二层红砖排成长长的一行做隔断,从红砖到墙边,里面铺着干草,再铺上自己带来的被褥。一天,另一班的某位同学发现了某种可恶的寄生虫,大家惊慌失措、避之而不及,引起了一阵骚动,纷纷将被褥拿到阳光下暴晒。
早餐是红萝卜咸菜加稀饭,中午和晚上是汤汤水水的大锅菜。上课听讲军事知识时坐着二块砖挺胸昂首,认真听课,久了硌的腚生疼。看电影时要挺直腰板地坐着,双手放在膝盖处,整齐划一。
听说夜里会紧急集合进行夜行军,同学们热切得期盼着,但不知是在那一晚上。突然一天凌晨,在寂静和安宁的营房里紧急集合的哨声蓦然响起,因有时间要求并且不允许开灯,同学们紧急起床,慌慌张张地穿衣服打背包,背包要求打得像军人的一样,绳带要捆绑成井字型。因当时睡的是通铺,在黑暗里慌乱中找不到鞋和衣服的,穿错鞋袜的,蹬错裤腿的,穿上别人裤子的,系不上鞋带的,背包打成铺卷的......大家乱哄哄、乌鸦鸦的像羊群一样往门外跑。
“立正一一向右看齐!”“报数!”同学们的脑袋像拨浪鼓一样:“1、2、3、4、5......” 部队带队的王排长厉声地喊着,然后迅速交待夜行军的时间、任务和目的,以及行军中的口令:防毒。夜行军中大家急匆匆、气吁吁地跑,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反正就是拚命地跟着前面的跑,跑累了肚子疼掐着肚子也要跑,军令如山倒,谁也不愿意落在后面。
跑着跑着前面传来问声:“口令?”“防毒!”记得住口令的回答正确,记不住的就以讹传讹变成了“黄土!”由于人多体力不均,结果队伍越拉越长,女生们大多拉在了后面,口令就越传越乱了。
说起到口令,我想起来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里面美国鬼子的口令:“口令?”“古伦姆”“欧巴。”想想好笑。
那时候最想摸摸真枪,看到哨兵端着冲锋枪威武地站岗,心想啥时候能练练打枪啊。
早晨出早操,上午学知识,下午练队列,一天到晚枯燥的很。经过一段时间后,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来了,开始拿枪练站姿、卧姿、瞄准了,那时感觉枪很重,个小的、女生们拿着有点费劲。练习瞄准有一个口诀:左眼闭右眼睁,标志缺口对准星,三点成为一条线,屏住呼吸钩板机。
记得有趣的一件事是练习卧姿持枪瞄准,长时间趴着一个姿势有点受不了,全身上下硌得难受,不知那位同学突发奇想,竟在裤腰带下敏感部位的地面上挖个小坑,结果效果明显,男生相互逗乐争相效仿,女生们见状纷纷羞涩地掩嘴而笑。
很快军营生活就要结束了,部队允许我们进行实弹射击,检验一下军训的最后成果。那一天和煦的阳光普照着大地,风清气爽,天高云淡。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一、二、一”喊着、唱着革命歌曲沿着张博路北行。
到了靶场,在部队指挥官的指导下分别在几个靶位进行实弹射击的准备,每人三发子弹,大家轮番上阵。平时同学们盼着打真枪,真要打的时候还是有点心惊胆战,大多数人紧张兮兮的,女生们更是如此,跺着脚搓着手稳定着情绪。后面还没打的赶紧问刚刚打过的:“怎么样?害怕吗?”有的女生由于害怕,迟迟不敢搂扳机,在发令员的再三敦促下,才勉强地开枪,只打几环的甚至跑靶的都有。自动步枪的后坐力还是挺大的,放了第一枪震得肩膀疼,有了开第一枪的体验,后面的两枪就放松了好多,每人紧张的“叭、叭、叭”三枪结束,然后等待报靶。
遗憾的是,我忘记了自己打了多少环。 十几岁的孩子就真枪实弹地干过,那份自豪感是没有参加过这种体验的孩子感受不到的,也是他们很羡慕的吧。 回到学校后,学校领导安排我们年级在排球场上进行队列训练表演,向左、向右转,齐步走......。高亢的口号声、嘹亮的歌声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军人般整齐的正步走,赢得了学校领导、老师及其它年级同学们的一片掌声和赞叹声。
在部队短暂的训练使同学们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严于律己的好作风。我们在部队学会的把被褥叠成豆腐块一样的方法,我在家里还坚持了一段时间。
白驹过隙,岁月如梭,几十年前的“三学”活动至今历历在目,回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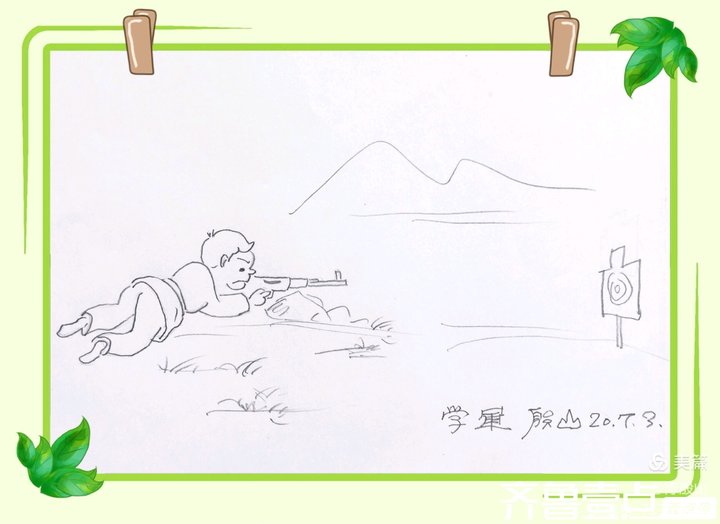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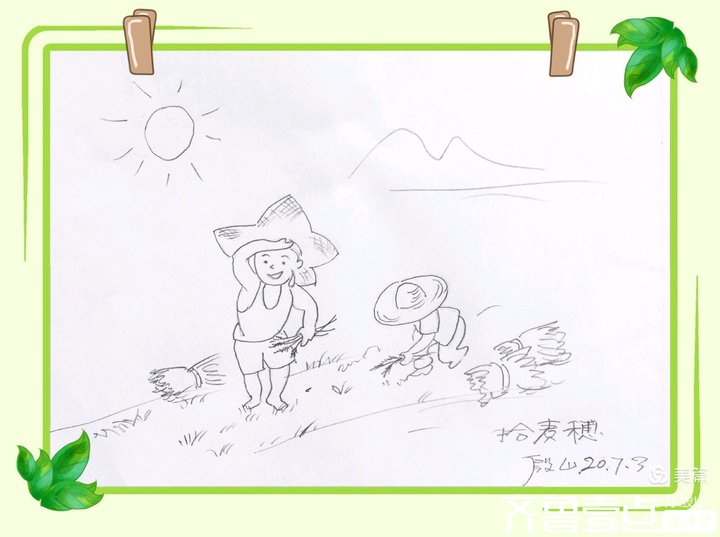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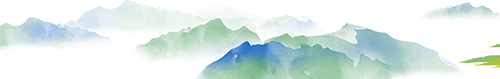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