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蜉生往事三则
赵远智

三
信使是奉派晓喻使命的人。雁阵是季节的信使,落叶是秋的信使,生死置之度外的信差是道义的信使,鸿雁传书,人言为信,仅以此而论,信使无疑于人质了……
小时候,极为羡慕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可以有秘密,有上着锁的抽屉,那是天机和密勿之地,是六耳不同谋的缄口黙言之处。其实,说到底是羡慕成年人有属于自的信件。
世界上只有一处地方神圣的不可有秘密——那便是向神父忏悔、苛求灵魂救赎之时,灵魂洁净的如浴后,期望秘密的降临,无异于容许藏污纳垢。
我不以为然;仅就信件而言,有其私密的成分,同时也具光风霁月的磊落,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简单归类,更有混淆视听之嫌。
还是小时候,对邮递员职业崇仰的不行。街上一有邮递员出现,便循着悦耳的铃声追撵一阵。
邮递员一手操把,一手拿着待发的信件,呼叫着收信人的名字。
每次路过邮局大门,总横竖往里看一会儿,如果赶上分发信件的时辰,算是饱了眼福:一排排邮递员说笑着各自东西,象晨间飞出的一簇簇鸽群,忽而展翅翱翔,忽而上下翻飞,忽而从天际的某块云间疾速而出,忽而又在某处楼宇丛中遁迹而去……
全绿色邮递车将春的元素尽收眼底,即便秋冬之际,也让人赏心悦目。加之邮递员的驾控水平高超至极,双手根本无需扶把,一圈圈倒着飞轮,车子也就稳稳当当支撑在马路沿上了。待邮递员又骑上车扬长而去,陶醉在树荫下的收信人方才打开信件,如醉如痴看个究竟。
然而,那种局外人的苦涩百爪挠心,刚才还和你说说笑笑,刹那间就沉下脸不再和你言语;凑不上身,又不甘于对信件的秘密一无所知,只好佯作若无其事样子观察阅信人的神情,似乎亦可读懂一点点内容。
那个时期刚过狗猫也烦的年龄,待狗猫能偎身了,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在哪里……
七十年代初,开始读高中了,人际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逆转——有女生的步子在身边轻蔓起来,说话的声音也柔和了许多。那时,余光和嗅觉的使用率极高,健硕的心脏经得住小鼓乱锤。家境好点的,开始穿衬衣、凉鞋、球裤了……时常见他们抹着油晃晃的嘴角走出附近的大众饭店,然后骑上自行车一骑绝尘直奔学校而去……
最有扮相的着装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军区大院的那帮人中龙凤;白衬衣、黄军裤、黑条北京布鞋,另搭洗的发白的军用挎包,当是火红年代最风光旖旎的一幕了。
可我班同学的鉴赏力远在这些凡规陋俗之上;他们的裤子补丁叠加补丁,上衣是肩领阔挺的苏式将校服外套,用破败不堪的国防服终年罩着将校服,可谓独具匠心——一切貌似漫不经心,实则极具无所不包的低调美感。
颇感失望的是,初、高中五年下来,竟未给某个女生说上一句完整的话。无形的大山横亘其间;壁垒森严,有一点的造次,就会遭到枪林弹雨的阻击。
马上要毕业了,望穿秋水,也没等来哪怕一张便条的一角。其实,男生的信也没接到。那时,人和人的交往极不善文字表达。尽管可以罗列一大堆鱼传尺素、青鸟传书的美谈,将书信称作书札、手札、尺牍,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事事远离这些雕饰文心,一味地扎聚藩篱,让原本轻快的生活人为复杂起来……
尤为让所有人失望的是,直至毕业跨出校门,班上男女生也没拍一张合影,若想再端详某张青春的姿容,已经遥不可及、比登天还难了。
锣鼓和鞭炮声中,终和那个青涩的年代相拥而别。
没成想,七十年代中叶的生活骤然发生了猝不及防的巨变。
下乡了——
屁股在老乡家的炕沿还没坐稳,一把把同学来信便紧随其后追上门来。起初,读得心潮澎湃、热泪沾巾。再后来,兴致锐减,回复的也有点拖沓迟缓起来。
出工、浇地、施肥、麦收,每一项生活内容都疏忽不得,都比回复信件重要百倍。
最要命的是,雨季刚过,每天要跑一百多里路往地里推粪;车辙漫过半个胶皮轮子,弯下的腰已超四十五度。所用的气力都已消耗殆尽,只需一分钟功夫歇歇身子,便可呼呼入睡——筋骨似已散架,需要重新组合分装,方能再次上路——
这时候兜里如果揣一封同学来信,那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快事。打开同学来信,倍感充实和满足;放慢频率节奏,字斟句酌默念着那些情深意切的语句,仿佛气血在汩汩回流……
这时想起古时《季布重诺》的典故,里面一句“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古训,让人对无价友情记忆尤深。特别让人感慨的是,信件开篇的那句老话、套话,咀嚼一下再行吞咽,倍感亲切和温情脉脉,直至暖透胸腔:
远智同学见字如面……
好一个见字如面!
这般惜墨如金的概括,这般点石成金的笔触横姿,当是中国文人间最具操行的练达文字了。
多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无意中聊起了过往,刘堃、付建民他们说,还有你的信件保留着。
我万分惊诧,屈指算来,几篇学生年代的小文,竟在人家箱底置存了半个世纪之久,仅凭这点,我辈也当获季布一诺的华彩锦章了。心存感念才是,怎忍心收回五十年前的信件呢!
“信和文章你们留着吧!”我颤巍巍由衷地说。
“好歹做个纪念。信件里面的东西真的已经不属于我了……”我不是客套,赶忙补充了一句。

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我收到过许多颇有来头的公函信件,上至省委领导办公室,下至乡间黎民百姓,种类多多、不一而足。让我最难忘怀的还是同学间的那几封沉甸甸信件。
本是同学间信件往来的寻常往事,却在心里逐浪排空,搅得周天寒彻。
与同学相聚的那个晚上,回去后便再难入睡,索性翻箱倒柜找出同学间的来信,摆满一床,按起止日期分拣起来,再后来干脆就饶有兴致一封封读了起来;从刘堃的谨严深沉,实则格高意远;到付建民的音和调低,实则高屋建瓴;从韩立泉的广识善缘,实则心性高远;到袁宏征的率性淋漓,实则奇石嶙峋;从马俊的谦和周至,实则宽严相济;到焦秋生的洒脱果敢,实则碧心如洗;从范围的豪气爽致,实则柔心慈蕊;到周焕涛的鞭辟入里,实则汪洋恣肆;从李济伦的纵身一跃,实则后力勃发,到从孙向阳的才华横溢、实则温和谦恭……
一张张可亲可敬的面孔萦绕不绝,在眼前、在脑海中浮现——
见字如面!
我轻声附和着这四个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信件,是同学间至臻至纯、弥足珍贵的礼物,是珍贵至极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感到疲惫的心灵中又布满一处处歇脚的驿站。假如生命中还有来生,这些信件一定是我再次上路的包裹行囊,负重前行的辎重给养。
知青岁月第一年后,与村里百姓的生活已经无异;国家已不再有粮油供应,所有的开销全仰赖自己解决。笛子、口琴、二胡声已成了远方生僻的异响。几只母鸡几乎无蛋可下,公鸡高亢的催鸣声却不见示弱。两头小猪崽距离分割过年还很遥远,但啼饥号寒,栉风沐雨的紧张生活仍在继续。想必大田里终日的操劳,同学间的来往信件也少了很多。说心里话,每次路过公社小邮局,我都会搭讪两句,问问有无来信,也不知道其他地方的知青怎样抵御眼下时光的煎熬。每次见我,邮局的人总是摇头;我也不抱什么奢望,只是走着走着,就有路径通向了这里……
绝望之时,说不定就是反弹之日。
这天,邮局的人叫住我,说是有封挂号信。我顿感好奇,不记得有什么重要信件需要挂号邮寄。我拿过信件,明显感到比平时的厚道很多,急忙打开来,发现就一张信纸,再打开叠了几层的东西,见是厚厚几摞邮票。怎么还寄邮票?我再看信件,方知道同学已在部队复员,补发的那点生活费,他全买邮票了,后语还特别嘱咐,别怕麻烦,多给他写信,他现在最盼着的就是我的来信,尽管写,邮票的钱他全包了。
我的心猛然抽搐了一下,知我家生活拮据,日子有点难,居然连回复的邮票也一道寄来,这该是一份怎样的情谊!
我的眼睛有些发潮,泪滴禁不住滚落下来。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当年的邮票我一张没用过……
直想一次次呼唤老同学的名字;以唤回那个视情谊为和璧隋珠的年代。
对我来讲,那个时代清心寡欲、贫馑的几乎一无所有;
对那个时代而言,我有时时没寄出邮票的相伴,一生,了无所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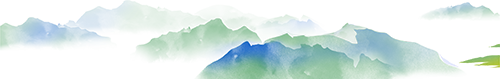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