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文/张庆林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是我五味杂陈、黯然失色的秋天。在这个秋天里,我告别了色彩斑斓的大学梦。
刚刚回到家那一刻,全家人被我沮丧的神情惊呆了。母亲一边帮我收拾被褥、书籍,一边小心翼翼地向我打探着消息。“考了吗?"我面对急切等着我回答的老娘,心里像亏欠她什么,依旧呆呆地站在那里,什么也说不出来。坐在椅子上的老父亲,显然被我失魂若魄、有问无答的神情激怒了,他大声地嚷嚷着:“考学的事,到底怎么样了,你说话呀,读书读傻了!”面对着上级无限期延长大学招生考试的通知,我又能说什么呢?
刚刚回到家的那个晚上,我躺在炕上,两眼涩涩的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依旧是刚刚填好的报考志愿、体检表和那让人烦恼的通知。
三年前,我初中毕业升高中时,年过半百体弱多病的父亲,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吞吞吐吐又小声地对我说:“小儿,你看我浑身是病,咱家人口多,挣工分的人少,日子实在不好过,咱就别考高中了吧……"父亲说着,情不自禁擦了擦他那深陷的眼晴。我从父亲无奈的表情里看出了他的为难和自责。我明白,善良慈祥的父亲,从我上学起,一直支持我读书,今天他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是有多为难下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决定不再继续读高中。
这件事,虽然是我和父亲偷偷作出的决定,但是,还是被母亲察觉了。一向做事大胆果断,说一不二,尤其是把我读书上学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母亲,听说父亲不让我考高中了,立即就火了。她当着全家人的面,拉下脸子,不容分辨地说:“儿子考高中的事,我把话说清楚,他不但要考高中,还要考大学,家里的困难再大,也不能耽误他一生的前程。"母亲说到这里,流下了眼泪。一向好人主义的父亲,心里明白,只要是母亲定了的事,就决不会改变,于是,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再也没有说话。后来,母亲请来了一位县里的驻村干部,陪着父亲吃饭聊天,顺便做了父亲的思想工作,解决了我上高中的事儿。
我的母亲,从我念小学开始,她看到我得的一张张奖状,以及别在我衣服上的二扛、三扛的的队徽,就拿定了供我上学读书的主意。母亲在家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只要我能够一级一级的考上学,她就是拉着棍子要饭,也要供我。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遭遇了特大自然灾害,家家户户的生活都很困难。我家由于七口人吃饭,只有父母二人挣工分,父亲又体弱多病,生活就更加困难。于是,家里吃饭穿衣的担子,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她为了让我们吃饱饭,想了很多办法。她曾经起早贪黑地卖大包子,卖窝头,卖茄子菜。也曾经在村头的公路边上的简易房里开茶馆,给拉脚的人们烩窝窝头。尤其是一九六一年,当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她一个人壮着胆子,把家里凡是看得上眼的衣服、被褥,包了一大包,坐着闷罐车,去了山东南部山区的农村,用衣物换回来了一大布袋地瓜干。当一家人吃上地瓜干粥的时候,母亲累得来不及换下脏兮兮的,已经发出酸臭味的衣服,躺在炕上便昏睡了过去。
每到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去拿窝头的时候,看见母亲总是在给我蒸的窝窝头里,尽量地少掺野菜,而让我在家的弟弟妹妹喝野菜粥,那时候我也打过退学的鼓,但是,都被母亲声色严厉地给阻止了。我的母亲,那瘦瘦地脸庞上,颧骨明显地凸起来,脸颊深陷下去,那弯弯地眉毛下,一双深陷眼窝的眼晴,常常动情地看着我,拿着蒸好的窝窝头,走出家门我心里便涌起一股说不清楚是喜还是痛的热浪,眼泪便不由自主滚出来。
有一天,母亲把我叫到里屋里,小声地和我商量说:“小儿,你回家已经一年多了,全国高考考试也没有消息,你也老大不小了,要不就结婚吧?听媒人讲,给你介绍的这个姑娘,不但人品好,还长得漂亮。”我听着母亲那掏心窝子的话,心里想,娘是诚心诚意为我好,为了安慰我那颗烦躁不安的心,让我放下考学的心思,在家跟她踏踏实实过日子。说句实在话,娘让我结婚,也是她没了办法的办法。但是,我却觉得,我一旦结了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就等于把自己拴在了一个小家里,若是今后有了高考的机会怎么办?还有带病的父亲、母亲,为我读书上学东跑西颠,借借取取,遭遇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这一切,不都付之东流了吗?我不但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和条件,还辜负了一家人为我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想到这些,我就对娘说:还是先让大弟结婚吧,他读书少,下力又多,给他成个家,好让他安心跟娘过日子。娘听了我的话,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也就早早地给大弟定了婚。
在回乡务农八年多的时间里,我干过农活,跟着村里的基干民兵挖过河,在生产队的染坊里接过布,而让我受益最多的是参加了四年人民解放军,当了新闻报道员,特别让我高兴地是,在我即将退役的日子里,我举起了右手,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四年的部队生活,我收获颇丰,我仿佛长大了许多,好像又重新活在了一个充满阳光的激情岁月里。
退伍返乡后,我一扫高中毕业回家后,那段时光的无奈和彷徨,那段无颜面对老爹老娘的羞涩和消沉,那段不能面对突兀而至的,命运的陡转和挑战,我心中又泛起了追逐新生活的涟漪和浪花。我决心扎根农村,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建设新农村。
我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基层党组织的肯定和认可。一天,村里的干部通知我,要我去夏津镇一趟,说是镇里的党委书记吕光森找我谈话。说实在的,镇里的党委一把手,要和村里的一名平平凡凡的社员谈话,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于是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按时来到了吕书记的屋里。
吕书记是我县德高望重,工作经验十分丰富的的老干部。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找我谈活的原因和目的。我听了吕书记的一番话,简直感到吃惊,我做梦也不会想到,镇党委会让一位刚刚退役回家的青年党员,去接任我村的一位党支部老书记。我面对着这个完全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没了主意。我考虑了很久,才静下心来,对吕书记说:“您看这样好吗?我村的老支书,是一位在位多年,有着诸多工作经验的老书记。我是一位年轻的党员,您先让我在老支书的培养下,配合老支书工作,等我熟悉了村里的工作,有了工作经验,再考虑接任老支书的工作,可以吗?”吕书记听完了我的工作建议,想了想,觉得这样也好,既锻炼了我,又让老支书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自从吕书记找我谈话后,只有短短几天时间,我就干起了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我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解决村里的问题,改变村容村貌,当作我的大事,放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我积极努力地工作,获得了镇党委的肯定,村里群众的认可。可是,正当我努力工作的时侯,村里的一位亲戚告诉我,有人到处散布我的谣言,说我要抢老支书的工作,争支书的权。我听了亲戚说的话,笑了笑说:“你信吗?我现在不是在老支书的领导下,给村里群众出力干活吗?再说,我还等着考大学呢。”我说得亲戚也跟着我笑起来。
又是两年后,我以具备八年实践工作经验的条件,被推荐到山师聊城分院中文系读大学,镇党委,村支部热情地欢送了我。我从1966年高中毕业,到1975年上大学,这期间,读大学的迫切愿望,整整拖延了九年。而我的同窗,大部分老三届的高中同学们,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才有幸上大学,这期间整整拖延了十一年。这十一年是黄金之年,是立业之年,是走向社会,成就事业,奉献青春才华的最关键的十一年。但是,钟表却整整停摆了十一年。一九七七年对我们老三届的高中生来说,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年,也是圆我们老三届大学梦的一年。我们幸运啊,党又帮我们找回了曾经失去的岁月和年华。让我们这些老三届的莘莘学子们,在祖国中断十年高考,人才奇缺,建设四个现代化急需用人之际,通过迟迟到来的高考机遇,再圆了大学之梦,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我和所有的老三届的同学们一样,在大学毕业后的三十多年里,任过教,从过政,为党的教育事业,为党的县乡村基层党政组织建设,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做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简介:
作者张庆林,山东夏津人,山东散文学会会员,德州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山师聊城分院中文系,曾服役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中国火炬》《人大代表报》《今日文艺报》。《山东工人报》《辽宁日报》《山东教育》《德州日报》《德州晚报》《盘锦日报》《棉花地》:《济南头条》《半盏平台》《两可诗社》等纸刊微刊多家媒体平台发表作品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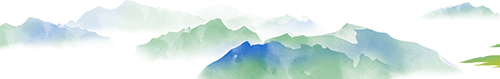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