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川巩家坞窑宋代白瓷探识
——山东淄博窑古陶瓷探索研究文章之四
文/图 魏传来
淄博窑,是我国古代北方较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也是著名的民间瓷窑。依据现有资料,淄博窑创烧于南北朝时的东魏,唐至五代开始繁荣,宋代达到鼎盛,金元、明清丶直至民国仍继续烧制,烧造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淄博窑在陶升华为瓷的生产力发展中一直位于中国北方的前列,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建国后,由于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淄博古窑址被一个个发现和发掘,千年窑火丶万世流芳的淄博窑古陶瓷辉煌终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笔者陪同中国故宫博物院古陶瓷权威专家耿宝昌(右)王莉英(中)在研究淄川窑古瓷
位于淄川区岭子镇的巩家坞窑,是构成淄博古窑址系统的一处重要窑址。巩家坞村古称荆业革瓦屋,是王洞庄的一部分(见淄川邱氏世谱》),明嘉靖二十五年《淄川县志》载名为革窊务,已独立成村。清初因巩姓居多改称巩家坞。其村地处淄川最西端绵延不断的冲山山脉,村西北山头便是淄邑名胜--形似野豹昂首而卧的豹山,海拔在350米。
巩家坞西接济南古镇章丘,南连莱芜茶业口,北有商埠周村旱码头,交通条件便利,是古代青州丶淄州通往济南府的隘口要道。这里有河水可提供充足的水源,有面积广阔的山岭提供森林木材燃料,地下有丰富的煤炭和烧制陶瓷器所需要的瓷土原料。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五代到北宋,这里一直窑火不断,瓷业发达,商贾云集。遗憾的是,巩家坞窑和淄博其它古窑一样,在历史文献上都查不到相关记载。
认识和了解淄博巩家坞窑,是一个历史的进程。1981年4月15日,淄博市文物局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曾组织对其进行了一次考察,采集了很多窑具和瓷器残片标本。2002年春,巩家坞村在村东修公路,发现古窑炉残址三处及大量残瓷碎片和完整白釉瓷器丶模具等。2014年5月和2015年10月,笔者在担任淄川区委宣传部《般阳文化》陶瓷文化研究课题组组长期间,参加了两次淄川区委宣传部组织的专家学者对巩家坞窑进行的实地考察丶调研活动,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笔者(左)与著名淄川文化学者韩云发先生(右二)等考察巩家务窑
随着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学术上也有很大突破。对巩家坞窑的烧制年代丶规模,产品种类及特点丶装饰手法等研究已颇见成效。
巩家坞窑址集中在村西北和村东两个地方。村西北范围极大,面积约30余亩。村东处稍小,面积近1亩。此两地因遍地都是衍,俯首可拾的古陶瓷丶古窑具碎片,被村民呼之为东“瓦碴地” 和 西“瓦碴地”。长期以来,人们在耕种土地时将这些陶瓷碎片捡拾到地头丶堰边,形成了多处“瓦碴堆”。同时,在一些高堰裸露处发现多处红烧土坑,系古窑炉遗址。
在学者们的眼里,这些跨越了上千年的古窑炉遗存,古窑具丶古模具残件和古陶瓷碎片,已经不是瓦碴垃圾了,而是我们赖以研究淄博窑的宝贵的实物资料;更象是几经浮沉、凝结了沧桑往事的一段段陶瓷历史,在彰显着淄博昔日的辉煌。

巩家坞宋代白瓷残片
采集和捡拾到的大量瓦碴碎片,经还原丶对比丶分析,其型制、装饰风格与磁村窑宋代窑址出土相似。其烧造时间集中在北宋(960—1127年) 前后。瓦碴碎片主要为窑具碎片与瓷器碎片二大类。(尚没有发现煤渣,说明这时还是柴烧窑阶段) 。
窑具就是用耐火陶土制成的在焙烧过程中对坯件起间隔、支托、承垫、保护等作用的器具。按用途可分为垫具和产品间隔具两种。垫具又称垫柱或窑棒,实心圆柱体。一端稍呈喇叭状,直径4-6厘米,长短不一,最长的可达半米。使用时将其安放在窑台上,顶端放置匣钵坯件,起支架作用。间隔具主要是置于坯胎与坯胎之间,作用是不使坯胎底足与另一坯胎直接接触而发生粘连。形制有单面三足支钉,环形七齿支钉丶圆形垫饼丶环形垫圈等。

巩家坞宋代窑址残片
值得关注的是,窑具中还发现有匣钵碎片。这说明巩家坞窑宋代时已普遍使用匣钵烧制瓷器。用匣钵烧制陶瓷是技术的进步。陶瓷坯成型后直接经火燃烧,会因烟尘而变色,装入匣钵就能防止这一缺陷,对白瓷烧造最为有利。从残片看,匣钵系用耐火粘土手工拉坯烧造,烧结较好。拼凑后大约高在20厘米左右,直径最大25厘米,厚约2厘米。底部中心处留一直径8厘米的圆孔。
发现的白釉瓷片数量最多。其品种造型十分丰富,主要是民间日常用瓷,还有少量的文具、玩具、娱乐用品及各种瓷塑等。器型主要有:盘、碗、碟、盏、盏托、渣斗、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瓶、壶、罐、钵、盆、水盂、笔洗、炉、香薰等,尤以多种多样的瓷灯最具代表性(见图)。

巩家坞宋代白瓷圈足碗
从这些在实地考察中采集到的大量残破瓷片分析,再结合附近村民们多年收集的完整器物标本,发现巩家坞窑宋代白瓷生产量很大,白釉系列陶瓷构成了巩家坞窑产品的基础。
这些白釉瓷器具有浓郁的山东乡土气息和淄川市井风情。造型虽然有点粗犷豪放,洒脱不羁,但不随意、不孱弱。风格朴实独特,充满了一种珍罕的雅拙之美。
巩家坞窑宋代白釉瓷器产品,圆形器普遍应用轮制法,异形器则用合范模制法,器胎体型较厚重。瓶罐类接痕明显,制作稍感粗糙,在器壁表里大都留有平行密集的轮纹。碗丶盘的器型中,往往有许多不够规整,其器物的足部造型基本上可以分圈足、饼足、玉璧足三种,从数量上看,以圈足为主(图)。从发现的大量内有支钉痕的残碗底看,巩家坞窑普遍采用支钉叠烧工艺。也发现有玉璧底叠烧工艺。

宋代淄川巩家坞窑白瓷灯(李永华藏)
俗话说:“人靠衣服,马靠鞍。”“三分长相,七分打扮。”此话道出了装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对瓷器的评价也是如此,当我们看到一件陶瓷器的时候,首先引起注意的与其说是它的造型、式样或坯体,毋宁说是罩在陶瓷表面上的釉,在瓷釉的装潢下,一件件陶瓷或洁白如玉,或彩色缤纷,十分美观。假如瓷器上没有挂釉的话,恐怕无论它的造型如何美、式样如何新,也会失掉这件瓷器的魅力,可以说,瓷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陶瓷的美观程度。
如果说,古代淄博磁村窑烧造的黑釉瓷以釉质晶莹滋润和色黑如漆而闻名一时,那么,代表淄博宋代白釉瓷风格的巩家坞窑陶瓷产品也曾独秀一方。素雅的白瓷是人们普遍喜爱的一个品种,虽然看上去没有艳丽的色彩,但在朴实无华中,它展示给人们的是那自然天成的美。
和淄博窑已发现的所有窑址生产的白瓷一样,巩家坞窑白瓷也并不是使用了在釉料中加进白色呈色剂的白釉。
白瓷是中国传统瓷器分类(青瓷,青花瓷,彩瓷,白瓷,黑瓷等)的一种。中国古代的白瓷产品,是选择含铁量较少的瓷土加工精制的较纯净的透明釉,将这种釉料挂于生坯上,如果瓷胎是洁白色的,入窑经过高温火焰烧成后就是白度很高的白釉瓷器了。因为釉是透明的,釉色因白润瓷胎的映衬而显出白色,故其所呈现的色是白瓷胎上的白,所以也称白釉是瓷器的本色釉。在中国传统瓷器命名中将这种白瓷也统称为白釉瓷。但真正的白釉应该是加入白色呈色剂的乳浊釉,是失透的。我国古代从元代的卵白釉瓷开始出现这种乳浊釉。
白色乳浊釉在淄博古窑历史上直到明代天启年间才开始出现,而且白度很不高。
巩家坞窑由于瓷器的胎坯使用的是当地出产的原料“青土”和“黄土”,这些原料一般出产在煤炭的夾层中,大多是在四行煤的底层,其结构较疏松,加之受当时的技术和条件所限,淘炼不细,胎坯原料颗粒粗,含铝量较高,常有未烧透的孔隙和斑点,另外原料中含铁、钛等着色杂质也很高,烧制出来的胎色呈灰色或灰褐色,挂上透明釉后呈现不出白色,所以必须另辟蹊径。那么,要怎样将胎色变成白色呢?巩家坞窑的匠师们巧妙地使用了“化妆土”技术。
所谓“化妆土”技术,就是把质量较好丶颗粒较细的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然后涂在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白色泥层。它就象人们在脸上使用的一层化妆粉一样,施在胎体上,可形成一层洁白光滑的外衣,让瓷胎表面变白。然后再挂上一层透明釉,烧成后便产生出了白色的瓷器产品。这种洁白光滑的色浆外衣,在陶瓷工艺上称为“化妆土”,也叫“陶衣” 丶“护胎釉”。化妆土除纯洁了胎体颜色以外,还填补坯胎气孔,遮盖了胎体表面的凹凸不平,使胎面变得细腻光滑。“化妆土”技术集装饰性丶功能性于一身,大大提高了瓷器的外观质量和釉的白度及光亮度。包括巩家坞窑在内的淄博窑明末以前生产的所有白釉瓷器,实际上都是用白色“化妆土”外罩透明釉生产的白瓷产品。
从巩家坞窑白釉瓷器的发展轨迹看,化妆土装饰技法已非常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这在当时应该是遮盖与弥补胎体粗糙及颜色不纯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技术手段,是一种创造。不但把釉面衬托得更加洁白润泽,而且为白釉瓷器表面的艺术装饰创造了条件。
巩家坞窑白釉瓷器,除了大部分为光素无花纹外,有一部分采用印花装饰丶划花装饰和剔花装饰。

巩家坞窑制碗双头印模
巩家坞窑白釉印花瓷器装饰有两种,一是用刻有装饰纹样的印模,在尚未干透的胎上印出花纹。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里,最精美的印花纹饰印在盘、碗等器物的内中心,没有发现里外都印有纹饰的器物。模印纹饰的特点是线条清晰,层次分明,工整素雅,繁而不乱,艺术气息浓郁。二是用刻有纹样的陶范制坯,使胎上留下花纹。然后施化妆土后再罩透明釉。其特点是,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充满浮雕感,

巩家坞宋代划花白瓷残熏炉
在窑址调查中,发现有完整的印花用陶质缠枝菊纹花卉碗模(图) 丶黒釉瓷质双头制碗印模--一头用来印花,一头用来制范(图)。并发现多件帶有纹饰的陶质枕范残件,上有“子母口”(凹凸连接体),以便合范制坯(图)。
划花,是巩家坞窑白釉瓷器装饰应用最多的技法。匠师们巧妙的利用了瓷胎本身的色泽与化妆土白色的反差来进行装饰。其方法是,瓷胎施化妆土后,在尚未干透的瓷胎表面用木刀丶竹条丶骨制器等尖状工具浅划出线条状花纹,划痕处便露出灰褐色胎底,然后再外罩透明釉,烧出后就形成了白釉地丶灰褐花纹效果。从发现的实物标本看,题材以有规则的菊瓣纹丶枝叶并茂的折枝花丶简洁明了的几何图案为主,通常是对称的。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花姿优美和谐,生动自然,有很强的立体感。

巩家坞窑制碗印花模
另外还发现有戳印着细密珍珠状小圆圈的珍珠地划花瓷片。说明巩家坞窑宋代也采用珍珠地划花装饰白瓷。其制作方法为:先在胚胎上施白色化妆土,然后划出主题花纹,于花纹以外的地子上满饰戳印的小珍珠(圆圈)纹。
剔花亦称剔刻,是指以剔除纹饰以外的空间进行坯胎装饰的方法,俗称减地露花。剔花实际是凸雕技法的一个变种,特别适合瓷胎较厚的产品。巩家坞窑白釉瓷器剔花装饰的方法是在坯体上敷一层化妆土,然后划出纹饰,露出深色的胎,再将花纹以外多余的“地子”剔除,最后罩透明釉烧成。烧成后花纹均在釉下。以褐地衬托着洁白的纹饰,独具特色。有着素雅、温和、洒脱的装饰效果。而且花纹凸起,看上去有浅浮雕的美感。

作者与淄博市原文物局副局长张光明研究员(右)在研究巩家坞窑瓷
巩家坞窑化妆土工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窑口)特征。其使用化妆土生产的白瓷产品,早期显现出灰白色,釉面光泽感不是很强,白色不太匀净。在有边棱的器物上,因化妆土脱流,边棱露胎明显。后期化妆土质地细腻、色泽均匀、白度比较高,上了一层透明釉以后,反映出来的白色很纯正,有的像雪花一样洁白。个别器物呈白中泛黄的奶白色,具有象牙白的质感。普遍釉层较薄,没有肥润感丶垂釉现象。化妆土和釉的附着力都较强,少见脱釉。在烧成过程中因膨胀系数的不同导致了化妆土外的透明釉层的表面产生裂隙,在瓷器表面形成有细碎开片。一般器物内外均施釉, 外釉施不及底。足不施釉,素底露胎。在瓷器表面上亦见露胎丶露釉丶露化妆土现象,胎体、化妆土、釉层清晰可辨。用手可感受到凹凸不平的釉面。
有宋一代,巩家坞窑历经辉煌,白釉瓷烧造规模独步一时。其产品造型古朴深沉、素雅简洁; 装饰技艺高超,印花丶划花纹样秀丽典雅。它的制瓷技艺在整个淄博窑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淄博陶瓷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值得重视的是,在窑址遗留的大量白瓷片中,有的白瓷片胎质细腻,釉色洁白纯正,组合复原后器型工整,极象“官窑”瓷器。容易让人联想到宋史记载的“青州贡白瓷”。
据《宋会要辑稿》一书记载,北宋时代朝廷在开封设“建隆坊”,专门有瓷器库,“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三班内侍二人监库。”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制漆中心在杭州和温州,也就是上引史料中所说的明、越二州。因此,青州的贡品只能是白瓷器。当时的饶州(即今景德镇)、定州(河北定窑)是北宋著名的瓷器生产中心,把青州和饶州、定州并列,说明在宋代青州也应是一处重要的制瓷工艺中心。但直到今天,青州(益都)本土并未发现古瓷窑址。而淄川与青州搭界,宋代时今山东地域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京东东路,治所设在青州,辖淄州。将京东东路从淄州各窑征集的进贡白瓷,文献记载为青州贡白瓷,应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象今天将山东从淄川征集的产品说成是山东产品一样。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2013年10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丶淄博市文物局丶淄川区文物局共同在对龙泉渭头河古窑址进行系统规范考古清理中,在二号水井的出土器物中,发现不少宋金时期白瓷器物碎片,经与青州博物馆所藏宋金白瓷片对比,竞然高度相似。

龙泉渭头河窑出土宋金白瓷残片
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探索课题:宋代的“青州贡白瓷”(官窑瓷)就是指今淄川磁村、巩家坞丶渭头河等窑当时生产的白瓷器。
但这是一个需要关注和深入研究探索的课题。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淄川陶瓷历史的发展和沿革虽然极为漫长,但有价值的可供参考的古代文献资料却极少,所以,我们在考古发掘实践中的实物证据和标本就更显得十分重要和珍贵。
2024.7.7.. 于张店海泉帝景澹庐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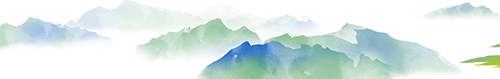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