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琪 《太阳以西》
引言
废名先生曾在《谈新诗》中论及,认为卞之琳的诗歌“欧化得有趣”“欧化得自然”“格调最新,风趣却最古了”。很显然,作为上世纪中国诗歌转型时期的重要诗人,这种将“新”与“古”交融而达成的“折衷”,是卞之琳的突出特点。至于具体如何“化欧”与“化古”,多年来我国学者已有众多丰富阐述。而我注意到,就卞之琳诗歌面相并不单维而言,众多的研究点显然有重经典轻全面之嫌。但在我看来,一位作者文本价值的轻重不过是外界评判的眼光,之于作者本人而言,所有的诗歌都是自己的“孩子”,区别仅在于“呈现”的差异。同时,私以为,卞之琳诗歌的“欧化”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特质之一,便是“迷乱”化的处理。“迷乱”是伊夫·博纳富瓦对瓦雷里诗歌的评价用词。在博纳富瓦看来,瓦雷里的诗歌具有一种“迷乱的力量”,认为这种力量呈现的特点是:感觉的轻易、基本与真纯,有着巴洛克式的不羁。用学者葛雷的话阐释便是:蓬勃而难以被梳理和固定的,且一旦将之条理和固定,其蓬勃的生命力便会顿然枯萎。对此,我的理解:这所谓的“迷乱”是直白当中的玄机,是思维交错的建筑,是诗人对诗之脉搏的强劲赋形。对于深受瓦雷里影响的卞之琳,我以为这等“迷乱”的不羁,同样是其诗歌在晦涩与古典之外的另一标签;是欧化精神得以显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依托不拘泥的诗歌实践,对“自我发明”与突破的勇气和追求,对诗歌内部力量蓬勃与复调化的试炼。
由此,本文拟以新批评理论“文本细读”的方法,以《春城》为例,从诗歌创作的技巧层面,试论我眼中卞之琳诗歌创作中的“迷乱”处理艺术。
一、反讽:表象之下的力量建设
《春城》由卞之琳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上世纪30年代的特殊性在于它“混沌”的多面性:紧张的中日关系、动荡的社会时局、现代化意识的萌动等。身处其中的诗人当然不会回避对如此拉锯般社会气象的正视。而戏剧性的是,诗人对此类严肃主题的表达并未采用“呐喊式”、“说教式”或“幽怨”的写法,而是以挑衅式的嘲讽表达了现实与情感的双重真实。对于现实的写真,我想引用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提到的所谓“写实的幻惑”的观点。即认为“写实法”就是“取材淡淡然,表现也是自然而然而不用丝毫的粉饰”,但却有着“藏于平淡写实中的那种深刻”。在我看来,《春城》中“现实的写真”便是该“写实论”的极好示例。“黄毛风搅弄大香炉”的天气、“拉不到人就在车磴上歇午觉”的车夫对话、“坐了独轮车游春”的花树等,这些确切的市井写照,表面上发挥的是诗歌的“眼睛”功能:提供后世跨时空捕捉时代图像的视角,但更重要的是那“背后的深刻”,也就是在语言的外衣下包裹的“情感的真实”。对“境”之下“情”的呈现,《春城》借助的手法是反讽。反讽是新批评派阵营代表人物布鲁克斯的一个重要观点。该观点认为反讽是诗歌的普遍原则,存在于上下文语境同陈述之间形成的歪曲与修饰之中,是决定诗歌意义的重要修饰。就《春城》而言,诗人对各种意象的选择显然并不天马行空,而是以有主题、有勾连的集群出场,使得意象在单体与单体、群落与群落之间,构成了视觉面与情感面上有层次的反讽张力,形成了有力度与深度的叙事推进。
意象的反差。仅看诗题,《春城》提供的显然是希望的、美好的、充满朝气的意象设定。诗歌的首句“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也类似,脱离语境角度的理解,“垃圾堆上放风筝”的行为完全能传达乐观、顽强、向上的品质。而这实际上正是卞之琳的“小心机”:对制造反讽效果的铺垫。比如诗歌的前三小节——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描一只花蝴蝶,描一只鹞鹰
在马德里蔚蓝的天心,
天如海,可惜也望不见你哪
京都!——
倒霉,又洗了一个灰土澡,
汽车,你游在浅水里,真是的,
还给我开什么玩笑?
对不住,这实在没有什么;
那才是胡闹(可恨,可恨):
黄毛风搅弄大香炉,
一炉千年的陈灰
飞,飞,飞,飞,飞,
飞出了马,飞出了狼,飞出了虎,
满街跑,满街滚,满街号,
扑到你的窗口,喷你一口,
扑到你的五角,打落一角,
一角琉璃瓦吧?——
卞之琳将这些诗句以现象白描叠加想象的方式加以组织。借意象的三次转折,完成了对诗首制造的美好假象的层层消解。三次转折分别发生在:第四行由“可惜”达成的“北京”之于“马德里”“京都”地理空间的切换;第六行由“倒霉”构成了“放风筝”之于“洗灰土澡”的事件对比;而对于第十行由“胡闹(可恨,可恨)”完成的前后视角转换中,诗人引入超现实手法,排场了时间角度的一段跳跃:那些飞出的、满街的、扑面的“千年的陈灰”,是多么可恶,因它是迥然差别于理想的“花蝴蝶”“鹞鹰”与“蔚蓝的天心”的。由此自意象之强烈反差中跃动出的,便是诗歌情感层面清晰的“负声调”。
情感的对位。《春城》中的人物指认显然是大于1个、2个也大于3个。但内部的情感色彩却并不复杂,集中呈现在诗歌侧重人事刻画的后五小节,不外乎“我”归一类,“他者”归另一类(细分两小类)。而对于“我”,诗人的设定是有爱国情怀,但也是无力与郁愤的。
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
碰到了怎能不依恋柳梢头,
你是我的家,我的坟,
要看你飞花,飞满城,
让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
在这里,卞之琳用隐喻的手法交代了个体与故土的关系。“断线的风筝”隐喻着有理想却渺小与被动的个人命运。回应春天的“柳梢头”,则是家园的指代。在这短短的一小节中,诗人不仅借助依恋对象的分化(“家”与“坟”)制造了情感的矛盾与对位,同时用表意的倒置,寄托了对北京的希冀。因为按正常的逻辑顺序,“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依附的是时间的过程性,“要看你飞花,飞满城”则是过程性时间抵达的结果,前者所意味的时间跨度是实现后者的必要条件,而非相反。这种倒置,显然离不开听觉顺滑与愉悦层面的韵脚考量,而整一诗节突然的向内化,并落脚于伤郁的声调,则隐隐散发着对某种信念的不确定。
对于诗歌中的“他者”群体所承载的情感。其中的一类,不管是“春梦做得够香了”的车夫还是“到春就怨天”的路人老方、得过且过式的路人老崔,在诗人笔下显然不过是象征传统糟粕与积习的“千年陈灰”人格化的投射与具象载体。
“好家伙!真吓坏了我,倒不是
一枚炸弹——哈哈哈哈哈!”
“真舒服,春梦做得够香了不是?
拉不到人就在车磴上歇午觉,
幸亏瓦片儿倒还有眼睛。”
“鸟矢儿也有眼睛——哈哈哈哈!”
……
……
昨儿天气才真是糟呢,
……
……说不定一夜睡了
就从此不见天日,要待多少年后
后世人的发掘吧,可是
今儿天气才真是好呢,
看街上花树也坐了独轮车游春,
看完了又可以红纱等下看牡丹。
……
很清晰地,“倒不是”“幸亏”“说不定”“可是”等所完成的串联,荡漾出的是浓浓的阿Q精神,一种“自扫门前雪”的姿态。与这种病态的“乐观”相对地“悲观”,则是诗歌中以小孩与老头儿为代表的另一波“他者”完成。在后续的诗节中,诗人接连用了四个“悲哉”,来表达对不同对象的感慨。其中,前两个属于懒散、撞钟式过活的车夫,后两个属于则老头子般的小孩子——希望、花蕾、未来的象征,却是老头子般的心境。这当中全然的悲哀是绝对的、彻底的,是“古木”的“古”般强劲的。而“古木”的木,则以其虽繁茂却毫无行动力的特点,同老人、小孩这一群体之间达成了巧妙的关联(这当中的呈现便是哈罗德所谓的“诗的本质”)。
以上,得以看出诗人在整首诗中设置的情感对比,“我”同“他者”之间形成的1:n关系,彰显的正是清醒者与沉睡者群体之间巨大的悬殊。这当中隐喻的,便是对时年内外动乱夹击之下国人精神麻木的讽刺。特别是诗歌末尾,以飞机“下蛋”来隐喻军机投炸弹的残酷,淋漓刻画出了时人愚昧、自我麻醉的阿Q精神是何其荒谬。
二、节奏:口语流质中的冲力营造
韵律,当属诗歌的天然属性。对于其在诗歌中扮演的角色,史蒂文斯认为它“创造了自己的虚构”,当属“缪斯”,而“所有的缪斯都是姐妹”。艾略特则认为,往往正是这个听觉的缪斯在召唤着词语。中国传统诗歌的格律艺术对韵律当然也有着毋庸置疑的肯定。但种种,都难及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流派对诗歌音乐性的极致推崇。魏尔伦干脆宣称“音乐先于一切事物”。早期追随象征主义的卞之琳同样十分重视诗歌的乐感,但不同于象征主义将乐感作为对抗传统声韵格律并释放诗歌“自由”手段的偏激,卞之琳认为即不能复古也不能轻视诗歌的“格律”,而得以以二字、三字的“顿”为骨干,做适当安排。这种观念,使得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实践,虽然始终让乐感扮演着机理作用,但并不拘泥于对古典格律手法的化用,诗歌的韵律、节奏并不单一。而有意思的一点是,卞之琳用听觉召唤的“词语”,这种表面编织的随意性,往往会在后续的行文中得到消解,从而被不动声色地组织成诗歌的有机成分。
《春城》中一个典型例子,是诗歌首节末句“京都”意象(参见前文引诗)。按卞之琳自己的说法,是个因想到当时的“善邻”而“随便扯到”的词。这种所谓的“随便”毫无疑问得益于音韵乐感的驱动,是“京”同“鹞鹰”“天心”构成阳韵之使然。但卞之琳的诗歌处理显然不止于此。因为在诗歌倒数第二节“他们这时候正看樱花吧?”:用“樱花”所具的“日本国花”这一意象外延,分明给出了意义机理层面的回应。但确切的,若结合当时日本侵华的社会语境,便会觉得“京都”不仅显得准确,同时制造了反讽奇效:一边是敌国入侵的赤裸裸现实,一边却是对异国的无端向往(京都如海的天、樱花的美)。这里插叙一句题外话,类似的经验倒并不孤例。西方现代主义音乐大家勋伯格就曾坦言自己“只有在创作的时候,剧本才变得清晰,有时,甚至是创作完成之后才变清晰”,这当中揭示的便是想法之于创作,扮演的并非一定前置的角色。
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召唤”,也正是口语化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卞之琳热爱的方式,口语化写作的语言,显得顺滑、自然、活脱脱、充满流速的质感,就像悉尼评论约翰·克莱尔的声音所说的,是“自成一体,而且有坚定的忠于自己原初的‘感觉的声音’的本能”。显然,换句话说,口语化写作不仅在于容易链接人的共鸣,还在于容易彰显诗人个人特质。在卞之琳这里,这种特质就在于,以“顿”的节奏来编织口语的速度机理——一种流质化的节奏。谈到这点,就指涉到一个对“停顿可靠性”的理解。我的观点是,诗歌的停顿并非仅指节奏的“顿”。也就是说,“顿”的显化是多方面的,非止于听觉之韵律,还包括体感上气息的转换、知觉上意义的关联处理等。仍回到上文“京都”的例子。将该词单列一行形成“二字顿”。“顿”的效果一方面被“都”单音节字短促的戛然得以强化,另一方面这种音效上的暂停却又被紧随的破折号以视觉上的滑行制造了新的延伸。由此达成的知觉层面转折、暗示与联想的补充,自然而然强化了上下诗节之间的关联,并让空格更有效地成为当中思维与气息勾连又转换的过渡空间。第二节的起首“倒霉”同样采用了“二字顿”,一则是对“京都”之顿的节奏延续,二则是对前文“ei”韵的回应。这里显化的卞之琳对音韵的编织化处理技巧在《春城》中随处可见:“ei”“ing”“ao”“eng”等韵脚贯穿诗歌始终,以类型丰富的态势制造了音效上的复调和“自成一体”的迷乱感。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冲力就来自于这种韵脚的“混合+重复”的语感强化。而进一步的,是卞之琳在诗歌中以极端化方式大量运用的“叠韵”,比如“飞,飞,飞,飞,飞,\飞出了马,飞出了狼,飞出了虎\满街跑,满街滚,满街号”、大量的“哈哈哈哈哈”、“呼啊,呼啊,呼啊,\归去也,归去也,”等等,语言在这里仿佛失去了“刹车”。但这些貌似“宣泄”的强烈表达显然只是制造“迷乱”的假象,背后的支撑是十足非情绪化的,且是相当清晰与有意图的。
康拉德·艾肯曾指出,所谓依托词语呈现的主题,“几乎总会自行召引出正确的调子”。就此,我的理解是:诗歌由沉默之词构成这一本质,迫使音的终极落地并非服务于听觉,而是心灵的频率。它的有效性的成立依托的是由想象召唤的心灵共振。而在生理的耳朵与心灵的耳朵之间,我以为往往正是这种“被召引的”调子所显化的声音差异,先于内容提供了诗歌印象的第一作用力。至于《春城》中所呈现的“主体情绪”,毫无疑问是泼然而非克制的。客观地讲,在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中,这类风格作品并不少见(如《酸梅汤》《路过居》《过节》等)。按诗人自己的话说便是存在着“风格偶尔放纵”“追求筑建式的倾向多让位于行云流水式倾向”的时期。诗人在《春城》中,给出的是一个游荡在北京街头的路人视角,是“有限浸入”市井生活的平行视角。而一旦理解这种“游荡”与“有限浸入”以及很关键的是诗人亟待宣泄的满腔悲郁,就能很好理解诗歌为何采用这种语速与腔调。这当中所蕴含的试图“刺”醒人的意图,我以为就是约翰·巴斯所说的“贯彻彻底的渴望”,而正是这种“渴望”能够“给语言带来活力”。同时,在我看来,卞之琳在《春城》中对制造声音力量的尝试,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象征主义将之当作反抗手段这一传统的显化,只是反抗的对象大于格律,是接地气的现实。
三、跳跃:开放体格中的张力创造
艾伦·泰特在1938年撰写的《论诗的张力》中,认为诗歌的“张力”是让诗歌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相统一为有机体的因素,而诗歌的意义则呈现于文本内部各矛盾因素的有机交织当中。就其具体特征,我国不少学者曾有过深入研究,如有观点认为可以概括为“多义性”“情感的饱绽”“对矛盾冲突的包孕”“弯弓待发的运动感”等特点。鉴于文章篇幅,在此姑且不做过多引述。而我以为,张力当属诗歌文本的基本机理,是诗歌向内的引力。如果说词语编织诗歌的皮肤,那么张力便成型意义的血脉。凭借着它,诗歌的意义在词群的躯体上呈现为或隐或显或张或驰的姿势,一种神秘的精神给养得以流动于词群底层。回到卞之琳的诗歌。他的很多作品,有着类似电影取景框的效果,《春城》也不例外。这意味着诗歌的呈现通常完成于某种距离——也即诗人自己所谓的对“距离的组织”。这种“距离”不仅指向结构、内容上的敞开与可生长,同时包括对“心理距离”的诗意化、艺术化处理。这使得卞之琳诗歌的张力,通常是种复调的编织,但从意义的角度可以说往往并不自成闭环,倒是韵律、节奏与气息的张力左右了诗歌的结束。在《春城》中,“距离的组织”则具体分化为意象编织、视角交错等层面。对诗歌张力的抵达,最突出的一种手法便是“跳跃”。
语言的活脱。意象作为构建诗歌的根本单位,毫无疑问是通向张力解构的重要切入口。《春城》中,卞之琳的语言活跃着杜尚般的先锋姿势:白话的基调上,文言、方言、书面语纷纷跳脱于各自气场的束缚,被取消距离后戏剧化地混搭、交织,洋洋洒洒,将情感震荡在戏谑与悲郁之间(当然前文也提到过,这些意象在表面的随意性下,具有精确聚焦于诗歌阐述对象“北京”的特点)。例如,诗歌倒数第二节,卞之琳在大篇幅的口语中,突然切换阅读语感,镶嵌了一个书面语“发掘”,以及在倒数第四节中运用大量文言文等,以此制造语体的对此,一方面有意弱化了口语的粗粝质感,另一方面也以语言的杂糅隐射了现实的混乱以及诗中的“我”精神层面的游移。同时,诗人借助典型的北方方言“瓦片儿”“鸟矢儿”、历史隐喻“千年陈灰”、地理特色符号“琉璃瓦”“黄毛风”“古都”“满城古木”“独轮车游春”等,勾勒出相对静态、难以变革的局面,同象征社会新事物与新遭遇的“汽车”“天上鸽铃”“飞机(敌机)”“炸弹”等之间,形成静与动的视景对比、时间上过去式与进行时的对比、社会旧与新的状态对比,由此交织出时空尺度上的立体张力。
这首诗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便是卞之琳对语法规则的淡化及一种提词型表达的运用(即缩词艺术)。这似乎是让语言更显“口语”的有效方法。比如,“说不定一夜睡了”的正常顺序当是“说不定睡了一夜”;“春完了”的完整表达是“春天结束后”,这类异于常规、略显突兀的表达,并不妨碍意义的传递,却大大强化了语调的不羁与流速,以及言说者骨子里得过且过的心态。
虚实的交织。《春城》中跳跃的视角,被“放风筝”这一细节有机贯穿在一起。诗歌的开头,诗人给出的是一个有距离的向上及向远的视角。内部的两对关系是:“风筝”与“蝴蝶”“鹞鹰”之间、“北京”与“马德里”“京都”之间,分别构成的高与低、近与远的空间组织。一种纵横的隐性在这里显现了粗浅的雏形,读者仿佛被置身于一个四通八达的原点,等待诗人的声音出现在低处、身后某个并置的方向:第三节中对脏污的抱怨、对汽车的调侃,读者的感官又迅速被引向当下。“又洗了一个灰土澡”,这里指向自然环境的“灰暗”,构成了紧接着第三节以超现实手法刻画的人文层面“灰暗”的前奏。从客观转向主观的写作视角,在第四节借“谈话的车夫”再次回到现实。并依托超现实的引入,完成了对诗歌容量的拓展、对想象的塑形、对可能性的洗牌。诗的第五节,“老头儿般的小孩”则是基于经验的想象化造型,让前文交错的虚与实在这里有了第一重交织。第二重交织则被安排在诗歌的倒数第二节。也就是说,这包含了对印象与想象的双重提取,让诗人始终扮演着两个角色:观看者与观想者。而“观”因为“思”的存在,使得向外的对外界有距离的选择性组织与向内的对主观意识的具象化提取相并置,从而成为前文提到的“有限浸入”。可以说,诗人确实忠实履行了诗歌在现实面前所能给出的唯一行动(“思”),并以独白的口吻完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理距离的组织:将读者带入亲密聆听者的角色。由此制造的张力,将诗人在诗歌中并未呈现的深层次上对解决问题的思考,植入到了读者的观想当中:作为清醒者如何让清醒扮演合适的角色?在虚与实的第二重交织中,“飞机看景致,我告诉你,\决不忍向琉璃瓦上下蛋也……”中的“我”显然并非诗人而是众多“他者”之一。也就是说,诗人的“观”分观外界、观自我、观他者内心三个层面。而这种对人物内心猜想的展示,第一人称口吻显然比第三人称(诗歌第五节)更显真实与有说服力。通过这种方式,“我”在诗歌中消除了唯一性,而有了另一层面的“普适”含义:这当中(“我告诉你”“决”“下蛋”)包含的无知、顽固与愚昧,足以形成同诗歌第三节的“千年陈灰”相联系。一种精神原型,得以在人称指向不动声色的切换中诞生,并构成了对前者语气强烈却点到为止的诠释。
这里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诗人在“观”与“思”之间呈现的空缺?虽然,《春城》中“风筝”、“灰”(天气、现实)的意象是种标识性的元素,发挥了串联与粘合的功能,但这种虚实交织、取景式的手法,很容易制造文本的开放性。它的生长空间将诞生于每节诗节内部与之外。比如在“决不忍向琉璃瓦上下蛋也……”之后,文本依然存在生长的惯性,诗人完全可以另起一段来回应诗歌第六节,对“我”的内心作进一步观想。但诗人最终以末首呼应的方式,自设了文本“定论(第一句)——阐释(中间)——感慨(末一句)”的闭环。但这并非是从意义的角度。这里实际上引发的是“诗歌结束于何处”的问题。查尔斯·查德维克在分析波德莱尔的诗歌时认为“诗人的目的不是讲故事,也不是说明某种思想,而是要创造一种情感,或是要表达一种印象”,我以为从这个角度,很适合阐述卞之琳在《春城》中的诗歌实践:完整的意义与其说取决于内容的克制,不如说更在于情感、节奏与气息。这就能很好理解在“我告诉你,\决不忍向琉璃瓦上下蛋也……”之后的骤然收尾,能制造怎样的效果:一种不完整的交谈被悬置,情绪上的张力紧绷于诗人提供的“无言以对”的暗示。
结语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欧美现代诗歌影响的中国诗坛,好比刚刚进入河蚌的流沙,珍珠的成型尚路漫漫而长远。可以说,当时的每个诗人都需要摸索着找到自己的路。与同时期的诗人相比,卞之琳的诗歌实践并不像冯至那般着眼于主题或意象的纵深挖掘,也不像艾青那般辽阔高亢,或如同李金发等过分侧重陌生化艺术的锻造。某种程度上,或可认为卞之琳并不拘泥于服从或追随某个固定的流派,而是有意地在古典、现代、象征、抒情……之间寻找平衡与探寻的可能,并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声音与意象美学。而《春城》作为创作于近百年前的诗歌,当我们今天去读它,仍能感受到它分明的现代主义气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之所以打动我的主要原因。但坦言地,对以此类方式创作的诗歌审美,显然是处于国内诗坛主流视线边缘的。而有时,我会想,倘若隐去作者卞之琳的名字,姑且署之以一无名小辈,我似乎很能确定必然会迎受许多否定的声音:缺乏诗意、意象粗燥、结构松散、过于直白等等。那种不负责任的、走马观花式、看人点菜的功利型品读毋庸置疑是对诗歌的侮辱。当然客观地讲,我们尚不能说这首诗是十全的完美,也存在着诸如对“无声之诗”(所谓的意蕴回味)之处理稍弱等瑕疵。但学习与传承的真正意义在于透彻理解基础上的合理取舍。因此对《春城》而言,对文本的细读是必要的。而学习从中呈现“迷乱”式的这种强劲的创新精神,在我看来,是真正有价值的、值得任何时代的人们学习与传承的,这种创新精神,也是让诗歌保持活力、不断生长的唯一可能。
(完稿于2021年10月)
吴晓晖,现居杭州。2018年开始创作诗歌,作品散见《诗潮》《江南诗》《芒种》《西湖》等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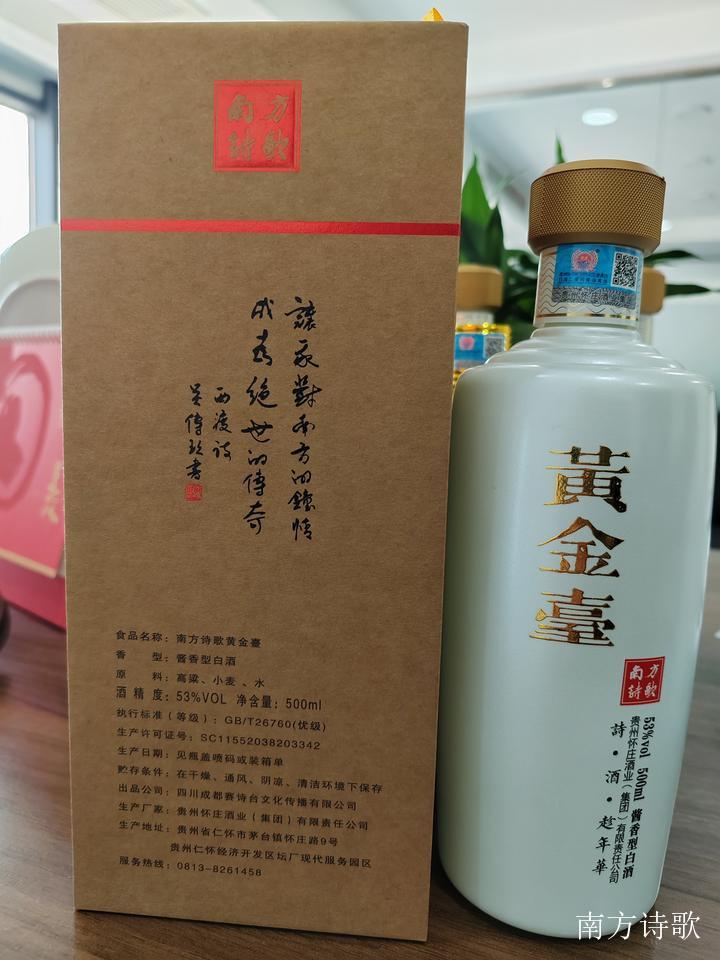

《南方诗歌》2021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2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元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二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三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四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五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六月总目录
陈先发|了忽焉
蒋立波|一架安置在斜坡上的造雪机
太阿|玄鹄——画像记
李心释|世界没有了我的样子
陈智泉|诗歌十年10首
木叶|平行生活
阿信|准备接受隐隐迫近的风霜
苏城|伞,是没有用的
姚辉|寻找倒影的人
周幼安|瓶中的珍珠李
熊流明|那双被天珠吻湿的手搂住了你藏香满庭的脖颈
李曼旎|年轻的宴席
獏|帮我锯开马头琴的男孩子
杜春翔|道视:星空迷域
汪剑钊|玫瑰何时开始飞翔
洛白|生死幻觉
叶朗|装酒的花瓶
鲁子:修正案
“他山诗石”:王家新 译|谢尔希.扎丹的诗歌及其评论
“90℃诗点”:吕布布&张媛媛 | 在废墟上呼出
“名家点评”:王敖|臧棣的智慧与世界
“品读”:雷默|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