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人的故事【七十】
邹星枢‖离开单县

【映】 李东川摄
仔细想想,人,大约都是一样的,有的人大约能把这感觉写出来,于是别人就知道了他。更多的人写不出这种感觉,于是他们便在这个世上悄无声息的消失了。
——编者的话
我们这一批从济南到单县的知青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弟,他们的父兄级别最高的是九级,什么市委书记、海军中将、高院院长、厅局长的大有人在。
虽然他们这批人中最快的几个月后就又回到济南安排了更好的工作,但一部分还是接受了现状在这里结婚生子。
离开这里重新进入城市的想法是在十年后,从一批由菏泽和单县干部子弟的到来开始的,他们压根就没有像我们一样接受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思想,由此蔓延滋生出我们也要主动选择自己人生之路的思潮。
就我个人来讲,最初唤醒我要离开单县之心的是钱素风,那天我遇到刚从济南回来的他,告诉我他去淄博了,是联系调到一家工厂的事。
他说“小邹啊,我要走主要是为了孩子。我不像你住的离场部还近点,我在十六方孤零零就那七八个人的荒郊野外,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我儿子都多大了还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懂,我和他妈每天下地干活,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有一天我发现他最大的快乐竟然是仰着头看天上飞过的小鸟。这样下去将来他比我们还惨!”
这句话让我猛然意识到这还真是个不能不认真考虑的大问题!
不久他就第一个调到淄博去了。
我也开始想办法联系调离。
经过不断的努力,接连有三个淄博的工厂愿意要我,当时场部是军管干部领导。那位军官富于同情心当即批准,但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县林业局长推说劳动局考虑到培养一个熟练的园艺工不容易不同意放人,找到劳动局长又推说是林业局不同意。
反复申请失败,我真的灰心丧气只能死了这份心。
但是人的命运就是有它自己的运转轨道。
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忘了因什么事回济南,这天想起该去看看早已经调回济南的季星如老先生。
他下放到场里时我们相处很好。无意中说起此事,季老笑了说小邹啊小邹,这样的事你怎么不来找我呢?我说你早已经不在那里了还有什么办法?
他不再说什么,到他的书房里关上门,出来时拿着两封信,一封是给劳动局长本人的,一封是给林业局长本人的。封上赫然印着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几个大字。聊了会天才知道现在他已经是省政府办公厅主任了。
哇塞!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喜从天降!回到单县直奔林业局长办公室。局长正端坐在椅子上喝茶,看到我便很不耐烦地说“你咋又来了,不是说不中嘛,不中就是不中,来多少次也不中。我没有说话掏出信给他。他打开一看再没说话,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张关于调动的表格,拿出印盒盖上公章只说了一句话”拿回去自己填吧。”
我又三步并作两步走进附近的劳动局长的办公室。劳动局长一见我说的话与林业局长几乎一样,我也是没有答话直接给他信看。劳动局长看完信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多了个摇摇头笑笑,依然没有说话,与林业局长的动作一模一样,拉开抽屉拿出表格盖上公章“回去自己填吧。”
调动办妥了。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或者说体制中地位或面子的份量。
信封并没有封口,内容也并不保密,老领导只是以熟人,也可以说是以过去相识的友好的口气,请两位局长理解我合乎情理的放行诉求。
现在想来,如果没有这位老领导的帮助,我的调动还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
挡是挡不住的,因为回城潮已经开始直至势不可挡,后来陆续调来淄博的就有十几对男女之多。但是对我来说永远忘不了这位老领导。
季星如先生(调来园艺场任领导时不知道为什么公布的叫主任)。第一次对全体员工讲话就与众不同。他说他是属猴的喜欢蹲着,随说着就拉过椅子蹲了上去。
还说“我既然做领导就不免作出一些决定,大家必须遵照执行,有意见可以当面提也可以背后骂骂出气,这是大家的权利。但我可能采纳也可能不采纳,这也是我的权利”。
季主任好到处转转。这天他忽然走进我家(那时我刚刚结婚)那间小屋,很有风趣地说“嗬,想不到你家还有个‘书架’呢!”那时我穷得只有一个用砖垒的床头小桌,所谓书架是往墙上砸进两根树枝,树枝上搭上块木板,把有限的几本书放上去。他随手取下三本,一本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本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都是当时当局要求大家读的六本马恩著作。还有一本是《巴黎公社史》忘了是谁的著作。
他笑着问“感兴趣吗?”我回答“感兴趣。就是有的很难懂。”
他哈哈一笑:“我来前是山大政治经济系主任。不懂的去问我。”
我心里很纳闷:大学教授?难道他在课堂上也放着椅子不坐蹲到上面?后来我遇到恩格斯关于善恶的论述感到迷惑不懂,真的去请教过他几次,他还真的引经据典令我心中钦佩。
拉近我们关系的是那天班里安排我夜里巡逻,他看到我竟然说“我来陪你”。
他还真的与我巡逻了一夜。就在这漫长的一个夜晚,他给我谈了很多很多。至今难忘的是提到他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孩子,被分配到报社,多年来跟编辑记者们学的文化。
可惜的是他最初一起工作的十几位同志,都是多好的领导啊,可惜都在西湖区“肃托”(内部肃清托洛茨基派反革命运动)时被自己人冤杀了,唯独剩下了他一个,主要是沾了年龄还小的光,否则也被给一锅端了!
我惊问那时候党内斗争就这么你死我活?他们死得也太冤了吧?!他摇摇头自我安慰地解释说“那时候敌我斗争环境太残酷,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些同志的牺牲也是有价值的,他们是为党的成熟成长作出的必要贡献。”
我听了不解。他说“你慢慢也会理解的”。可是我让他失望了,这一说法我至今也不理解。
八十年代末,我又去看过他一次,当时他正与几位老人打麻将,我没有停留就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也退休快十年的一个傍晚在海边散步,看到站在身边的一个人,从个头身材到脸部几乎就是与季主任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憋不住上前说“我过去一个领导,你长得几乎与他一样。”
他笑笑说“是吗?”
我说他叫季星如,他夫人叫邵静如”。
他哈哈一笑“那是我爸妈”。
我一惊。问“他现在也在威海?”
他说“前几天刚走。”我立刻用他的电话与老领导通了话,原来我们就住在威海的同一栋楼上。十几年了竟然就没有碰过面!他说没关系,现在知道了,明年再来时再见。可惜的是天不作美,他年纪大了,我等了好几年,再也没能等到他!

【飘】 李东川摄
七十岁以后的自己已经静下来了,像个局外人一样看着自己的过往,浮生不过梦一场,于是内心便有了份释然和明白。
——编者的话

邹星枢
1946年生于济南故郡黑虎泉畔,性喜清涟而不耐浊浑。曾上山下乡、进工厂多年,创作的二十几部大戏在国家中心期刊及省级专业期刊发表或剧院演出,三次搬上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教学舞台;《绿帽子》由五十年代著名导演张琪宏和北京人艺、中戏及国家话剧院等艺术家在北京公演;中、短篇小说散见于《钟山》、《雨花》、《清明》、《百花洲》等文学期刊,晚年致力于随笔及诗歌探索。拍摄电视剧几十部集。 作者刻意追求的,无不是尽力摆脱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定式,努力探索共同人性中爱与善的张扬和恶与恨的批判、以及人的尊严以及生命权利的普世价值,至今致力于人的灵性和精神探索。

【酒出野田香】 于受万画
编辑:李东川
2024年6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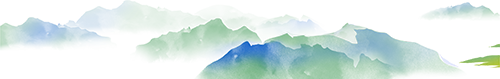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