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笔生花荷出彩
全 兴

龙行龘龘,龙年来也!
就在龙年随着新春的信风款款而至之时,舞笛约我和“味无味处”三文友小酌,一来迎新春之欢,二来久违畅叙,当我打开《铁荷之光》的精装硬皮书封,不免两眼放光——这是一部由中国文化出版社推出的由我市青年作家安建功先生以铁荷派画家刘德功先生为主题事迹创作的报告文学专著,因我与舞笛先生的“老铁之交”的缘故,在他参加《铁荷之光》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时,代我讨来这部煌煌巨著,扉页上有本书作者和主人公的联袂签名,心头自是激动不已。
我禁不住为他们两人妙笔生花为荷出彩而喝彩。为荷,为何?
荷者,莲也,同花异名;荷者,非莲者,出水亭亭玉立者荷,随波摇曳弄姿者莲,大同小异,同源分支,一门二派。
荷者,不仅有莲之雅称,更有菡萏、水芙蓉、芙蕖、莲花、碗莲、缸莲等美名。
荷者,出淤泥而不染,有莲(廉)洁意蕴之品质;立于流水而亭亭玉立,不随波逐流,有独立自主之风格。
荷与“和”、“合”谐音,“莲”与“联”、“连”谐音,荷(莲)寓意和平、和谐、合力、联合,代表祥和吉利,象征清廉高洁。
故荷,被文人墨客所钟爱,为丹青妙手所热衷,受僧仙道儒所推崇。
荷花集佛家的圣洁、道家的祥瑞、儒家的高洁于一体。正是荷花其独特的品性成为佛道儒三家共同的象征。《封神演义》中有诗为证:“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来是一家。”一语道破三家间的通灵关系。
三家都共爱荷,佛侧重莲,道侧重于荷,儒则是莲花同爱,三爱虽异,但异曲同工。
莲花在佛教中,寓意圣洁、清净和吉祥,象征着神圣与不灭,是佛的化身。
入淤泥生而不污,出淤泥中长而不染,如菩提般在生死的烦恼中超生解脱,寓意超脱红尘,四大皆空。又因其根新年重生,更象征万物轮回,生生不息。
荷莲也因其净化心灵不受外淤和物欲所动,超然物外而被道家赞之为金莲。绿叶红花相映,如阴阴相抱;荷花的盛衰契合阴阳变化;荷入水之中温和如阴柔,出水之后坚定阳刚,一荷含阴阳。
比之于佛教用莲花来象征高贵、圣洁、智慧、慈悲等品质,而道教钟爱用荷花来表现坚韧、纯净、自然、平衡等特质。
相比于佛家不垢不净出世无我,道家的超然自然隐世忘我,荷之于儒家,更多的是克己复礼和入世修我。
故荷花之于古今之文人士大夫,既寄情于荷花,又托志于荷花。
周敦颐的《爱莲说》,托物言志,区区百余字,言简意赅,以牡丹作反衬,用菊花作陪衬而颂莲。字字珠玑,寄君子之志,得义理气韵,见正大气象。至今让人们吟诵不已。
被喻为谪仙的大诗人自称青莲居士,爱莲有加,恋荷有余,其对荷莲的敬爱之情不言而喻。
宋代诗人杨万里,《小池》大作,清新活泼的笔调,绰约自然的诗意,情趣盎然的荷韵,让人美不胜收,赞不绝口。
荷,何曾没有自己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但更钟情于夏;荷,何尝没有自已的风采,但更愿用残叶枯枝展示自已的神韵,如沙漠之胡杨。败于岁序,仍留风姿,枯有风骨,更有神韵,墨客骚人向来为其所叹服而倾笔。
也许是满池残荷待春生的期待,使得一池残荷如诗画;也许是风骨残荷绽余晖的韵致,使得曲尽其妙荷出彩。
残荷,身枯傲骨在,迟暮壮心存,虽花尽叶去茎瘦,仍旧风韵犹存。这种风韵,是繁华落尽之后的孤傲与静谧。
君不见,枯枝如骨,孤于秋水中,静默中尽显禅意。先历经生之勃勃,又有夏之璀璨绚烂,再经秋之沧桑凄枯,终来无怨无悔,这种遗世独立的沧桑感。正是残荷枯枝硕果呈现出的独特美感和韵味。让人回味无穷,百感交集。
残荷之意不在于形而在于神,不在其枯荣而在于韵。其昭示众生:形可残,但神不可无,枝可枯,但韵不可失,愈是艰难,愈要内心坚定和宁静。
“枝残叶败怯寒霜,默默无声底气藏。待到明年夏风吻,满湖菡萏抱阳光。”谁说荷光没有明天?来年没有荷光?
残荷,枯枝凋零,少了份灿烂,失去了几多赞颂,可正是这份光彩褪去后的打磨和磨炼后的那份坚韧饱满,以及潜藏在孤独美感后的铮铮傲骨,使其更富有韵味。
南唐中主李璟笔下的残荷。“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谁不感叹时光飞逝心生幽怨,感慨万千。
李清照的“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秋日残荷的美,与刘禹锡的“我言秋日胜春朝”是不同诗人的跨时代同感。
同样是听雨,晚唐的李商隐“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与南宋末年的蒋捷“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都有一种国将尽,雨更愁之通感,尽管如此,有无残荷是不一样的,也许有了残荷更动听也更动人。
同样是残荷,同样是晚唐,同样是李商隐,“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年年岁岁残荷似,岁岁年年残荷异。”何尝不是一种荷花版的《花妖》。
自古以来,丹青绘荷美的数不胜数,诗文赞荷韵的不胜枚举。
但今天,让我感同身受的当数刘德功和安建功两位先生了。刘德功先生爱荷如命,久久为功,数十年画荷,创铁荷画派,如林逋之梅妻鹤子;安建功先生十几年来笔耕不辍,让铁荷发光,如伯牙与子期之高山流水遇知音,一个钟情翰墨,一个奋笔疾书;一个不停地绘制,一个不停地善解;一个在画内下功夫,一个在画外作文章,可谓是妙笔生花荷出彩,珠联璧合神韵来。
他们对残荷的情有独钟,作品不断见诸报端。我于他们虽无一面之交,但早已神交。

甲辰龙年的春潮渐退,烟花散尽,年味到味无味处时,我与舞笛先生和“味无味处”挚友三人以《铁荷之光》为由相约小酌,当舞笛把一本由他代为讨签来的《铁荷之光》转给我时,两位先生的签名让我受宠若惊。
一个是知天命之年的“50后”、一个是步入花甲之年的“60后”,一个是已届古稀之年的“70后”,三人相谈甚欢,对铁荷和《铁荷之光》更是赞誉有加,尤其是卷首语《爱是一种光》和末页的《金太阳》作品,特别是安建功先生那篇《震憾与感悟》和刘德功先生历时十五载、呕心沥血精心创作的那幅《百米铁荷长卷》以及他所开创的铁荷画派,着实令人震憾,让我感叹。
几十年来,刘德功先生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基础上,在继承中创新,在致力于技法的创新和个人风格的塑造中,以荷花尤其以残荷为主要创作题材,通过独特的线条和色彩处理,展现出荷花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不仅展现了荷花的艺术美,也体现了画家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现代艺术的探索。
其画风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不仅追求古典之厚重,而且富有现代之风格,既有传统中国画的线条美学,又融入了现代的视觉元素。刚柔相济兼具力度与柔美、情志互融,展现出了荷花的铁骨与风韵。
其画法呈现出的技法创新,在坚守线条这个中国画的灵魂的同时,注重线条的流畅与变化,以及墨色的深浅与渲染,不仅体现对宋代绘画高古典雅清新脱俗意境的追求,而且还展现了铁荷画派深厚的学术基石和文化底蕴,使得作品既有立体感又不失空灵感。其价值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创作和创新,更代表了对中国传统绘画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其功至伟,其德至大,其名至刘。
十几年来,安建功老师循着刘德功先生的铁荷之路,通过近一年的深度采访,深入探究了铁荷画派的艺术特色和背后的故事,深刻诠释了铁荷画派的理解和高度评价。利用业余时间,历时八个月完成了《铁荷之光》这部展现铁荷画派创始人刘德功艺术成就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并详细记录了这位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和艺术理念。三卷36篇文章,总字数达到13万字的《铁荷之光》,不仅是对刘德功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顾,也是对铁荷画派这一艺术流派的一次系统性梳理。有了《铁荷之光》,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铁荷画派的创始人刘德功的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以及他在当代中国画坛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
循着《铁荷之光》,其功可歌,其建可树,其心可安。
不看不解铁荷意,初看已知文中人。
从鹰城“二功”的思绪中跳出来,我们也在感慨,人生百年,我们三人何尝不是残荷?
几十年来,在字里行间行走,蓦然回首,我们何尝不是一根根枝枯叶尽的残荷?
当我们不再刻意拨弄时光的指针时,我们还有余力拨弄文字,可以赏荷咏荷,为荷光增辉。
我们三人面面相对的那一刹那,《铁荷之光》《爱是一种光》《金太阳》的辉光与我们的目光交汇时,我们都为之心动。
何也?荷如人生,人生如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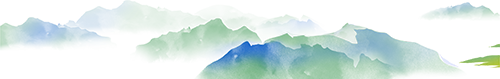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