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洁白如玉的流苏
魏耕祥

郑家庄的流苏远近闻名。又是一年的四月份下旬,正值流苏盛开的时节,忽然接到高中班长郑家振同学的盛情邀请,前往博山镇郑家庄观赏盛开的流苏花。这里有一百多棵流苏树,有些已有百年左右的树龄,每逢流苏盛开季节,漫山遍野洁白如玉的流苏花成为南部山区一大景观,前来欣赏流苏花的人络绎不绝。为此当地政府特意设置“郑家庄流苏节”,以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名片。
流苏,木樨科流苏树属落叶乔木或乔木植物,因花序圆锥形,着生许多白色小花,很像流苏饰品,因而取名流苏树。流苏树喜光,不耐隐蔽,略耐寒,耐干旱瘠薄,生长速度较慢,寿命长,淄川区土泉村有棵流苏树已有上千年的树龄,成为当地一张名片。流苏生长于海拔三千米以下的稀疏混交林中或灌木丛中,在肥沃通透性好的沙土地上有着更好地生长表现,在我国北方多数地方都有生长。流苏是学名,在家乡叫做“幽公”,是嫁接桂花的砧木。前些年流行桂花,推高了桂花市场价格,不少人前往封山挖掘流苏嫁接制作桂花盆景,对流苏树造成一些损害。自古以来,人们对白色的花卉赋予了美好的品质,洁白的流苏花被古人赋予了“孝廉”、“清正廉洁”的文化精神,也被人们当作乡土、家园的象征。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也不惜笔墨给予赞赏。唐代著名诗人杜牧赋诗流苏:“春花杂落埋流苏,青春似雪月如珠。不见故人何处寻,落花黄柳占春愁。”诗人借写洁白的流苏花凋谢,表达对青春已逝的无限感慨。宋代著名诗人苏轼写的“遥知流苏情意意,佳人独向瑶池强”,寄托了诗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情感。
四月二十六日,我们十位同学齐聚郑家庄老班长郑家振同学家,这是我们高中毕业五十二年之后第一次在老班长家聚会。郑家庄位于一条山溜北面的向阳山坡上,老班长家住村东,新建的房子新式房间设计和现代家具,凝聚着老班长和嫂夫人若干年奋斗的汗水。老班长年轻时曾任民办教师,在淄博师范学校招生民办教师时,老班长考了博山区第七名,却因资格问题失之交臂,第二年却又阴差阳错地被裁撤,原本一个优秀教师的人生之路遭到逆转,老班长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创造新的人生,翻建了村中的旧房屋,在村东购置地皮建筑一套新式住宅,赡养和送走九十多岁的父母,将两个女儿培养成才,虽然在城里买了商品房,依然在家守护着那一片洁白如玉的流苏花,守护着这片纯洁的净土,这样的人生不也同样富有价值吗?流苏年年盛开,而时光流逝,青春早已成为过去,我们这代人在文革前受过初小教育,成长过程大都在文革期间,忍过饥挨过饿,耽误了正规的教育,蹉跎了成长成才的道路,纵然人生充满了坎坷,依然坚守了人生的责任,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纯真执着初心不改,犹如这纯洁如雪的流苏花,不掺一丝杂色。

郑家庄的流苏树就在村子对面的南山坡上。古人在建立村庄时,大都选择背阴的山坡上建立一个“封山”,体现了古人的自然与风水的理念。所谓“封山”,就是历代村民的共同约定:这一片山坡的树木不准随意砍伐,即便其他山坡的草木被割得干干净净,封山的树木也不准动,仿佛神山一样敬畏,因而“封山”里的树木,仿佛原始森林一样茂密。郑家庄的流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成了以流苏树为主的特定风景。
据老班长说,原来“封山”的流苏树更多,文革期间砍掉了一大片,现在的流苏面积比原先小多了。站在老班长家门口远观郑家庄流苏风景,但见巍巍南山,流苏树与黄栌等杂树参差错落,每逢流苏盛开的时节,黄栌树以青翠欲滴的绿叶衬托起洁白如雪的流苏花,更加显得层次分明,洁白如云,仿佛碧玉翡翠衬托着羊脂白玉一般。到了秋后,流苏和各种杂树相约落尽树叶,以稀疏的枝条和空间将满山的红叶衬托得层林尽染。真个是,你在春天把我映衬得洁白如玉、志趣高洁,到了秋天我把你的灿烂如霞、修成正果告知天下,万事万物相辅相成,相依为命,天道自然。大家为这感人的流苏花,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打卡。
在老班长的引领下,我们一起走进南山近距离观赏流苏花。南山坡度比较陡,我们顺着山间小路,一路欣赏沿途的流苏花。百余棵百年左右的流苏树,高低错落地根植于南山坡上,年长的树冠庞大威武浩渺,年轻的树冠虽小却也摇曳多姿,一片片盛开的流苏花仿佛一簇簇白云在空中腾起,辗转腾挪,起伏跌宕。只有近距离观赏,才会看到流苏花盛开的气势,洁白如云不掺一点杂质。走过一树又一树,每棵流苏树粗壮不同,气势不一,品格各异,有的是谦谦君子,有的是威武的壮士,有的是指挥若定的大将军,有的是窈窕淑女楚楚动人,有淳朴的乡民,也有含情脉脉期盼远方的亲人早日归来,各种形态各种姿势,各种丰富的审美意象,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走进南山近距离观赏流苏的审美体验,与在北山的郑家庄远观南山流苏花的整体景象,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审美印象。郑家庄的流苏的确不同寻常。
其实,我早就想来郑家庄拜访,这里曾经住着我的一位特殊老师,一直想采访一下他特殊的人生经历。说他特殊,其实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又确实“教”过我们那一级学生,不过他给我们当的是“反面教员”。
那是一九七一年初春,我们按照当时的招生政策,推荐入读淄博二十一中高中三级,其实我们这届学生大多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文化运动”,正常的教育秩序被破坏,学习知识虽然被耽误了,但阶级斗争的课程必须上好。某日,学校组织级部开会,等到级部三个班都到齐之后,才知道今天的会议是批判右派分子顾承隆,据主持会议的学校党支部书记说,顾承隆因心情郁闷,到南博山公社饭店以喝酒为名发泄不满,被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遭到批判。顾承隆老师站在全年级学生面前,只见他中等偏低的个子,身材有些敦实,神情黯然惨淡,低着头,任凭大会批判,或许自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来,这样的批判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至于会上有谁发言,批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顾承隆老师那副惨淡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逐步了解到,顾承隆老师是上海人,据说是上海资本家的公子,典型的富家子弟,五十年代初响应上级“支援山东建设”的号召,怀着一颗纯洁的报国之心,报考山东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淄博一中任生物课教师,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了“阳谋”,被打成淄博一中四大右派之一,被发配到位于南部山区的淄博二十一中接受劳动改造,住在学校一间逼仄的宿舍。听校友说,顾老师说一口浓重的上海话,文革前给学生上课,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听懂他的课。顾老师是科班出身,自然功底扎实,上课效率自然是好的,但那时的生物课早已变成“农业基础知识”,主要是到学校农场干各种农活亲身体验。因为这次批判会,同学们认识了右派顾承隆,同学们大多没有那么敏感的阶级斗争意识,也不知道右派的含义,见到他也没视若洪水猛兽。听说他是南方人会吃蛇,北方人是从来不吃的。有一次,不知是哪个班的学生到学校农场劳动,打死一条虎口粗的花蛇,拖拉回来送给他。据说顾老师露出少有的微笑,顾老师熟练的剥皮、去除内脏、清洗,不久他那逼仄的宿舍里便飘出肉香味,据闻到味的同学说:“味道挺香!”文革后期阶级斗争的紧张氛围慢慢放松,学校开始让顾老师承担教学任务,有热心的同事关心他孑然单身的生活,于是给他介绍了王家庄的一位寡妇,从此顾承隆老师过上了正常的生活,那年顾老师四十七岁。再次听到顾老师的信息,大约在八十年代初,听说顾老师已被平反,也没再回到淄博一中,成为淄博二十一中的骨干教师,政治上不再受到歧视,工作上也有了自己的地位。夫妻两人没有自己的子女,二人世界过了二十二年,妻子也没将顾老师陪到最后,在顾老师退休八年后撇下顾老师独自走了。后来热心人牵线和郑家庄寡居的郑向会女士结为连理,她和继子女陪着顾老师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在他八十八岁那年往生去了,终于有个圆满的结局。郑家庄和周边村庄有顾老师的几代学生,这里有他特定的熟人社会,想来不会寂寞吧。

老班长指给我顾老师墓地的方向,那是南山脚下流苏树映衬的田园。一个大上海的富家子弟,在历经落难贬谪、平反昭雪、归于正常工作与退休后,寄居于偏远的山村郑家庄,最后永远栖息在这里。忽然想起《红楼梦》的葬花词,“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顾老师捧着一颗纯洁的心志而来,带着纯洁的因果而走,葬在纯洁如雪的南山流苏花下,每当洁白的流苏花盛开的时候,将顾老师的归宿地映衬地如此纯洁无瑕,这或许是顾老师最好的归宿。本想在我退休后,到郑家庄细致采访顾老师,访问他的家世、因何打成右派,及其平反昭雪、重新工作、建立家庭后的感触,披露一个被信任又被侮辱,重获尊重而早已扭曲的人生。待我退休,却得知顾老师已在前一年远行往生了,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本该前往顾老师墓前,献上一束洁白的流苏花,但因事先没有准备,也怕过于唐突,遂再留下一个遗憾。或许人生若没有遗憾,圆满也就不够真实。
回到老班长家,嫂夫人早已准备了满满一桌喷香的菜肴,老班长招呼大家落座,满满地酙上酒,举杯向同学们提议:为了郑家庄盛开的流苏花,为了我们逝去的青春岁月,为了我们曾经如同流苏花般的纯真友谊,干杯!
2024年5月4日于张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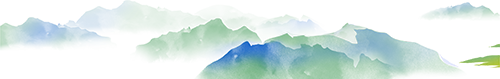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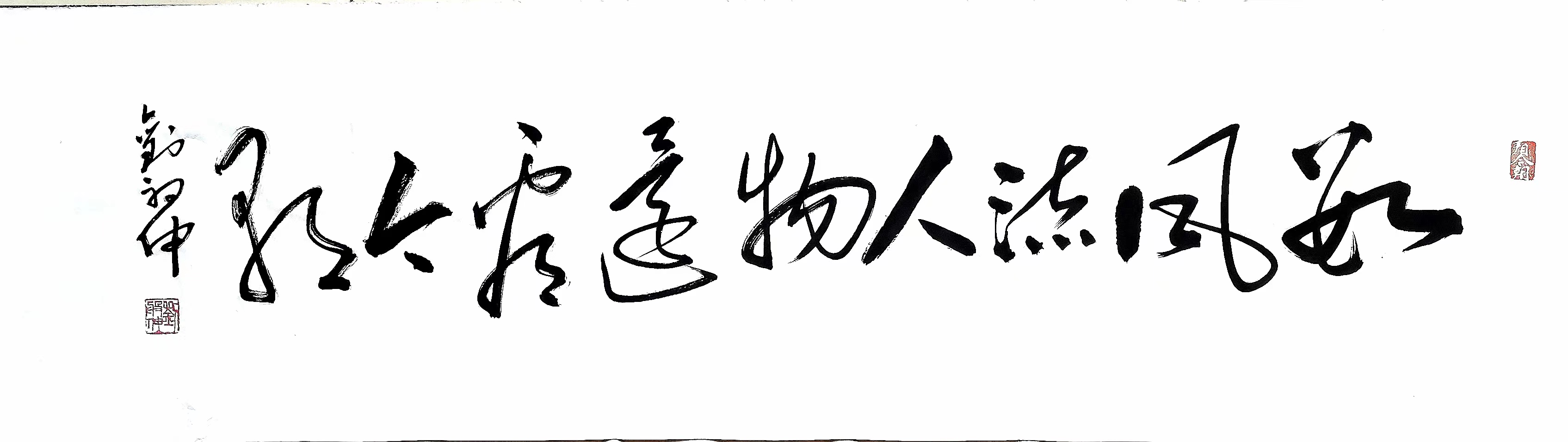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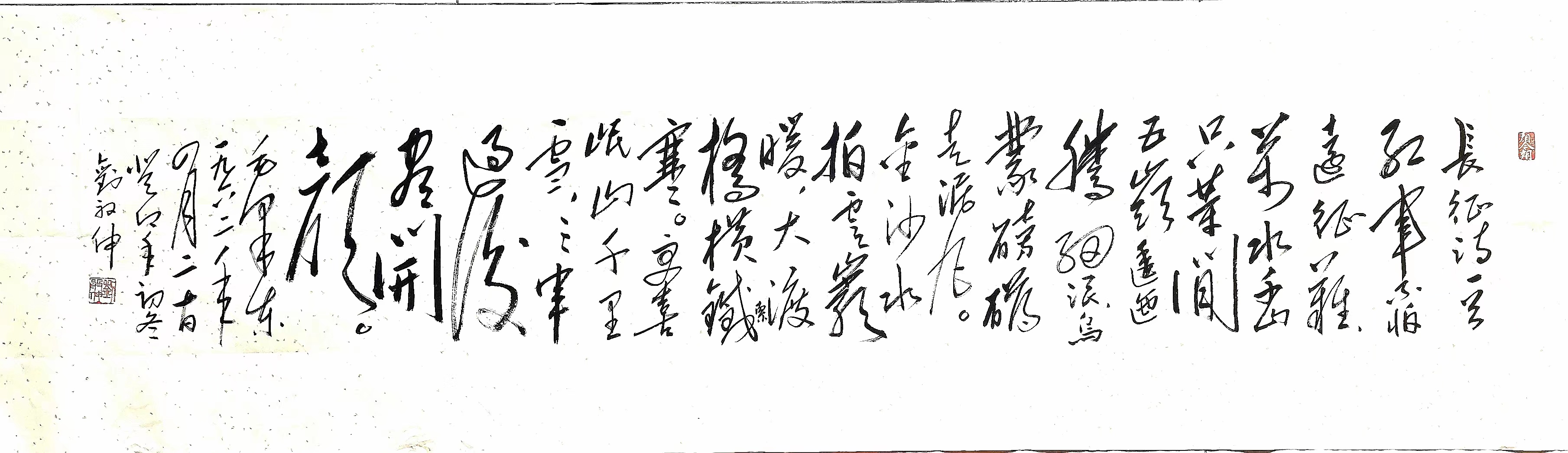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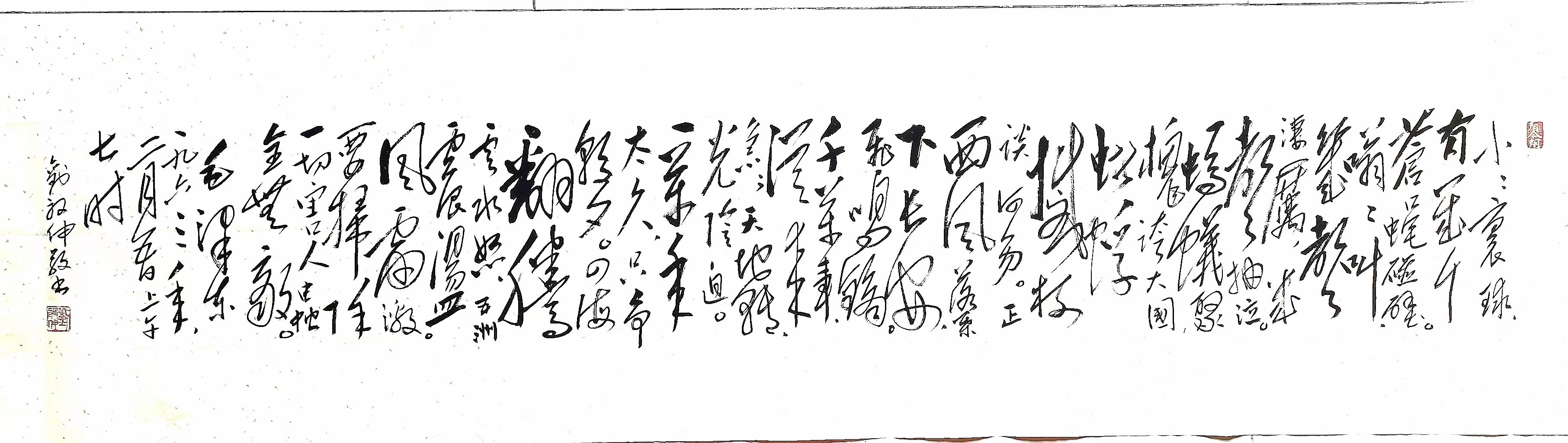
艺术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