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雨 《秘境系列》
在玄武湖划船
韩东
我还记得那阵风
它起自湖面
到岸边结束
任意摆布我们的船①
我还记得
想象中的孤单
在绿色的湖面上
我们同时操桨
又都把船桨搁下
船头顿时歪向一旁
我还记得摸出烟来抽②
四只手捂住的火③
记得我们刚刚还在湖上
完全是这样的④
我记得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大路上
注释:
① 《诗刊》发表时,“任意”为“随意”。收入诗集《白色的石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时改为“任意”。
② 《诗刊》发表稿、《白色的石头》此行均为“我还记得拿出烟来抽”,收入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时改为“我记得摸出烟来抽”。《爸爸在天上看我》所收为此诗定本,以后各版未再改动。
③ 《爸爸在天上看我》“捂住”改为“罩住”。
④ 《诗刊》发表时,“这样的”为“即兴的”。《白色的石头》改为“这样的”,《爸爸在天上看我》又 改回“即兴的”。

韩东,诗人、小说家,著有诗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四十种。最新出版作品有:诗集《奇迹》《悲伤或永生》《买盐路上的随想》;小说集《幽暗》《狼踪》。
惟直接才能暗示
—— 读韩东《在玄武湖划船》
西渡
1986年9月韩东参加了《诗刊》第六届青春诗会。诗会结束后,《诗刊》第11期发表了韩东《诗六首》,这是其中的一首。当时我读大学二年级,在图书馆读到这首诗,让我 吃了一惊。说实话,它比议论纷纷的《有关大雁塔》《你来自大海》那几首更让我惊讶。我感到一种新的诗诞生了。《有关大雁塔》引人注目的是那种反对朦胧诗的姿态,但它也被这种姿态和它反对的对象所绑架。而在这首诗中,韩东完全是他自己,是摆脱了“三个世俗角色”之后,以自己的皮肤面对世界的自己。这种直面世界的态度让新诗回到了《诗经》时代,回到了诗的起点。这在新诗史上是件大事。胡适和初期白话诗人模模糊糊有点这意识。但对于他们来说,文化太强大了,而诗又太弱小了。他们都无法把诗带回到起点。废名 1930年代提倡新诗的“古风”,实际上他自己的诗也没做到。这首诗是真的回到了起点。
这首诗似乎只写了一些简单的事实,与朋友在玄武湖划船,湖上起风,船被风摆布,为了控制船,众人合力操桨,只要搁下桨,船头就会歪向一旁。此情此景让“我”感到有点孤单。也许这是因为在茫茫湖水中,“我”感到了某种大于我们、大于人的力量,也 许还有一点危险。不过,这些涉及心理层面的东西,都没有说出来,诗人只用了“想象中的孤单”六个字加以暗示;说出来的都是事实。风小了,危险消失了,“我”拿出烟来抽, 还没完全消失的风让点烟这个动作变得困难,“我”和朋友用四只手才能捂住小小的火。“我们”终于上岸,回到大路上。这里描述的都是事实,没有政治、历史、文化介入的日常的事实,没有带有暗示意义的意象,也没有微言大义的、象征的深度。
那么,这首诗的诗意体现在哪里?就在事实本身。韩东说“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世界就在我们的前面,伸手可及”。这个伸手可及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存在、生命的事实, 也是我们的命运。诗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体会和经验。它们全都包含在这首诗中了。如果你认为这些事实没有意义,那是因为你受到了观念的毒害,用观念替代和遮蔽了我们生命的事实。为了呈现事实,这首诗最大程度上采用了客观的写法,并做到了最大程度的简洁。诗中的每一个动词都非常准确,具有绝对的表现力,是表现诗中的事实无可替代的、唯一的词。实际上,这首诗的每一个词都是必须的,在它最合适的位置上,挪动或改变一个词,也就意味着改变事实,改变这首诗。写风,“它起自湖面/到岸 边结束/任意摆布我们的船”;写我们与风的对抗和放弃:“我们同时操桨/又都把船桨下”;写船,“船头顿时歪向一旁”;写点烟:“我还记得摸出烟来抽/四只手捂住的火”。一个动词就写活了一个事物、一个场景。收入诗集时的几处修改也体现了这种对准确的追求。从“随意摆布我们的船”到“任意摆布我们的船”,风的意志成分增强了,“任意” 与“摆布”的搭配更合理,因为“摆布”是一种有意志的行动。“摸出烟来抽”也比“拿出烟来抽”更为准确,更准确于船上、风中的环境。《诗刊》发表稿“完全是即兴的”,这个表述有点含糊,是指“我们”的划船,还是指风的来去?把读者注意力分散了。“完全是这样的”,是对上文的收束,也是对读者注意力的集中,让我们再次返回现场。至于后来又改回“即兴”,透露出作者在追求这种准确中的犹豫。另一失败的修改是“捂住”改为“罩住”,“罩住”之“罩”可大可小,远不如“捂住”之能准确传达风中点烟的手上动作。所以,这两处我们采用了《白色的石头》的表述,而没有采用定本。这种犹豫和失败正好说明达到准确的不易。
诗所追求的理想中的准确语言是内容和形式等值的语言,这样的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形式”,就是诗。也就是说,这些似乎不包含暗示、象征意义的事实,最终变成了生命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直接就是暗示;甚至可以说,惟直接才能暗示。从这个角度说,直接的语言也是暗示的语言,而且是最有力的暗示的语言,因为它暗示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反而给意义带来无限的可能。
当然,这首诗并非完全客观,在这首一共十六行的诗中,“我还记得”出现了三次, “记得”出现一次,“我记得”出现一次,而且有两次单独成行。“记得”这个表述,它的第一个作用是把进行时转化为过去时,把实象转为虚象。也就是说,诗人一边呈现事实, 一边把它抹去。这是通过在空间中引入时间的因素,在我们似乎可以把握的事实中制造了一个漏洞,让事实呈现为不可能和不可把握的。“我还记得”“记得”的高频重复,其第二个作用是造成一种淡淡的忧伤的感觉。这种忧伤源于人,一个拒绝依靠政治、文化、历史的人,面对时间和空间的无奈。它也是“想象中的孤单”的来源。这种忧伤是主观的,但并非自我的;它属于诗,而不属于诗人。它就像波提切利笔下刚刚从浪花中诞生的维纳斯的忧伤。面对陌生的时间和空间,新生的女神感到莫名的悲喜,兴奋中混合着沉重和倦怠。与维纳斯一样,独自面对世界的诗,也有一种莫名的悲喜。这是一种创始的悲喜。诗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感到命运的分量,然而肉体还没有获得担起这分量的力量和经验,于是忧伤笼罩了刚刚从浪花中显露的身体。
形象的蕴含是无限的,不能穷尽的恰恰是直接的诗。这首诗以高度简洁、准确的语言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说还原也许不对,诗中的事实归根结底是语言构造的事实,带有虚构性质,用苏珊·朗格的话说,是一种幻象——体现了高超的语言技巧。但这种幻象如此逼真,以至于现实与它比起来反而成了一种虚假和苍白的东西——现实的不稳定、转瞬即逝怎么能和诗的确定和永恒相比呢?罗伯特·潘·沃伦说:“一首诗读罢,如果你不是直到脚趾都有感受的话,那不是一首好诗。……肉体的感受是最根本的。许多人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诗歌都是优美的。优美?见鬼去吧!诗歌就是生活,是充满了活力的经历。”诗的真实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让它向诗的需求发动起来。
原载于《当代·诗歌》2024年第2期

西渡,诗人、诗歌批评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67年8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其间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2018年调入清华大学。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鸟语林》《天使之箭》,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壮烈风景》《读诗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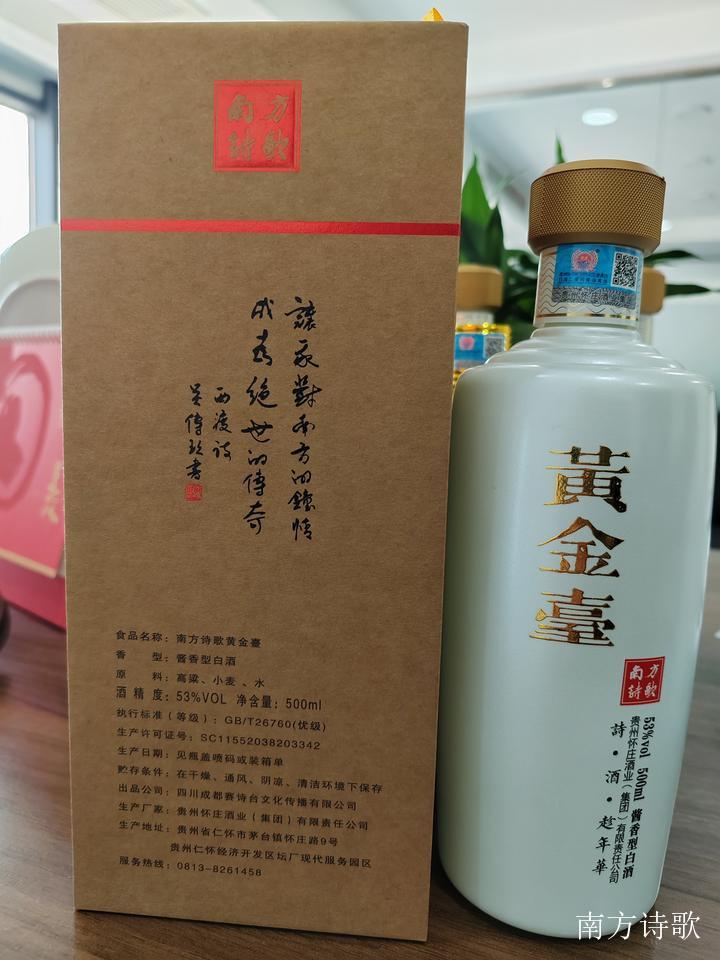

《南方诗歌》2021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2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元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二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三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四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五月总目录
诗歌原创
高春林|花镜和芦笛
北野|在浑善达克
楼河|蓝色的星球凝结着坑洞般的巨眼
窦凤晓|我暂时不想跟你讨论烤鱼
章平|在一滴海水里,把自己慢慢变淡
谷莉|我也是一只蝌蚪
楚雨|基弗
黄啸|豹和它的城市
陈子弘|《只有一种模式》诗选10首
张正|它那么小
苏楷|在陌生的肖像下
晨叶|拜访另一个村庄
石人|诗集《瓷片》选录10首
长诗
张洪波|穿越新生界
“他山诗石”:赵四 译|十二首,为卡瓦菲斯而作
“他山诗石”:李以亮 译|R.S.托马斯诗选
“名家点评”:胡亮|蒋浩反蒋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