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人的故事【五十七】
邹星枢‖坏小孩的艰难成长

【轻灵】 李东川摄
当光投射进你心中时,你在捕捉光的同时,一定要用它驱逐黑暗。
——编者的话
小时候我真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孩子。
偷家里的小东西换看小人书、卖掉家里的古玩买乒乓球拍、夏天夜里偷吃小贩存放在在河水里的西瓜、晚上偷骑残疾荣军的三轮车差点掉到河里、喜欢上画画没几天又没了兴趣、吹了几天笛子拉了几天小提琴又都半途而废、背过的书更是没几天就忘。
11岁失怙后病中的母亲为我犯愁,要我跟一个表舅学手艺。表舅是旗人,姓锡名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有在蜡纸上作出精美七套色的绝技。他教我从刻钢板上的蜡纸练字开始,但几天后表舅就说,你写字怎么连你的名字都一次一个样?孩子啊你实在不是这块料。从此不再教我。
十六岁上慈母见背,我才开始犯愁甚至恐惧:将来可怎么活!
所以当我与几十个青年分乘三辆大客车去火车站要赴单县园艺场时,我的心境是愉快甚至是急切的,因为我终于离开济南离开东青龙街了,尽管这里是生我养我之地,有着滋养我身体净化我心灵的黑虎泉水,有着温馨父母家庭的余温,但也是我太多的伤心之地。
就在这时站在我对面的叫刘金岭的男孩竟突然痛哭出声,我问他哭什么?他抽泣地说还不知道那边什么样,可这里是再也回不来了!
我真的着实不解,我说“你可哭什么呀,园艺场那里应该是一片绿色的海洋,里面一定会有那么多从没见过的虫子啊小动物啊多有趣啊”。
当时他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我与你没话可说”而转过脸去不再理我。
当时我就猜出他有一个爹妈都在的正常温暖的家,他有很多我所没有的挂牵,而我虽然所幸还有哥哥姐姐在,但毕竟无法与父母相比。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面对同一件事,每个人所处的境况不同心理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
我至今还念着园艺场的好,尽管割麦子累得腰要断了,收葡萄汗流浃背黑衣服都被汗水里的盐碱变成白的,割豆子整个手都被扎伤,夏天打药导致我身体里的汞含量超标五倍,整个寒冬冒着呼啸的北风爬到树上剪枝,积肥弄得满身臭味。但那里有离开后再也不得一见的白日蓝天的云卷云舒,夜里也是蓝天的灿烂繁星。那时那里夜空的蓝是那样的奇美,城里长大的现代人是难得一见的。
我在园艺场的十三年,那里几乎所有的老领导真的没有现在的官气,通情达理按那时的政策不走样:任何一个工人生病,从场医务室开一张条子,就可以去县医院就医住院不用花自己一分钱。生病六个月内发全工资。需要转院只要县医院医生开了条子,地区医院省里医院随便去,医疗费用包括旅费都可以报销,场里还派人陪护。
我妻子就曾出省到无锡去看病,到济南看病还派我做陪护。
但在另一面,由于政治学习思想灌输的每周不断,导致我到了二十多岁还是个没有自己大脑的机器人:深信不疑领袖的绝对正确与不可动摇的权威。
此间并不是没有一点应该去思考的信息,譬如从《参考消息》透漏的蛛丝马迹与《人民日报》的不同里,从正常的逻辑导引出应有的质疑与分析,起码是应该自己说服自己吧。
只是到了那一年第一次听说过的那架三叉戟在蒙古的不正常坠毁,才好像觉得事情太过蹊跷不可思议,甚至传达的文件也难以自圆其说。但是仍不敢其实是不习惯再往深里想下去。这时候的大脑已经失去应有的功能,做为一个人只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活吃饭睡觉。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点点所谓的愿望,那也仅仅是盼着孩子快一点长大,至于长大了又怎么着?儿子的名字是斌,他姥爷取的,大概是盼他文武全才。女儿的名字是春雨,我取的,只是每个田舍郎对春天雨水的渴望,完全与诗意无关。
至于再多的期盼?不知道。根本就没想过。仅此而已。而已。
细想起来我到了那里学到的第一课竟是:原来可以这样骂人。
六三年初冬开始学习剪树。剪树不但直接影响到果树第二年结果的多少,还决定此树将来是否成长为有最大承载量的树形,直接影响几十年的产量。
学习的第一天由各队农学院毕业的技术员边剪边讲出每一剪的道理。大家围成一圈仔细观看听讲。结束后大家一起把剪下的枝条收拢带回,做为编筐的材料或做饭的燃料。
这是学修剪的第一天上午,大家正在小路边的一棵树下认真听讲,一位又瘦又矮的老太太从路边经过,弯腰拾捡剪下的枝条。队长看到说“别让她捡。”当时我站的地方离老太太最近,就过去制止。老太太抱着已经捡到手的枝条要走。那时的我十分认真地让她放下。老太太无奈地放下走了。
事情就这样过去。我的心思也回到了学习上。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老太太又回到这里,突然一屁股做到地上,一边用力怕打着地面,一边手指着一个方向大声开骂。骂的非常难听,什么没好心不得好死、什么丧良心断子绝孙,还有更难听的鲁迅所说的国骂都出来了。
围着听讲的众人回头看看并没人理她。大家仍然继续自己的学习。
由于我站的地方还是离她最近,我看她鼻子一把泪一把的顿生怜悯之心,觉得老太太家里一定遇到了很大的冤屈或不幸,甚至由她想到了我去世不久的娘,我娘受到冤屈与虐待可是连这样大哭也不敢呀!
既然我离她最近,怎么可以眼看着这位如此伤心的老人无动于衷呢?于是我走过去俯下身蹲到她旁边,十分同情和真诚地劝她说:“大娘你怎么了?遇到了什么事这样伤心?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这样生气会被气坏的。快想开点回家吧。”
我这样劝着,老太太反而哭骂的更起劲,几乎是伤心欲绝了。我真的给吓坏了,害怕她伤心过度会晕倒。于是用手去搀扶她说:“大娘,你住的不远吧?哪个村的?来,我扶你回家。”
不料我此话一说,老太太竟恶狠狠但又似无奈地瞪了我一眼,说了句让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话:“俺就没见过这样的!”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走了。
与此同时我身后爆发出一阵大笑。我莫名其妙地转回身,队长走过来说:“小邹啊小邹你可真是个孩子!你就听不出她骂的就是你吗?”
“骂我?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再说她是指着村子那边骂的啊。”
“你这个孩子,指鸡骂狗指桑骂槐你难道都不懂吗?”
“可是。可是我并没有惹她啊?”我仍迟钝地质疑。
“刚才你不是刚让她拿枝条的事忘了?”
我还真的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这件事让我明白那几根不起眼的枝条对我根本不算什么,可在这个几乎寸草不生的黄河故道,对一定十分贫穷的她来说,却是可以用来烧两顿饭的!从此以后在遇到村民来捡枝条我再也不管了。
多少年后我写剧本,很多看似不起眼无关紧要的台词和对白,都借鉴那位老太太指桑骂槐的启示,尽量做到话外有话弦外有音含蓄而富有内涵。

【溪流】 李东川摄
随意流淌的思绪,也许有一点会触动你,汇入你脑海中,成为你思想的亮点。
——编者的话

邹星枢
1946年生于济南故郡黑虎泉畔,性喜清涟而不耐浊浑。曾上山下乡、进工厂多年,创作的二十几部大戏在国家中心期刊及省级专业期刊发表或剧院演出,三次搬上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教学舞台;《绿帽子》由五十年代著名导演张琪宏和北京人艺、中戏及国家话剧院等艺术家在北京公演;中、短篇小说散见于《钟山》、《雨花》、《清明》、《百花洲》等文学期刊,晚年致力于随笔及诗歌探索。拍摄电视剧几十部集。 作者刻意追求的,无不是尽力摆脱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定式,努力探索共同人性中爱与善的张扬和恶与恨的批判、以及人的尊严以及生命权利的普世价值,至今致力于人的灵性和精神探索。

【游山图】 于受万画
编辑:李东川
2024年5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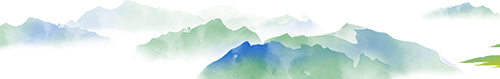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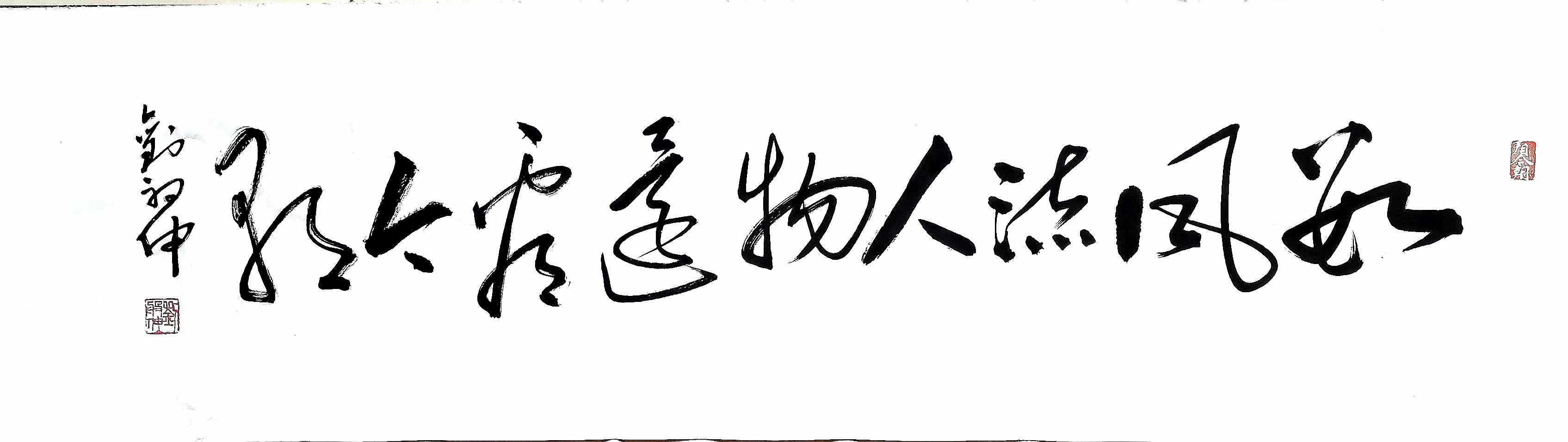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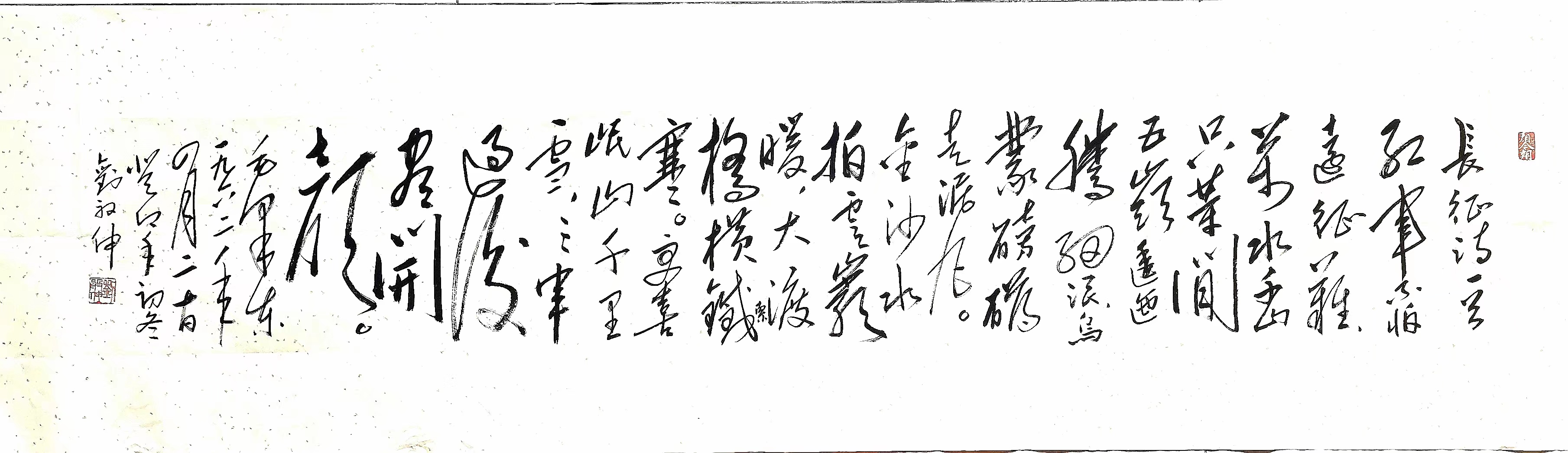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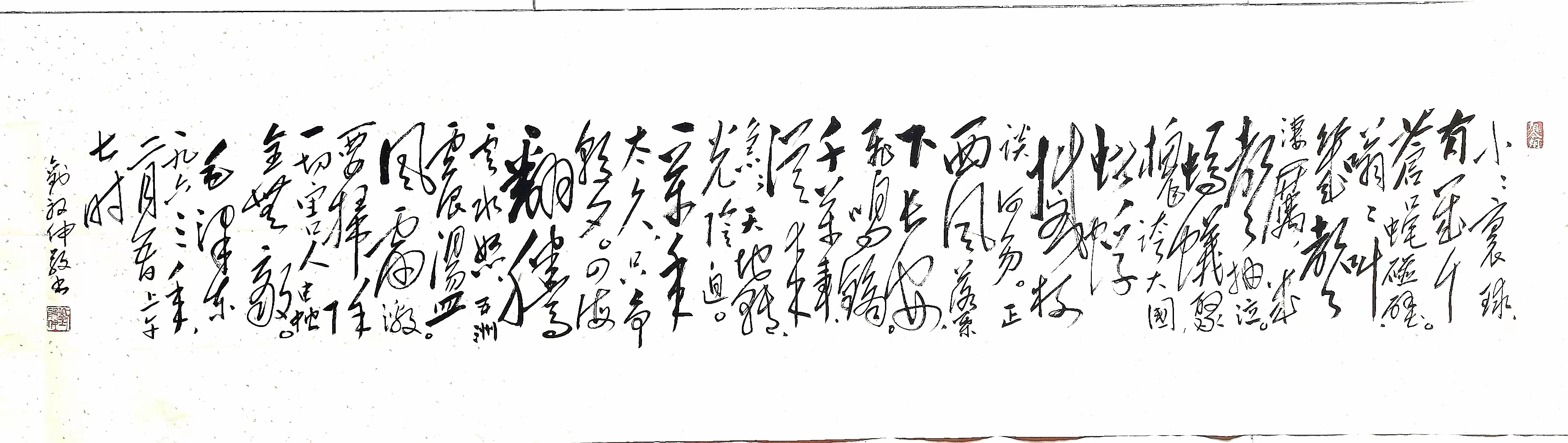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