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洪明 画
现代战争
一切都变得多么便捷啊。
从前的士兵握着冰冷的刀,
看见对方的脸,
看见对方看着自己。
血溅在他身上,
对方的表情印在他脑中,
扰乱他此后的梦。
现在一切多么便捷啊。
可以一边喝咖啡,
一边按下一个按钮,
就像关灯一样,
羞怯的人,孩子也可以做到。
多么整洁,
听不见尖叫,看不见尸体,
仿佛那些发生在另外的世界。
“都给我闭嘴”
楼上又吵架了,
听不清有几个人,
脚步奔突,什么东西掉落,
男人女人的高声。
然后我听清了一个男子的一句台词:
“都给我闭嘴”。
我仿佛看见另外的几个人,
在一种压力之下矮了下去。
我在他们的舞台底下,
无法看见他们。
电梯里遇见的邻居总是很平静,
仿佛一切是我的幻听。
冰山般的树
树是一种冰山,
只有一部分被世界看见。
它的根仿佛地上的倒影,
一棵向下生长的树,
被地心的太阳吸引。
它沉默而缓慢,
在黑暗中摸索,
最终让自己与大地无法分割。
它从大地深处的源泉汲取生命。
就这样,树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
但没有断裂,
在光与黑暗中它睁着许多不同的眼睛。
遗产
我们的祖先都死了。
他们留给我们一块玉,
现在它在博物馆里,
发着温润的光。
我们隔着玻璃,用目光触摸它,
然而无法佩戴它。
他们留给我们一把剑,
它在另一片玻璃后面,
依然锋利。
然而我们忘记了怎样使用它,
它不会再尝到鲜血的咸味。
他们留给我们一些方块字,一些诗。
这些一直活着,
没有像古树一样生出皱纹,
而像河流一样活着。
它们是我们每日的食粮,
从我们的口中说出,
像风,落在我们耳中。
我们沉默的时候,
它们睡在我们身体里。
我们做梦的时候,
它们像一群鸟,飞向四面八方。
蚂蚁说
其实我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在别人看来我们几乎相同。
我也愿意长生,
我对忙碌的生活从未感到厌倦。
然而我们总是很短暂,
危险在四面八方潜伏,
每天都有意外发生。
比如今天,
有几位同伴死于一个奔跑的孩子脚下,
另外几位迷路后,至今踪迹全无。
不过,谁不是短暂的呢?
在土壤中,
我们常常遇到比我们更小的生物。
天空
那弯曲在我们之上的寂静的天空。
它与大海相对,
同样的蓝在它们中涌动。
大海永远涛声起伏,
而它如同一面无言的镜子。
它弯曲在喧嚣的城市之上,
火车穿过的平原之上。
有时候风在它下面奔驰,
但不会触动它,
风的声音不是它的声音。
飞鸟的叫声加深了它的寂静。
然而当它骤然开口,
当雷电的火车滚滚而过,
它震动,一次次炸裂又愈合,
那时大海和大地都屏住呼吸,
像被恐惧攫住的孩子。
泡沫时代
持久之物越来越稀有,
或许它们一直都在,
是看不见的潜流。
而海面上涌出无穷的泡沫,
每个都闪着新的光泽,
每个都迅速破碎,没有声息。
新的欢舞紧锣密鼓,
将叹息和哭泣淹没。
太阳在天空悄悄行走,
又过了一日。
人们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散去,
昨日遥远得如同前世。
猫和草木支撑的世界
人很高大,
人所制造的,远高于人
——摩天大楼,火箭发射塔。
然而人带来一些幸福,
也带来许多痛苦,
人的制造常常近似于毁坏。
但猫是不同的,
它要求于人的很少,
给予人的很多。
草木对人没有要求。
人的天空常常向他压下来,
幸而有猫和草木支撑着它。
它们为人提供了庇护,
虽然它们未必有意如此。
迷宫
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迷宫,
飞过的鸟看见了它的格局。
道路通向道路,
通向一面墙,一棵孤零零的树,
通向起点。
人们每天在其中奔走,
有时向北,有时向南,
仿佛在寻找某物。
人们拥挤在路上,妨碍彼此。
迷宫向四周的平原敞开,
然而人们并不离开,
他们在迷宫里度过一生。
与道路和墙一样,
他们也是迷宫的一部分。
弦月
难以想象那是一块布满疤痕的石头。
在我们遥望的眼中,
它恢复为不占据空间的冷光;
一片没有瑕疵的玉,
切割成奇异的形状。
从它表面归来的宇航员,
夜里怎样遥望它,
怎样做关于它的梦?
在梦里,
他对它是向往,还是惊恐?

秦立彦,诗人,译者,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大学硕士、学士。出版有诗集《地铁里的博尔赫斯》《可以幸福的时刻》《各自的世界》《山火》,译有《华兹华斯叙事诗选》《我孤独地漫游,如一朵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等,并有学术专著《理想世界及其裂隙——华兹华斯叙事诗研究》等。曾获人民文学奖,丁玲文学奖,李叔同诗歌奖诗集提名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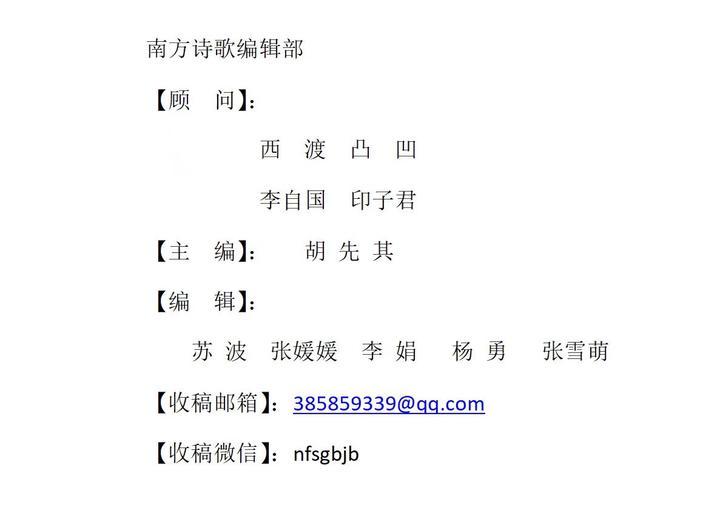
《南方诗歌》2021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2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元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二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三月目录
冯晏|抵达赛音山达能量中心
白一丁|在雨水中奔跑
“他山诗石”:高兴 译|手掌中的萨拉热窝
潘以默|一个客体主义者的征迁记
海春|我与死亡不可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