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纳丁·穆萨贝戈维奇诗选
塞纳丁·穆萨贝戈维奇(Senadin Musabegovic,1970— ),波黑著名诗人,出生于萨拉热窝。大学期间攻读哲学,后留学意大利,获博士学位。现为萨拉热窝大学哲学院教授。曾多次访问中国,参加过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十分羡慕中国和平繁荣的景象。而他的祖国却饱受战争磨难。萨拉热窝被围困期间,塞纳丁曾参军赴前线,并担任过军队记者。战争期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出版《身体打击》(1995年)、《祖国在成熟》(1999年)、《天堂般的星球》(2004年)等诗集。
波黑战争给塞纳丁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他的诗歌大多将战争中的人性、情感和心灵体验当作自己的诗歌主题。他的诗歌凝练,硬朗,不动声色,摒弃简单的道德评议和是非判断,只是注重细节描写,并通过细节描写来呈现、发掘和提炼人性、心灵和情感。而残酷的战争背景,又让他的这些人性、心灵和情感诗歌获得了特殊的张力、感染力和震撼力。诗人期望他的诗歌能让人们意识到战争的恐怖和残酷,更期望他的诗歌能唤醒人们对和平,以及美好心灵和情感的热爱和珍惜。
译 者
祖国在成熟
他们领我们走过长长的走廊,
让头发散落在我们刚刚剃过的脖子上,
贴着粗糙的衬衣领,
就像贴着一名军官的刻满黄色水疱的手。
他们将我们拽进换衣间,
脱光我们的衣裳,
让我们步入唯有换气扇在转动的房间:
棉袜的印痕在淡淡的静脉上泛红,
三角裤的裤带将皮肉挤在黑黑的肚脐旁,
白色的背心在肩膀上印上两道红线。
他们命令我们排好队,
带我们去淋浴,
让冷水洗去我们所有的耻辱,
我们的父辈用手指注入我们皲裂的皮肤里的耻辱。
他们让我们套上僵硬的制服,
朝我们大声吼叫,
让所有纽扣下面故土的温暖抚摩我们的呼吸。
他们让五星肩章那红色的唇膏替代女人的吻,
涂抹我们汗津津的额头,
英雄的血已在肩章上凝结。
夜里,
他们给我们看黄色杂志,
让我们一边手淫,
一边齐声恸哭。
这里,
没有隐私,
没有茅厕。
他们让我们面对面蹲着,
眉头紧皱,
青筋直暴。
洗完脚,
我们钻进床单,
梦见自己扯着举起的命根跨过静脉。
他们让我们把血缓缓地滴在绷紧的内衣裤上,
滴在擦得锃亮的地板上,
在我们用水果浸润肥沃的祖国那干瘪的乳房时,
让尘土变成地板裂缝中红色的颗粒。
“起来!”
茫然中
我们用指尖将塑料纽扣
塞进汗津津的衣领上
窄窄的扣眼,
他们让我们在身上搜寻内在的敌人。
喘息
在古老的阿尔法科瓦奇墓地,
我将手掌转向天空。
雪花纷纷落在上面,
将我的手掌变成一幅新地图,
从中我看到世界所有的隆起物
都在
我的呼吸上
旅行
***
我吹掉手掌中的暴风雪,
看着雪片滚动,
变成白色粉末,
给予我的手指
触碰
万物的轻盈感。
***
身旁,白色的墓碑,
尸体最后冻结的叹息,
仿佛月亮低垂着头
羞怯地挤压着天空。
***
雪飘落,让这个世界更加柔软。
白色的裹尸布下,万事万物仿佛
都已退回自身,
只是为了
在柔和的
呼吸中
低语秘密,
当母亲祈祷时,
那缕缕呼吸就聚拢在她白色的丝巾下。
***
事物从白色的雪帽下面偷窥,
酷似那些受伤的天使,怒气冲冲地
靠近我。
***
上帝呼了一口气,创造出世界。
我望着手掌中的萨拉热窝,
我画出新的山丘,
我触摸分离。
一名孕妇肚子里
孩子的踢打让我困惑,
我用一枚婚戒
在衣裙下面
摸索着走路,
我变成一位老人的手指,
他一边想象
一边用手掌撸了撸自己胡子拉碴的脸颊,
同他儿子一模一样,
在白色的石头下面
在泥土的芬芳中,分崩离析。
***
我透过那些孩童的眼睛打量这世界,
他们正在焚毁的图书馆的墙壁间玩着打仗游戏。
他们相互杀戮,故意摔倒在挖掘过的地上,
呵呵地笑着,
呼吸滚过参差不齐的牙齿,
而成长的恐惧正在闲扯。
***
唯有垃圾堆上那只黑猫我无法吸入。
她没有露出凝视的微笑,
她静脉中的血正在冻结,
她的肺部出现一颗颗冰粒。
对于我的凝视,她已过于清晰。
吻我祖母的头巾
我们正坐在公园长椅上。
你张开嘴巴,想要吻我,
在你口腔深处
我看到黑暗正在贴近我。
里面,我看到
被捕获的鸟的羽毛花衣
在猫的哈欠中反射。
里面,我看到一只狗,
在战争荒原上游荡,
他满怀思恋地想起主人的衣领,
将爱抚塞进楼道旁灰色的垃圾箱里,
在他洁白的牙齿下,
一顿家庭晚餐的残羹剩饭正在溶解,
粘住了一份色情杂志的
纸页
里面,我看到一个姑娘的颤栗,
就在她通过话筒
与她男友低声细语的时候,
与此同时,狙击手的子弹之吻正在飞近,
将窗户纸撕成
斗鸡眼的形状,
透过它
凝望午后房间的
寂静:
公园长椅红色的木板上,生锈的钉子,
渗出一小团一小团的颜色;
白杨树顶,绿叶舔舐着吹来
犹太祷告的风;
我们两人冰冷的脸上,一声尖叫
犹如一咎黑发
滑落。
里面,我看见自己,
在屋子里,唯有冰箱在嗡嗡作响,
我在祖母床前俯下身来,
她的脸,
盖着用细线绣着
天堂孔雀的
沾满斑点的头巾,
正慢慢融化。
当她吐出最后一口气时,
她那皲裂的粉红色嘴唇
紧紧贴着那副嘈杂的
假牙。
苍白
我蜷缩在战壕里,
无聊透顶,
就用一支红铅笔,
试着
描绘世界。
事物消失,在那些唤醒它们的尖锐线条
之下,
唯有白纸的空无吞噬一切。
有人将天空涂成了
白色,我被画进天空,仿佛被画进一个疯子的眼睛;
有人将树根涂成了
白色,那些树根肿胀得犹如
推搡我们的手臂;
有人将落在我们头上的
金合欢涂成了白色;
有人将我走向你的
步子涂成了白色;
有人将我母亲的
凝视涂成了白色,
她还在想
死神
一定抓不住我的。
离别前,收集小雕像
蟋蟀的鸣叫中
你的瞳孔
扩大
又
收缩。
我们已相互说出一切,
已经发生的一切。
惟有你眼帘的触摸
掩饰
又
组合着
世界的形象。
他们烧毁了城市,
有人已将街市洗劫一空。
城里,一切都已发生。
一个小女孩
破裂的头颅之上
红色的天空得以命名。
城里,一切都已发生。
彩色的衣衫散落一地,
相互刺杀的时刻,
一阵突然的推搡,
我们看到自己的梦粘在一起,
冻结于一个玻璃瞬间,
比我们肉体的在场更加有力。
城里,一切都已发生。
当月亮从老刺槐树上投下
影子,
清真寺前,
人们传送着白布裹着的尸体。
白桦树的低语融入他们的呼吸。
他们用手传递着,
在手指的轻触下
尸体滑动,
经过,变成一个
正与他们分别的美人的白色的呼吸。
城里,一切都已发生。
就在我们离别的时刻,
你说着我的名字,
当面烧毁了我的照片。
一丝红色的唇膏
印在你的右犬齿尖上。
你嘴唇上的血块
渔夫将鱼从海里钓起。
鱼嘴已被鱼钩撕裂。
天空的蔚蓝中,她看到
海的深度全都流进了自己眼里。
你沉默不语。
你抿紧嘴唇,
嘴里,
嘴里某处
你发出一声尖叫,
尖叫声中,天空扩展,
尖叫声中,海的崭新的蓝色变得更深,
尖叫声中,鱼的眼睛可爱地凝望着你。
你嘴唇的鲜红中
聚集着世界所有的秘密,
你张开嘴,对我说了些什么,
但话语顷刻被风吹走,
那一刻,恰好风吹过你的嘴巴
将海盐储存在
你洁白的牙齿下。
你在我身下爬行,
就像野兽爬进兽窝。
你的恐惧紧贴着我毛茸茸的皮肤。
为了忘掉自己,
你用手撸了撸我的眼睛,
指尖压着我黑色的瞳孔,
模糊了整个世界。
在你的手指下
我慢慢消失,
勉强能
听见
那
鱼
用三角形的
鳍尖
击碎
蓝色浪涛
折叠的
镜子。
我将头从你身上移开
转向
太阳的头。
我们面对面站着。
它黄色的凝视
像子弹
射向我。
击中。
被黄色。
我的眼睛
将我拽了进来,
并在我心底
拉上一道黑帘,
我看到身体溢出的所有色彩
纷纷流进我的眼睛。
一个女人的头发掠过我的脸,留下痕迹
我们整夜都在争论。
只是到了凌晨,
听到鸟儿的鸣叫时,
我们的思绪
才得以重新想起了
世界。
头顶上环绕的人群,
迷迷顿顿,
将夜晚星星的动静带给城市。
你告诉我每颗星星上面
某位逝者
此刻都在望着我们。
尖锐的鸟喙击打着窗户,
击打声中,蓝天
在我们之间
震颤。
我在波尔吉内挖战壕。
一名狙击手开始射击。
我扑倒在地,从那里可以看见萨拉热窝。
一只鸟影从我头顶飞过,
轻触了我一下,犹如女人的头发。
白衬衣下面,
死亡所有的柔情扭动着
涌上我的胸口。
我站起身来,思忖:
——鸟影总在坠落,就像一具冰尸跟在我们后面走动。
灰尘在外科手套上呼吸
房间里,
唯有锁孔中的钥匙链,
伴着绞刑架的声音在晃动。
下面,
一个小丑的头,
红红的唇,
僵硬的笑。
火,犹如发威的火车头,
载着我们,超越我们自身,
超越我们粘在一起的骨头,
在汗津津的情人的拥抱中。
你说出“火”这个词。
词里,我看到一束火焰
焚烧你的嘴,削去你的牙和脸,
用红红的舌,舔舐你的两颊。
当你走得更近时,
你身体的芬芳在房间里弥散,
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我的凝望下,你的皮肤开始
劈啪作响;
你微笑的声响
在我红红的唇上脱落。
你的凝视,
努力够到我的发尖,
从眼睛里跳出;
那肿胀的乳房
溢出你的身体
犹如
一只粉红的、破碎的、神圣的眼;
你腿间的黑色缝隙
正低声哼着
一首童年的
摇篮曲。
你朝我
分开,
伸展,
拥抱并
吻我,
这时,
一颗炸弹
在附近某处爆炸。
静谧中,
我们听到教堂的钟声。
钟声里,我发现我们成为天使,
教堂的左侧,
陷入无形的色彩,
我们的眼张开,
盯着潮湿的墙,
等候死亡。
我对你说:
“我们应该做爱,
因为时间在流失。”
此刻,某地,
倒下的战士
正僵硬地躺在防空洞里。
以添加剂为食。
蛆虫进入不了他们。
他们的脸已同身体分离。
随后,有人会将他们尸体的呼吸
宣布为民族光荣。
你对我说:
“我们应该做爱,
因为明天,手术台上,
外科刀下,我们兴许会相互
微笑致意。”
停火
物体利用日落
投下影子,
以便分离。
我感觉脚步里
响起了被弃物体的回音,
当我朝着
在光中
闪烁的
破交通灯那红和黄窗格玻璃眨眼时。
其余细节在繁殖。
一只黑猫跃过一块白色的路标
尸首一般,干燥的柏油马路上的前列腺。
一个女人在整理自己的红发簪,
当光线分解她的脸的时候,
手指触摸了一下红别针,
别着一只塑料蝴蝶,尴尬地前倾,
飞行中被捕捉的样子。
自始至终
我都听见孩童的声音从商场前的公园传出。
他们在朝一只赛特犬吼叫,
那犬被搞糊涂了,
跳跃着,分不清
到底是嘲弄,还是威胁。
恐惧中,
事物存在,唯有当
它们的影子同样掠过他的嘴唇的时候。
在朝向地面
不停转圈的黄叶里,
某人的凝视
发出了一声尖叫。
复活
独自在家。
被抛弃。
硕大的家具瞪着我。
从锁上的门里,手指的气味四散。
无人走进我,
我在旋转。
每件事情都在经过我,我厌倦。
我明白,父亲的衬衣于我太大,
但穿着它,我可以捉住鸟儿的恐惧,
但穿着它,我可以飞越母亲,
但穿着它,我可以感觉天空的颜色。
我在公园里游戏,正对着老教堂。
我走近它那影子般的内部。
香气的芬芳令我晕眩,
我看见那具钉在十字架上的
肉身。
我悄悄潜入他的喊叫。
我捕捉让他无法张开双臂
飞翔的
恐惧。
我的肉身慢慢变成石头。
走出教堂,母亲的手拉住我,
父亲的婚戒在上面
闪烁
犹如凯撒的金鞭,
那金鞭,对于藏匿于一缕缕
黑色卷发之下的安东尼的目光而言,
已经显示出罗马所有遥远的
角落。
不合时宜
此刻,
走了这么远,
我在悉心听取战争细节,
河水的喃喃低语
扩散着
通过我的耳朵,
就像蘑菇
刚从腐肉上
长出嫩芽。
此刻,
词语为我命名,
在我眼前滑动,犹如被碾压的炮灰,
面对它们,
我将两手插进口袋,
以免用触摸
伤害这个世界。
此刻,
万事万物都朝我倾斜,
我感到羞愧。
那羞愧舔舐着我,用树影
酷似士兵的
舌头,
当他们
啃咬
尘土时。
此刻,
目睹用橙色书写的世界的残酷,
我藏在树荫下,当树呼吸时,我的颈项
叹息着,犹如母亲的乳房,忘记我的存在。
此刻,
我用一根针保护自己,抵挡一切,
那根针沾满了
来自女友的血滴,
她曾用它扎耳洞
并戴上
狮子头
耳坠。
此刻,父亲的断手
用白单子
紧紧包着,
开始抚摸我。
此刻,
从童年起一直跟着我的流浪狗注意到了我。
我们相互面对,
他和我,
我们相互凝望并理解。
在那受伤的动物眼里,
我融化为
闪光的粘液,
惟有黑色的眼皮
还在
慵懒地
睁开,
再合上……
闪回(之二)
起床的时候,
透过晨曦,我看见
我睡过的
枕头上
有个黑洞,
是那个消失的家伙留下的,
整夜,我都在
同他搏斗。
那个黑洞,
一个巨人的脚印,
就像伤员的断腿,
让我浑身
发痒。
闪回(之三)
我在镜子前站定,
对面,
我的皮肤从我
身体剥落,
并且
黏住
冰冷的玻璃。
两只对称的圆眼睛
从我的眼袋里生出,
就像两匹狼。
嘴唇伸展时,
下巴从脸上掉落。
三角形的鼻子在呼吸中瓦解。
脸上新生的胡须打破皮肤的柔软
唤醒那个整夜都在攻击我的野兽的形象。
我伸直弯曲的手臂,
满心欢喜,
因为唯有幸存者才了解真实。
洗着
我的脸,
它像一片泛黄的碎裂的叶子,
透过一滴水落进
白洗脸池,
爬进
黑下水道的地下,
同一簇簇头发一起
漱口。
擦脸时,
白毛巾下,一切各就各位。
我的脸归整好自己。
擦去水滴时,脸变得更加平滑,
白毛巾带给它崭新的柔软。
一个手势就足以让一切
洁白,
干净,
犹如早晨天空的封面憩息于
殉道者眼睛的
边缘。
猫叫
隔壁房间,那只老猫奄奄一息。
你朝她俯下身来,
唤她可怜的宝贝,
摩挲着她干枯的肋间
起皱的
皮肤。
在屋子幽暗的角落里,
她看到她最后的
呼吸,
对我们竖起毛发,
缩进
又
伸出
她的爪子。
那一夜,我们睡在一起,
你张开嘴,躺在我臂弯里,
说我让你窒息,
用指甲抓我,
呼吸贴住我的肋骨,
皮肤从笼子里垂下。
翌日,
老猫被埋在
大门旁的
花坛里。
早餐后,我们做爱。
老猫的黑女儿跳到我们身边,
用毛发抚摸我们,
身子扭动,如你的臀部。
你生出
嫉妒,
呵斥她,
用脚趾将她踢开。
我笑了笑,打起了盹。
我梦见自己躺在大门旁的花坛里,
器官变成山谷中的开阔地。
我的脚趾尖呈叶状,就像两棵
茂盛的
白桦树。
我的肝脏在一棵雪花莲的腰部弯下身来。
我的眼睛长成两个孤独的灌木丛,彼此
相望。
我的牙齿掉落在地,变成尖锐的石头,切割
你的裸足。
我的眉毛间长出猫的毛发,像我儿子
在你子宫里的
胎毛。
醒来时,你说了声二椅子!
你砰的撞上门。
黑色的缝隙
蹭着
我的胸部。
黄昏时分,
黑暗聚拢在房间周围,
孤独
像只黑猫
发出嘶嘶的叫声。
在你的眼睫毛尖上
你睡觉的时候,
我看见
灰尘落在你的眼睫毛上。
你曾用它们来测量
我的身体比例。
此刻,在它们的飘扬中,我在你的梦里
察觉出自己的姿势。
你的呼吸突然改变了事物出现的方式。
它靠近它们,缠绕着它们,
就像那只暹罗猫在你的
梦里喘息。
最后,它敏捷地脱身,像男子的手
在你的梦里
将你拆分。
它让我化为
尘粒
落在你的睫毛上。
从你的眼角,
我改变了
你梦里世界的
形象。
一名士兵的剪贴簿
这里,天空在嘲笑我们,
扭曲我们的脸。
睡眠中,
我们的性器跟随着它的路线,
渴望重新勃起,以便穿越它。
它们的重量落在我们身上,
弄醒我们,
仿佛一道目光沿着枪管
穿越
那
死者。

高兴,诗人,翻译家。曾任《世界文学》主编。出版过《水的形状》《米兰·昆德拉传》《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孤独与孤独的拥抱》等诗集、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等图书。2012年起,开始主编“蓝色东欧”丛书。主要译著有《我的初恋》《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水的空白:索雷斯库诗选》《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尼基塔·斯特内斯库诗选》《深处的镜子:布拉加诗选》《风吹来星星: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等。2016年出版诗歌和译诗合集《忧伤的恋歌》。曾获得中国桂冠诗歌翻译奖、蔡文姬文学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西部文学奖、捷克扬·马萨里克银质奖章等奖项和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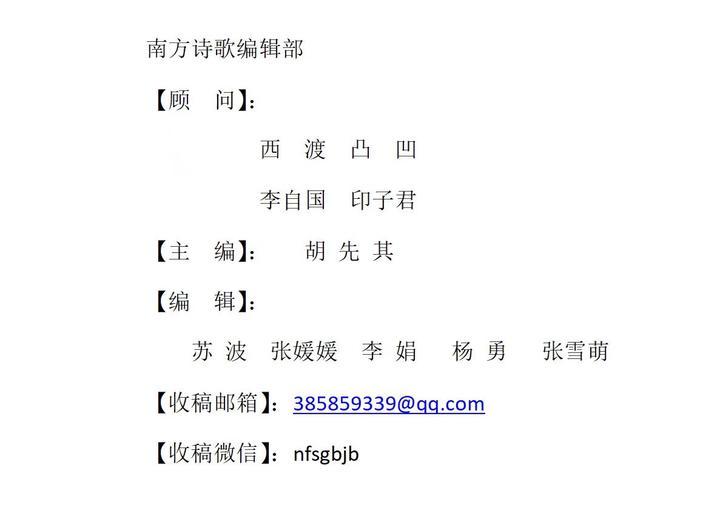
《南方诗歌》2021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2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元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二月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三月目录
冯晏|抵达赛音山达能量中心
白一丁|在雨水中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