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崴(台北) 画
卢家山杂忆
驮物上山的马
被一把磨出脾气的岩刀杀了
不好吃的马肉,太好吃了
去山下村小上学,群狗扑来
飞石打瞎一只狗眼
准头之好,瞎猫撞上死耗子
一间教室,两个年级的演讲
一块黑板
左右都红得刺鼻、硌眼
采蘑菇吃,一个排中毒
我人小量小,成为漏网之鱼
为这个,阴到笑了好些年
是傍晚。那位白胖得不像话的叔叔
用刮胡刀自绝
一盏灯死了,又活了
莫名害天花
趴在家父背上夜奔。一脸凸凹
还给了突然的人世,更突然的坎坷
砍柴,弯刀脱手,飞落崖下
至今插在心窝。一到下雨天
卢家山就在弯刀上打颤
2022.12.10
注:卢家山,罗文境内,当年万源县五七干校(后名共大农场)所在地。作者曾随父母居住此地,念过一阵小学。
死亡诗
黑夜被野猫的眼睛和爪子延长
爱情的气息,情爱的焦虑
像裹尸布包裹着我们走下去的路
即便依然有空气中的稻草可供呼吸
即便还在路上,也成行尸走肉
春天在的,国家跟我
如一片落叶,离开树枝的大地
久久不能抵达母族的故乡
好消息像坏消息一样好,坏消息
像好消息一样坏。属于我们的
苹果,总也砸不到我们思想深处的牛顿
大河倒流、失火,火山下雪、结冰
身体中的任何一个关节
都是冰火两重天
刀枪、毒、水、硬物和高差
无不是时间的动词、险词与日课
这一周,想法绝决、怀柔
特别短促:一如黑猫的利爪
特别悠长:一如黑猫的泪光
2020.11.25
绝望诗
我说,太阳不会打西边出来
你说,快看,在高速的倒片上
爱因斯坦活过来了
我说,太阳不会下雪。你说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走过雪豹的高原
我说,她早已忘记我的存在
你说,因为她压根不存在。我说
我太短,而时光又太长
你说,你说得对,没有哪个人
可以跟时光争高矮、论短长
你说,时光就是我们祖先用死亡
修的房子。我们承继、修补、安住
不厌其烦,传给我们的我们
——那些方方正正的自圆其说
我说,可我怎么说呢
你说,说什么都行的
瞧,就这样多好——
我们这一说,都说了好几个世纪了
2020.11.23
郁闷的长相诗
职场,长得像上司、同事和客户
商店,长得像柜台的嘴巴和唾沫飞溅
家中,长得像这个那个亲人
年份酒告诉我,在一些酒的年份
长得像暗藏的、不为当事者所知的
情敌。长相,画在我身体外边
在别人的镜中放羊、驯马、做怪相
却在我身体里扎营,修筑城堡
记不得从哪一个暮春开始
我把我写作和游泳这双老手
全部抽调出来,向身体的大后方进军
左手寻找包块,右手拆除包块
是的,到了我这里
长相大变,营房、城堡全是托辞
无不以包块真身示人
大如游丝的呼吸告诉我
一些包块是气做的,还有一些包块
也是气做的。上个月,我从区医院出来
血糖高得直逼糖尿病的山门
长相像糖,尤其像
一串熟透的葡萄胎句式的糖
2020.11.22
上床睡觉诗
上床睡觉,一些人一动不动
一夜无梦,完全不知自己睡没睡觉
另一些人,一动不动,让一册梦
做得比西游记更扯蛋,也更靠谱
还有人把觉,睡成了体力活
——干革命干事业般拚命。一匹马
又一匹马,将床跑得比草原和运动辽阔
比门缝和一把指纹锁逼窄。上床睡觉
与年龄有关,与国家有关
与风吹草动不见牛羊有关。进入中年
我的觉没有哪一天踏实过。即便
把自己灌成酩酊大醉
也会在二三个小时内惊醒,辗转反侧
冷汗与口渴可用同样的修饰与比喻
结为同志。现在
床是一个平台,一动不动
人生一分为二,在睡觉中睡觉
当床,一夜之间猫进主人的身体
令上床与睡觉拆开——
亲密粘合中远远背离
不太平的床,才会消停下来
成为时下真理的佐证,假寐太平的措辞
2020.11.5
上路诗
该上路了。上路的日头到了
不管上哪条路,都要跟亲人、故乡和
内心的秘密告别,都是我跟我的永别
时间与时间的背叛、割袍和
不再见。一个人一生只有两条路可走
说第三条路还在路上,纯属小说虚构
一个人一生要上很多次路
条条像鞭子。平顺,陡峭,宽窄
以及重复、逆转、突然,都是路
连酒窝、蝴蝶、伤口,也是。该上路了
上路的香炷到了。不管活多小年龄
多大岁数,每一次上路,都是
少年负气、老年深虑——都是理想国
把远方的路,扛送到面前
在上路的词典里
有人用前行上路,有人用后退上路
上路即上道、入道,即着道。一辈子
被路的河流放逐、捆缚、拥抱
是幸福的。幸福里有满满的对血缘的感恩
和仇恨。该上路了。上路的美酒到了
有一种上路,一生只有一次
这条路横竖都是竖,要么上天
要么下地。像回头路与断头路
不沟通、不和解、只求背道而驰
老死不相往来。也有另外的剧情
回头路就是断头路,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但没有谁能把一条路走通顺
走到黑,正像没有谁能把一个造句
制造至完美。最痛苦的上路,不算上路
因为内衣里的建筑美学
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式态
2020.11.5
病房诗
一座病房的心肝,住着很多病房
一个病人的身体,住着很多病人
这天,从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
从一个病人到另一个病人
我看见病人拖着病房,那么多
在我身体的廊道进进出出。探病人的我
仿佛与暮秋交换了场地
我看见我的肾脏开始打雷,听见
腹部下霜。肉里的太平间
一个词在为另一个词作尸检
当我打通一亿万年的关节
终于回到春天,我发觉我的仁慈与诗歌
早已狼狈不堪,老得只能手语、吃流食了
2020.10.27
镜房诗
这些天,我只想躲进一间房子
一间有门有窗的房子,一间被玻璃镜
覆盖了六个维度的房子。我要
自绝后路,不再想、不再愿
与世界同框。为了让细胞中的月亮
等待周三的复检,我让未来的我出面
放弃了八十年代诗派领袖人物的
饭局;天府广记三部曲
摆在宽窄巷的梦酒,也是
滴酒未沾。这些天,我要素茶淡饭
清心寡欲。我要拿出
九十年代办装修公司的本事,把房子
好好装修一番,让玻璃镜成为
所有的硬装与软装,唯一的
饰词与逻辑。在这里
出门进门,进出的是自己。开窗关窗
开关的是自己。我打碎六个方向的我
却有无数个我,从碎片的雪地
与太阳中露出脸来,跟着我点灯
微笑,做一些从未做过的鬼动作
即便我怎么去赴死,都有无数个我
在我死去的地方活过来,闪闪发光
2020.10.27
别墅区轶事诗
这片浪波的土地太新,新得
只有夜间才能听见一片树叶
和一缕猫毛掉落的声音。至于
人类白日梦,永远够不着竣工的响器
无数美学的动静,比
各种皮囊下的建筑与脾气
更复杂、澎湃和吊诡。一觉醒来
业主群爆棚,看见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遭到今天的强拆。那些
搭建的草原、蓝天、乡土和巴黎
——那些从房产证上延伸出去的平台
纷纷坍塌,如一道
流星雨的瀑布。这一事象
令我想起园区外的某些地方——
闹市,田野,和一些字词句的
拼积木游戏。二者相似得那么迥异
思想的机具在哨子的间隙
掏耳,低头,紧张茶歇
2020.10.21
洗水诗
以水洗水,这有什么不好懂
就像钱洗钱,空气洗空气,血液
透析血液,人排开人
过去的成都,茶坊里的上等水
必须是锦江的活水,必须是
一遍一遍水洗水
这样的水,才能让娇嫩的蒙山顶上茶
在体内的铁骨与壶胆里醒过来
让一千年前死过去的茶客
一千零一年地活过来
洗水是一件充满想象的活儿
其危险,远不是洗一张草纸可比拟的
正像我的老家,让一袋汤圆浆
沥水变干的办法,不是拿太阳晒
而是瓮在水中,以水逼水
跟这样的文化比文化
诗人的想象与能力,多少有点水
多少是多少?半罐子吧
2020.10.13

凸凹,本名魏平。生于成都西都江堰边,现居成都东龙泉山下。诗人,小说家,编剧。出版有诗集《蚯蚓之舞》《桃果上的树》《水房子》、长篇小说《甑子场》《大三线》《汤汤水命》《安生》、中短篇小说集《花儿与手枪》、散文随笔集《花蕊中的古驿》《纹道》、批评札记《字篓里的词屑》诸书20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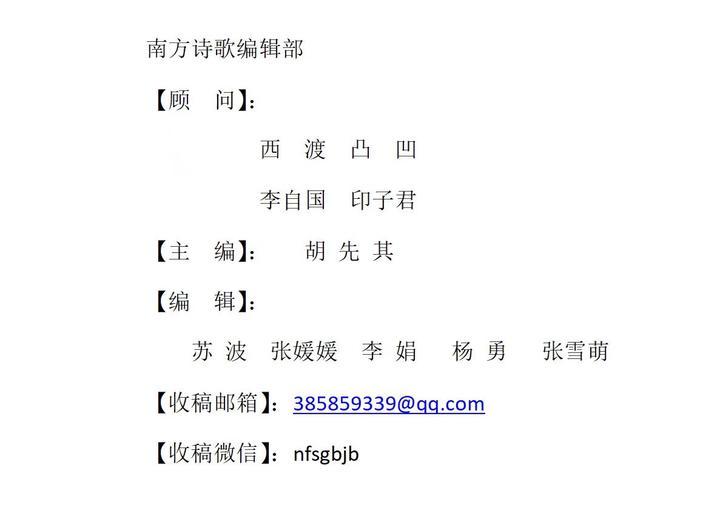
《南方诗歌》2021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2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元月目录
季羽|盘旋地日子没有安魂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