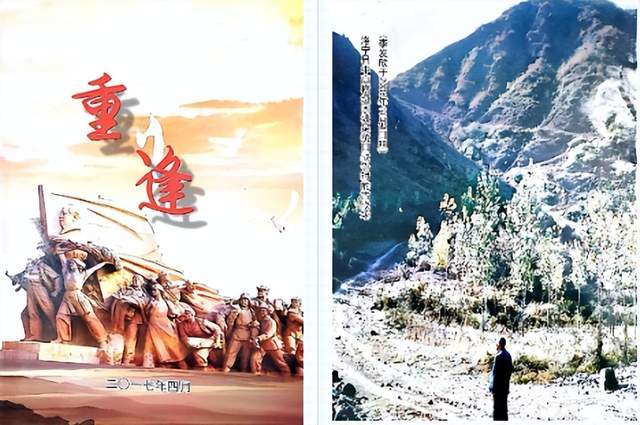
四、团圆
(3)
经过一天多的奔波,火车、汽车的漫长旅程,2016年6月5日,发喜终于重返刘家峡,这个他阔别了50多年的地方。刘家峡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旧貌换新颜。当年小川、红柳台、砂石料厂和一排排泥皮房的工程局办公地,以及工程局门前那棵拉引体向上的小枣树,如今已经长大,郁郁葱葱。
往日摇摇晃晃的索桥已被那单跨黄河的第一桥所取代,桥下河水汹涌澎湃。一排排高楼和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高耸的大坝造出了一个碧波荡漾的湖泊。游客们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刘家峡啊,你是黄河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为人民造福,必将永放光芒。
发喜来到1960年春天建成的大楼,站在楼前的广场上,他陷入深思。这座大楼依然屹立不倒。在二楼西头,有两间办公室,是他当年在技术处定额预算科工作时的常驻之地。今昔交织,记忆与现实似乎交织在一起。他怀念同室的同事们:张观景、黄丙灿、何聚秀、石传政、国真和陈树梅。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
他走进大楼,感觉这里依然温暖而亲切。无论现在变化多大,这个地方在他的记忆中始终如一,它代表着他的青春岁月。
日月交替,新旧更迭。在时间的流转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深深印刻在记忆中,成为无法忘怀的过去。
这些珍贵的片段,或许是温馨的家庭时光,或许是青春的激情与梦想,亦或是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
无论时间如何变迁,这些永恒的记忆将永远闪耀在心灵深处,成为我们前行的力量和温暖的港湾。
6天过去了,李发喜仍未找到任何一位当年的老同志。于是,他向电站管理局提出了寻找当年土建团赵清海的请求。
电站管理局办公室的同志们对此表示惊讶和疑惑:“电站建成后,那些人员早已分散各地,我们也不清楚他们具体去了哪里。五六十年过去了,去哪里找那些人呢?”
发喜无奈地沉思了一会儿,问道:“你们组织部有没有保存当年的档案?”
一位同志回答说:“当时的人员调动频繁,档案都随着人员转走了,组织部并没有留下那些人的档案。”
发喜沉默了,他思索着,却又感到无可奈何。于是,他慢慢地从挎包里拿出了他以前在刘家峡工作时的一些证件:
1.刘家峡水电工程局职工医院医疗证。发证号数:7118;发证日期:1959年11月30日;姓名:李发喜;性别:男;年龄:23岁;籍贯:河南;职别:干部;服务单位:组织部;医疗待遇:公费。
2.1959年12月30日颁发的截流现场胸前戴的工作证。姓名:李发喜;单位:工程局施工处;职务:查定员;发证日期:1959年12月30日。
3.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函授生新生手册和学生证。专业:河川枢纽水电站及水工建筑专业。邮寄地址:甘肃省刘家峡水电工程局技术处定额预算科。
4.1960年元月4日的甘肃日报,上面有关于1960年元月1日刘家峡截流胜利的全部报道。
这时,办公室的几个人都分别看了李发喜所带来的证件证据。他们突然站起身来,赞叹道:“啊呀,原来他是建站的功臣!您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说明呢?”
李发喜讲述了赵清海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以及他现在唯一的渴望,希望能够使他的家人团聚。
“好的,原来是这样。”办公室的几个人都回答道。
最后,办公室主任张孝先说:“自建站以来,所有的历史资料档案都在档案室里,但是查找起来不太方便。即使你找到了他的名字,也不一定能在我们这里找到他人,因为建站的那些人早就分散到各地去了。现在,‘黄河干流阶梯开发计划’已经基本完成,我们已经建成了总容量5744亿立方米的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这使得黄河几十年来安然无恙。这彻底打破了1950年在印度举行的国际防洪会议上,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曾经悲观地预言‘人类永远不能征服黄河,几千年之后,中国华北大平原也可能变成沙漠’的谎言。”
“不过,黄河上最后建的一个大电站是小浪底,工程于1992年9月开始建设,目前还不确定所有的人员是否都转移到了那里。”
“啊,小浪底!那是我们洛阳市的大工程,可惜当时没能去参观一下。”
听到这个消息,李发喜知道黄河已经被驯服和利用,这个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感到非常激动,忽闻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便心驰神往地说:“好,我一定要去小浪底看看。”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李发欣,1933年4月生,洛宁县底张乡中高村人。1955年7月参加刘家峡水电站建设;1961年奉命到江西拓林电站支援建设;1963年回到底张乡石井头翟家村担任民办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