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云飞 《孤勇者》
1、一个令人欣喜的迹象
2023年,以张伟栋为代表的几位年轻学者提出了“未来诗学”主张。从批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代表着当代诗歌批评在理论建构上有了超前的自主和独立的思考。随着这个话题在讨论中其概念和建立的缘起不断趋向清晰,特别是2024年1月20日我和一行在微信上对话之后,我对“未来诗学”的理论着眼点和目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张伟栋的几篇文章和讨论会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理论深受拉图尔、斯洛特戴克、维利里奥、维尔诺等当前最活跃一批思想家的影响,批判的对象是现代派和后现现代派建立的诗学思想,批评的手段在历史方面,去历史原境化,通过历史构境试图重构历史;在面对现实方面,重新审视现代的否定性和后现代的破碎性写作实践,通过对“诸众”(维尔诺)话语的关注,以及网络和数码技术对人主体虚化,重新建立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命运、人与自然、人与神话的宏大叙事以及多元写作可能性。
这也是我近几年重点思考的问题以及方向。我对西方哲学、宗教思想做系统梳理就是要厘清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发展的轨迹,洞悉西方思想在近当代为什么如此发达的本质,以便反观我们自身在文化基因、思想套路、语言模式、想象力等存在的诸多局限。
从方向上说,我支持他们开展的理论探索。不过,我对这个理论目前一些观点自身成立与否也产生了诸多疑问。比如他们把批判的对象聚焦到九十年代诗歌身上,这个样本的选取是否具有足够的理论反向承担?对此我表示怀疑。我们知道拉图尔的“行动主义”是建立在“实验室”即科研、生产体系基础之上的,他将实用主义和科技幻想(发明)的宏大叙事建立在有效性实践之上。斯洛特戴克承担他理论构建的批判支撑是海德格尔的“现世性”存在理论和德国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如果张伟栋按照他的理论构想,建立一种非线性、超时空的历史观和批判语境,把九十年代写作当作反向支点就太脆弱了。除非,这里的九十年代不单纯指中国的诗歌时代,而是全球的时代(斯洛特戴克的历史构境和批判话语正是建立在全球化视野之下的,因为这种构境建立的是一种“小说”式的历史图景,所以,它能担负起如斯洛特戴克自己所说的“夸大狂患者与冷静的结合为一体”的道说。)
按照张伟栋对“未来诗学”的解释,“未来诗学”针对的存在症候,即“当代诗歌处于困难和危机之中”。“基本的出发点是历史的与诗歌的双重危机。”“诗歌危机,一言以蔽之,就是诗歌失去了真理性,它只呈现某种片面的、主观的、个人化和文本化的特征。”尽管在诗学和美学上对颠覆对象指认尚不够清晰,即究竟现代和后现代谁和什么理论是造成“危机”的根源?提出对治性的理论是什么?这种理论是否具有方法的可操作性?是否对未来诗歌具有示范和开发作用?等等问题尚不够清晰,但这个框架和建树是值得期待的。对于这批年轻的学者来说,他们已经在理论和批判实践上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年龄上也正逢其时,且他们的学术视野已经和国际顶尖的思想家同步,所以,我对他们未来的理论成果充满期待!
2、对“未来诗歌”的质疑与追问
“对九十年代诗歌写作重估”引燃了对“未来诗歌”这一话题的讨论。就目前来看,关于这个话题引发的诗人普遍“众怒”远远大于对他们真实想法的倾听。从策略上说,他们这样的策划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就像斯洛特戴克当年对哈贝马斯的触怒所引起的舆论轰动效应一样。我不排除这种可能,即“未来诗歌”作为一个事件而不是单纯的理论,自打它一出现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是一个有组织性的行动。这种行动带有现代派思潮打出自己旗帜时的某些影子:团体、行动、纲领和批判对象构成一种出击阵营,然后密集出场。
最初的“投石”未必有多少合理性。比如针对张伟栋提出的:“诗歌危机,一言以蔽之,就是诗歌失去了真理性,它只呈现某种片面的、主观的、个人化和文本化的特征。”我在1月20日凌晨在微信里向一行发出了一连串尖锐的追问(给一行的追问不包括此文对真理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是在这篇文章首次提给张伟栋的):
你们说个人写作是无视真理的,这些判词的依据是什么?真理的定义是什么?是柏拉图的纯粹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是黑格尔的“只要是存在的就是符合理性的”?如果说个人写作是对宏大叙事政治化以及形式的模式化反驳的话,这种反驳未必是与宏大叙事不相关的。对此,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判词的出处,也要列举出考察了哪些诗歌样本?从宏大叙事的历史性视域来看,整个九十年代的诗人难道不是活过来的吗?不是与宏大的政治事件,社会形态变革,世界变迁,包括全球化运动,东欧剧变,海湾战争等等历史相伴生吗?非要歌颂现实(抒情与歌赞)才是历史感吗?海德格尔把个人的此在之延续(在路上)看作是撰写个人的史诗,难道中国诗人完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史诗”这一撰写了吗?在个人写作中无疑存在着某种反对和嘲弄宏大叙事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本身不就有宏大的回声和穿透力吗?比如尼采和兰波,这种个人的声音就没有历史感吗?甚至出离和纯粹就没有历史感吗?那,马拉美、瓦雷里也算不上有历史感了。甚至,陶渊明也是没有历史感的。如果你们认为是这样的,那你们认为好了,这些认为和诗人有什么关系?和诗歌写作有什么关系?可能只和学者的脑大有关系。
你们忽略1990年之后市场经济转型带给写作的大背景,来片面讨论个人写作,你们这种考察是有历史感的吗?你们一面无视历史,一面大谈历史,有什么资格?不管你们认为哪几个诗人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或者在后来的写作中与当初所坚持的先锋性写作精神相背叛,但几个诗人的症候可以代表整个九十年代吗?九十年代的写作是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写作作定性评价还为时尚早。
针对以上的追问,一行给了我非常耐心、客气而认真的回复。一行的回复让我看到这些学者的雄心和勇气,当代诗歌写作需要做迭代式创新,突破代际线性发展轨迹,放下已有的成果,构建一种全新的写作理论未必不是这个时代乃至未来诗歌需要做的紧迫事情。重估九十年代诗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引发的并非是单向度的重估,即一行说的站在当下写作角度的重估,还包括历史性的重估。前者的重估追问其局限性,后者重估则追问其有效价值。看似视角和取向不同,其实殊途同归。
3、对九十年代诗歌以及先锋性重估
说到对九十年代以来建立的个人写作的突围,张伟栋列举了北岛的文章。但北岛还具有写作的先锋性吗?我的意思是说创新与突围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具体写作的诗人身上,他们尽管没写文章说自己在突围,实际上每一首诗的创作都在谋求创新和自我超越。北岛就算写文章提出对九十年代诗歌的超越,他自身的表现和写作事实都已经证明处于完成状态。即奥登所说的那种从第一首诗开始就已确立了一生完成的写作。在我看来,北岛作为先锋诗歌的引领者地位已彻底崩塌了(当然,他作为历史性价值依旧重要。)。除此之外,先锋诗人犬儒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即一度作为先锋诗歌的领袖们,后来都选择了妥协,有的向资本妥协,有的向学院优渥的有尊严的生活妥协,有的向官方奖项妥协。他们的先锋性在与主流(政治或世俗)达成默契后,其价值得到了即时兑现,所以,这些人身上的先锋性都已经转化为红利。
先锋性根本特征就是它的价值永远是待估的,就像面对马拉美或安托南·阿尔托,他们身上坚定和锐利的东西什么时候去面对,都带给人激励和启发。先锋性的意义永远都是把人从某种蛰伏和自满的状态,带向对一成不变或某种牢固势力勇敢的冲破中。张伟栋也把马拉美和阿尔托当作重建诗歌写作的范例,在这一点上,我和张伟栋的认识是一致的。反观当下的写作,九十年代号称先锋的一些诗人纷纷收起了他们的锋芒。不过,九十年代孕育出来的诗人绝不都是类似这些今天看来名利双收的诗人,还有诸多富有开端创建,但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诗人。如果对九十年代诗人或诗歌以“个人写作”为罪名一棒子打死,那得制造多少冤假错案啊!
4、对当前诗歌写作的系统思考
我最近密集地写了一些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所指的。其中《谁不爱混乱,谁就不是一个创造者》是想说明诗人和知识(包括真理)的关系。大家都饱读诗书,每个诗人都有一个世界视域的书架,但为什么有创造力的诗人那么少?齐奥朗提醒我们,知识不是越多越好。
《当代诗歌呼唤极端》是针对现代性建设,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是未完成的,或者说是不彻底的。我们现代性未完成的标志就是从未诞生过类似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式具有开端性建立的重要诗人,以及与他们的身份相匹配的经典作品。我们的诗歌创作从形式到观念和行为,都需要完成对反叛和否定的一次极端触达,我们的诗歌文本、语言、思维和批判的张力都要得到充分展开与释放。
《当形式飞出大脑之外》是基于今天很多诗人还纠缠在形式、内容、语言等这类粗浅问题上而写的。这个问题自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演讲之后就已经解决了。他解决了作品与素材,作品与作者,作品之存在形态、作品之审美等一切对立问题,凡是还纠缠于这些问题的人,都是重复现代性初期,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诗歌理论的陈词滥调。
《当代诗歌实践之反思:仅有聪明是不够的——以欧阳江河为例》是针对当下一些功成名就的诗人,特别是以知识分子身份自居的诗人而写的。这些人的共性毛病就是说的比做得好。太会说了,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局限。他们对楷模的弘扬和树立,也使他们自己沾染了大师的傲慢气,让他们在大师,比如他们和策兰或米沃什之间出现面容上的混淆。
《当代诗歌实践之反思:九十年代诗歌的个性自治(一份提纲)》这篇文章是针对“未来诗学”倡导者对九十年代诗歌提出颠覆性审判而言的。对中国诗人而言,自古至今都不缺乏和政治的同谋和俯仰天地的视野,老子的《道德经》就是以道治国和俯仰天地的经典。斯洛特戴克引入中国的道家思想用来改造欧洲文化,并著《欧洲道家》(Eurotaoismus)一书。他和拉图尔共同谋求地球的安居性,这些理念是基于世界动荡起因都始于欧洲。他把现代性发端从哥白尼转变为麦哲伦也是看到欧洲的帝国侵略扩张才是现代性的根本动因。欧洲文化里欠缺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他们提出:“球体和网络都是为了反对同一类敌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古老而不断加深的鸿沟。”
我认为“个性自治”并不像张伟栋所说的造成人和群体的隔阂,相反,在集权政治和崇尚圣人哲学的中国文化里,恰是“个人自治”构建起文化和社会的脊梁。所以,张伟栋如果把去“个人写作”建立在对斯洛特戴克针对欧洲文化背景和全球化“帝国梦”的响应上,按照“人类公园原则”构建“共同体”,我要提醒的是注意中欧文化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作为诗人我们要不要做社会管控机制和伦理规训的推手?这一点需要深思。
还有一篇即《当代诗歌实践之反思:让诗歌独自存在——以潞潞《无题》为例》是针对那些真正有独创性的作品和不太会营销自己的老实巴交诗人做一点公允的呈现。我认为今天尚未得到呈现的诞生于九十年代的杰出诗歌一定不少。
5、对“未来诗学”的展望
未来诗歌怎么写,属于发生学,而不是设计院设计出来的规划图。我们正处在一个迅速变化的全新时代,诗人必然会说出属于他们内心的真话。值得警惕的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看到资本帝国不仅控制了我们的身体(城市空间)也控制了我们的精神(定制的或预制的娱乐平台)。人在资本帝国的控制中已经让自己同化为货币。同时,技术对人的规训已经细微到毛细血管里(福柯)。人的官能和精神都陷入现实和远程的双重控制之中。
从我们的现实处境来看,技术的进步对思想自由并未带来解放,恰好相反,技术反而成了加剧控制思想和言行的帮手。我们的生活也被“城市空间”所控制,普遍模式是建立斯洛特戴克式的“人类公园”和栅格式“居住社区”。维利里奥的“瞬间”在取消时间和空间之后为斩断“乡愁”和族群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凡是建立在线性时间上的记忆都面临集体遗忘。一切都建立在“平流”和“共时”空间之中。网络和虚拟空间,商务广场,乐园和电影院将人吸引到精心打造的空间内,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些满足转移了人对自由的本质需求,人心甘情愿接受资本的调动、控制,甚至奴役(斯洛特戴克)。消费和游戏也使人获得了自我消弭,他们不再追问我是谁?而是加入到普遍的消费潮流(大写的我或诸众)和游戏之中(快乐动员),在那里,贫富的差距并不造成个人的优越感和尊严的损伤。这种存在的瞬间化也不再追问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的差别,不是人分裂了,而是多重空间使人的瞬间安顿有了多样性(徳勒滋的根茎)。
同时,帝国从来都没有停止侵略和扩张霸权。技术和商业的统治图谋突破了国界的设防,渗透到世界各地。帝国的本质就是垄断和统治,所以,认为技术和商业不具有侵略性就大错特错了。那只变魔术的手,一边向你演示令你惊讶的梦幻故事,一边从你兜里掏走金钱,并为监控和操控你埋下隐线。这种经济掠夺、惩制和封锁,政治的远程渗透和操控,国家和个人核心机密的窃取,核心生产力的操控等无时不在帝国与帝国之间、帝国与诸众之间发生冲突和较量。斯洛特戴克所谓的“没有鸿沟的共同体”是一个新型乌托邦而已。
技术和商品具有致幻和麻醉性,技术和资本为什么在侵略中让人喜欢,不觉得是冒犯?这是因为技术和资本的出发点都源自人的欲望、梦想和烦恼。我们的确需要直面世界和未来的写作,但这个写作诗学的基点不应该仅仅建立在对九十年代诗歌的审判上,我们应该直面现在和未来开创一种全新的诗歌。特别是,我们要关注技术时代的特征以及他在哲学上和理性思想、艺术思想的深层呼应。科技走向超语言,即数字和图像(当然,数字乃至数字背后的转换也是语言的转换),就写作而言诗人无法不依赖语言。诗人的创造力受到科技的挑战。科技不断改变生活的方式乃至世界,诗人除了提供感觉和感受这些人文主义美学的东西,其它能提供的可供更新审美的东西很少。科技每天在追求日新日新日日新,诗歌反倒落得退守退守再退守的地步。
在语言上,只有极少数诗人具备创造力,绝大部分诗人在使用语言,即在修辞意义和语用学意义上使用语言。修辞受制于语法,语用受制于功效。诗人不能令语言新生也就不能令诗歌新生。
2024年1月22日

李德武,1963年生于辽宁彰武,1982——2002,居于哈尔滨。2002至今,迁居苏州。著有诗集《窒息的钟》《李德武诗文集上下册》,哲学诗学随笔集《挣脱时间的网——从芝诺的两个悖论说起》《在万米高空遇见庄子》,批评文集《气质•语言•风格:李德武诗画评论》等。主编民刊《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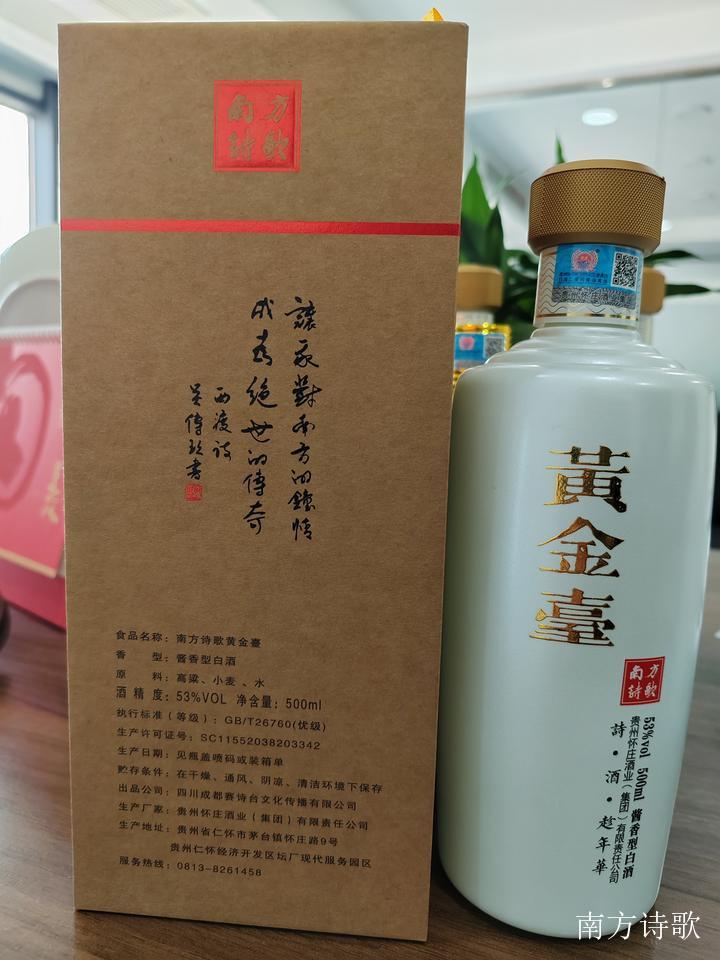

《南方诗歌》2021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2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4年一月目录
跨年专辑:39位诗人近作展(2023)
萧逸帆|中间没有什么(5首)
以琳|借你的胸膛穿过
吴悯|起身追赶影子
“南北诗人”|杜迎冬&文 若
“他山诗石”:董伯韬 译|遇见博纳富瓦
胡仁泽|屏住呼吸,风无声配合雨(5首)
王学|狭窄的四壁
张尧| 父亲:木匠、农民与其它(组诗)
廖俊|父亲(组诗)
金爽|生命的容器
子非花|遗失的图景
茶心|没有过多的虚词
码头水鬼|活着
骆家 译|我的头在地上翻滚.....
苍松|自由的宽度
心冘|万物生长的气息
刘恩崇|听见故乡喊痛的声音
岳秀红|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
木叶|硅基新年
许梦熊|鲸鱼在最后的悲鸣
“90℃诗点”:姚辉&张媛媛| 收藏天气的人
“香樟木诗学”:“中国当代诗歌呼唤绝对文本”全对话记录
云上研讨会|品读张新泉
“崖丽娟诗访谈”:蒋立波|诗的“辩难”与语言推进中“必要的阻滞”
张守刚|被故乡放牧
哑石|2023散诗30首
哈尔滨诗人桑克|写哈尔滨的诗
“他山诗石”:汪剑钊 译|阿赫玛杜琳娜诗选
张笃德|硝烟中变异的事物
王负剑|被往事紧攥
卢文悦|我们的神话
太阿|在我们的时代
万木灰|把骄傲的手伸入光明
兰童|杜家街村简史
杨森浩|矮山
叶朗|2024断章1号
绿子|爱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