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曲光辉 画
现代汉诗需要一种气度,在历史的节点上,同时看到一个种族在衰败与上升的那个转折时刻。诗人只有在历史节点上的痛苦经验,并在历史的痛点上获得超然的目光,才可能逆转时代的衰败,只有在逆转中形成的诗意姿态,才可能超越时代,获得诗意自身的真理性。
汉语诗歌的标志是面对历史时刻所形成的气度,而不是所谓的天赋与才华,既非出生与身份,也非精致与智慧,而是气度与神痴,才是汉语诗歌的至高准则。才华可能丧失,尤其对于早熟的古典汉语写作而言,大致在40岁之前,诗歌即已抵达极致,除非获得历史灾变的垂青,才有衰年之变法;出生可能高贵,但也可能在时代转折时刻,成为一种消极奢华的颓唐自残;甚至也不是智慧,中国文化的最高情志乃是神性的大痴,是由痴迷而生大智慧,超越人性的界限,只有大痴可以生成气度;气度乃是一种审时度势却又逆势而为的勇气,一种高华云端而不失悲悯的至深情志。
可惜进入现代性的汉诗写作,气度非凡之人稀罕之至。哪怕如同鲁迅先生之深沉苦辣者,也失之峻急尖刻,而早逝也导致先生没有抵达晚熟之从容。现代汉诗在语言上的双重翻译,翻译古典语文与西方大师,导致汉语的不成熟,现代汉诗写作必须摆脱文人习性的自傲,并抹平翻译皱褶的炫技,只有获得了持久写作的耐力与至深情志的陶冶后,才可能把汉语带往凝练的晚熟之境,走出中年写作的徘徊与声名的虚幻,而在回望中获得一种超然的气度。
气度,乃是面对大历史的一种目光,一种远眺与追忆的双重时间所赋予的深远目光。现代汉诗一直缺乏从历史的尺度衡量汉族命运的诗作,当然这是大历史的个体化尺度,并非某个阶层的利益或者某个朝代的兴衰,而是探究种族根性的大历史尺度。这把尺子,只有诗艺可以给予,因为历史的真理不在历史的特殊叙事,而是诗艺的普遍性,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就指明的尺度,历史的诗意高于历史的事实,因为只有诗意的觉悟与气象,才可以超越现实历史的铁则,超越时代的局限。
赵野最近几年的写作,随着他退居于云南苍山脚下,获得了一种自从1980年代罕有的旁观者的超然目光,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裹挟了中国人的生命经验,没有人能够从中摆脱出来,没有多少诗人形成一种反思的目光,更没有诗人从种族的根性与大历史的时间跨度,来面对我们当下的困境。而在西方现代性的大诗人那里,从艾略特的《荒原》到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再到布罗茨基的叙事诗等,诗意的敏锐触角刺痛了时代的节点,因而成为历史本身的一部分,但又具有超越历史的维度,因为诗意指向的是时间的情感尺度:“不洁的现实,雪花失忆的当下/唯有书能劈开内心冰封的大海。“因为这关涉到布罗茨基所言的“文明的教义”。
赵野的这首回应夏可君的长诗,不只是回应一本哲学著作《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而是回应一种古老文明的命运,中国及其汉族,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其种族的精神,其人性的命运,其可能给出的文明的教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中国现代诗至高的立意!中国伟大的诗歌传统,从来都以“立意”来判决高低,如同西方伟大的绘画从来都是对动机或主题(Motif)的回应,立意所体现出的气度,才是阅读的尺度。
1
这首《中国长城建造时》分为十四段,也是回应卡夫卡的“分段修建”的建构方法,但诗人的叙事在口气上一开始就模仿了卡夫卡,就是直接从卡夫卡开始,“我叫卡夫卡”,这也是回应夏可君的文本一开始就借卡夫卡之口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如此的直接称号,不同于张枣对于《卡夫卡致菲丽丝》的虚构改写,而是更为切中个体当下的命运,并且回到中国文化的历史场景,赵野与张枣因为卡夫卡而被关联起来,将构成未来汉语诗歌研究的“双翼”。赵野诗歌的气度与语调全然不同,他进入其间但也同时脱身而出,正是这种出入的转换姿态,让赵野最近的长诗写作具有了非凡的气度与格局。
是的,就是格局,面对历史的大势,只有看透其趋势者,才可能抓住局面,只有有此大局观者,才可能有着宏大的视野,由此杜甫在夔门写出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因为他看到了盛唐的不再,但又有着不舍的眷顾。只有如此的大格局才成就了杜甫的伟大,而不是之前的诗歌。
赵野最近几年的写作,以其形式的块状对称,如同汉字的方块字结构,大致是十行诗的格式也是汉语数字的整数,但其间蕴含奇妙转折的腰韵,并不刻意去压尾韵。以其叙事的从容,但并不追求1990以来中国诗歌的那种刻意的戏剧化,而是深入历史命运的事件,不是个体日常生活的细节,尤其活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用典”,但又使其成为一种高超的“化典”风格,一切都如此自然贴切,但又不失当下的活泼。
2
诗歌的第一段,开始于自我的卡夫卡化,而且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作者,这是双重的自我确认:失败者与失败的作家,中国诗人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失败的身份与命运,只有从失败与无力开始,我们的写作才可能开始,这是不可能的可能性,而卡夫卡从来都处于此写作多重不可能的煎熬经验中。但如此的相遇,乃是致命的亲吻,永远不可能抵达目的地,此不可能抵达也是长诗的题铭:从未抵达,却早已结束。如此的命运,既是生命个体的,也是诗歌写作的,其错位带来了双重的失败:一方面从未抵达,确实要去抵达;但另一方面,却早已结束,还没有开始抵达,还没有开始,就终结了,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如此的晚到,是中国文人的命运,是中国历史进入现代性的苦楚与苦涩:一切都发生过了,没有了秘密,对于文学不也是如此?西方大师的典范压得诗人们喘不过气来,一旦经过青春期的天才写作之后,深入时代的经验,因为缺乏反思尺度的诗意写作,只能是重复与模仿,以至于赵野甚至在1990年代末期,就干脆停止了写作,彻底融入这个无比翻腾的混杂现代性生活之中,但正是得益于此混杂经验的参与,以及多重经验,让他一旦重新开始写作,就有了质的飞跃。
就可以让声音开花,就具有了炼金术的手法,当然这是反讽,世界已经没有了秘密,而只有——“黄金巷垂泪”,这是赵野特有的组词法,黄金是炼金术提炼的丹药,而却只有狭窄的巷子在倾吐此丹药的流沙,但不是丹液,而是老泪,如此奇特的组合,混杂了不同跨度与不同感知的时空,既老辣又新鲜。
赵野的大历史视野,使他可以自由地穿越不同的时空加以混杂的组合。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巴别塔,当然这是与长城对立的空间模型,指向了人与神的关系,但在赵野笔下,上帝是坏脾气的,是喜欢开玩笑的诗意的上帝,但也带入了中国人对于苍茫世间的虚妄感。
但是,一切都要回到感性,回到生命的燃烧,但也是悖论式的,化为“布拉格的雨”,但依然还是再次的反转:根本上这个布拉格人要成为中国人,现在,就是“现在,我要回家”,当然,在我们的倾听中,这也是中国人,诗人赵野,要回家。
一个在家的中国人,却要再次回家,这是卡夫卡这个犹太人带来的教义,那文明的教义:我们的人性,即便在家,其实也是无家可归的,而必须持久地迂回,必须参照他者,如同在异地德国的张枣,也是试图通过卡夫卡的双肺寻找回家的路。
3
进入第二段,则是进入我们的民族,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是以中华民族的口气开始叙事的,他关心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如同犹太人喜欢走向高处——要建造塔而接近上帝或者成为上帝,而中国人则更为莫名其妙,就是要让同类诧异不已,以至于帝王只有成为诗人才体现出真正的才华与福气,或者,古老的咒语,幸福的与不幸的,还一直萦绕在辞藻的回纹之中,无法自拔,但也自得其乐。
从太肥硕的桃花,到烟尘里的谶言,从一个朝代的兴亡到浮华的月夜,中华民族,从帝王到诗人,都生活在一个把绿松石与荧惑星重叠的梦幻世界里,这是一个最为“文气”的民族,这是一个被各种“旋转的纹饰”所缠绕起来的文明类型,这是能够在即刻幻化与旷古闪电合谋的宫廷政变中,去改写旧文明的冒险传说,但总是要再次回到治乱的循环,最终导致的只是帝国记忆的崩溃,而需要唤醒活力时,又只能借助于外部游牧敌人的致命一击,庞大帝国的崩溃只有在一首哀悼的挽歌中,才可以在回味中获得唏嘘的宽慰。
4
这个古老的族类似乎不可能自觉的更新,而更为需要敌人的毒药与祝福的受虐。
诗歌进入第三段,再次回到万里长城,因为长城的伟大奇想就是来自于皇帝对于敌人的恐惧,恐惧放大了恐惧,帝王的恐惧则绝对放大了绝对的恐惧,帝国的博大来自于爬虫化为飞龙的幻化,但恐惧也在幻化中深入骨髓,乃至于中国梦其实是云烟炼就的丹药。中华民族也许比其它所有民族,都生活在一种放大的恐惧中,从对于天上的飞龙,到地上的走兽老虎,到水中的鳄鱼,乃至于地上的爬虫,还有梦中各种怪物的交叠变幻,中华民族乐此不疲地以这些妖魔鬼怪,来滋养自己梦中的惊恐,以惊恐繁殖惊恐,因此,长城其实就是一种面对惊恐时的全民参与的伟大游戏,纯粹而极致。
这才有全民对于建筑,尤其是筑墙术的爱好,赵野的叙事跟随卡夫卡小说的步伐,随意加以点染,或者回应夏可君哲学的思辨,加以诗意的夸张,这才有对于形式主义之炫目高度的诊断,炫目的高度也是恐惧的宽度,才有万里长城的伟业,才有体系化的艺术,才有整体总动员的统治术。
甚至才有日日维新的干劲,搂起袖子加油干的口号,而且,此“分段修建”的奇特组合方法,还一举兼顾了北方的坏天气与人民的老困顿,尤其是那令人缠绵悱恻的文学细节,我们这个民族,只有有着文学的细节,只要细节足够的文学化,就比如文革,全民大炼钢铁,哪怕吃不饱也要把破铜烂铁锤炼成可以飞上天的卫星,因为那卫星乃是放大的希望,是中国龙的现代转型,也是针对西方或者苏联原子弹的恐惧。只要有着伟大的目标与文学的细节,我们这个民族可以想象出任何的伟大事业,那所谓“最高的精神性”。
也许,只有诗意的想象才可能洞穿此民族性格的诗意,但这是反讽与悖谬的民族根性,是无法自拔的根性,这是苦涩的根性,乃至于越来越虚无化的根性。
5
进入第四段,诗意的目光进入到帝国统治的秘密,那些隐喻,仿佛的假巧妙,一切都是花拳绣腿的花招,一切都是装样子的花招,是成功的花招或者失败的花招,卡夫卡发现这来自于我们的人民在性种上的轻率,诗人赵野甚至发现这轻率来自于:深谙落花流水的意趣!是的,这是绝对的洞见,落花之美与流水之态,但二者都沦落为无情的下降态,却独独被中国人青睐有加,因为此“本质的轻率”——这被卡夫卡所洞见的中国性,却是中国人自己一直没有觉察到的,这是异族目光的毒辣。因为此轻率的本性,我们也习惯了忍耐,逆天地顺受,在笼子里也其乐融融。
诗人说,我们只能在能指里活着,只是在符号繁殖的幻象中幻想,只有当灾变来临才可能撕碎所指,把想当然的快乐击碎。但是还有制度,悠久的制度胜过疲惫的人心,轻率的族类只有依靠强大专横的制度才可能被规训,如同民众对于食盐的需要,集体的意志从来强大,如同我们前面指出的大炼钢铁,历史在重复中形成民族性格的单调复数。
我们的民族总是复数,多民族的帝国从来都是复数,这既是数量上的多数,也是技术复制的数字,我们的块量化思维,我们文学轻率的意趣,文武都合一了,因为一切都成为了装样子的套路。
借助于诗人的目光,我们可以对于汉民族的性格,对于历史的深渊,有着更为直接的经验。这个民族不是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深渊,但分段修建的套路一旦确定,裂隙就无处不在,我们的民族生活在一次又一次的被裂隙穿越而来的敌人那蛮横的冲杀,帝国的颜面尽管不容侵侮,但来自于黑暗中的势力,也“俄顷黑暗中隐匿”,这是诗人了不起的洞见,来自于黑暗的再次归于黑暗,但从来没有得到过清晰的辨认,因为我们并不关心它们。我们仅仅沉迷于自身的款式,一切仅仅是老款式中的新装而已,我们仅仅沉迷于虚无的造作游戏,那恐惧滋生恐惧的游戏,万里长城不过就是此恐惧游戏最好的玩物。
因此,这是卡夫卡与本雅明,还有被夏可君强化的中国智慧及其可直观性:认认真真做某事同时却又两手空空。
6
这是一种智慧,此无用的智慧,保持自己的无用性,因此结果似乎不重要。在这首长诗中,赵野大量地引用已有的习语,赵野的晚近风格并不追求语言的新奇与修辞的密度,而是松弛中的张力,看似很多惯常的习语,乃至于套话,但都被置于一种重复的戏谑之中,一种反讽的机智被悄然融入到提炼历史的深度之中,这是场景与智慧的凝练抽取,历史与细节的奇妙连接,是一种混杂的诗意智慧,它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单纯用典,也不是西方纯诗的密度意象,而是一种夹叙夹议的诗意叙事,其宏大的视野就是为了在历史的时空与人性的晦暗之夹缝中,寻找到撕裂的地带,感知生命的苦涩。
因此,从《道德经》圣人们的教诲,到东方哲学的大海,一切都被归于为无用的缥缈,但此缥缈似乎又与体制完好地融合,以至于让空间锁死了时间,没有脑袋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往上飞跃,我们体制的宫殿却让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中华民族的时间性乃是被彻底天地人三位一体固化的结构,这在汉代的《月令》图示中彻底奠基下来,就是人类按照时令节气来劳动,而统治的宫殿,无论是其形制,还是其结构,无论是皇恩浩荡还是远方的叛乱,其实都是对称的,都是回旋的,都是回环的,都是套路,直到套路成为了铁链。
但是诗人指出,这是看不见的铁链,因此,就没有什么可以砸碎的,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摆脱的,也就不需要解放。反而,任何试图挣脱锁链的那种努力,显得无聊而空洞。但是,锻造一只看不见的锁链,那万里的长城,却是帝王与民众,心照不宣的秘密,并且一起合力持久地去打造它:好一个认认真真做某事,同时却空无所成的,无用之高超的秘密!
7
进入第七段,诗人扩展开来,继续冥想天下的历史逻辑,夜晚青灯的阅读中,点燃的其实是血滴与万古愁,哪里有着统治的合法性?一代代的奔流中,帝王的力量与北斗星的气运在暗中较量,不死的意志乃是执念,只是要把死亡填满丛山峻岭,昭昭的大赋与永无止境的劳作,只是让勤劳的人民一直抱有其“菁菁孩子气”,诗人的概括总是准确生动,而且还有诗意的典雅,这是永远无法长大的诗意的民族。
对于诗人,对于卡夫卡式的民族,诗人的本性是与民族的性格同调的,这就是痛苦的根源,没有哪一个民族比汉民族更为具有诗意的品性:孩子气,轻率,着迷于无常的幻象,文辞韵律中的回环吟哦,喜好无常之物的空及其荣誉的盛大。
但如此诗意的政治想象,把阴谋与阳谋统合起来,也就锁定了想象力的终点,一切就都成为套话,文学艺术也被程式化,哪怕是鹤唳的目光,生生世世,也被长城环顾而无法超出。
有着终结的时日吗?有着走出此困局的智慧吗?长城会倒下?各种传说兴起,最为著名的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但只有石头里的亡灵醒来,才可能把个体性的悲剧转换为公共性的抗争。但显然帝国从来没有如此的时刻,我们依然活在一首革命的歌曲,血肉铸成的长城,依然还是形象的工程。
古旧的叙事到新的形象叙事,历史再次进入轮回的复制。就如同卡夫卡似乎已经提前就把布拉格的雨水看做纳粹的枪林弹雨,因此,伟大的万里长城,在异域的目光中,怎么看都堪比一次玩笑,是的,是无法升级的玩笑。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玩笑有着严肃的态度,或者说,你分不清这个民族对于玩笑,到底是严肃的呢还是玩笑的呢,这是卡夫卡试图要破解的吊诡:对于一个领导的指令,或者对于长城修建的指令,任何正确的理解与错误的理解,都是合理的。
文学与诗歌的出路何在?如果诗歌不是解咒的艺术,哪里还有诗歌存在的合法性?如果这个民族持久地生活在咒语之中,甚至把咒语与歌谣,还有测算命运的卦爻,都巧妙地叠加起来,成为了一种长城幡旗的最美纹饰,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那么,“他妈的”诅咒也可以入诗,那么,世界再无恒义。这是第九段,诗人无法忍受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
但汉语的本性就在于混淆视听,就可以掩耳盗铃,即指鹿为马,看似长城在护卫着它的民众,以此消解民众与帝国的紧张关系,但一切都成为了谎言,典籍不再有真理的言说,一切就成为了往昔的幽灵,而长城也就成为了我们的身份,乃至于宿命。
8
卡夫卡在《中国长城建造时》写道:“村口的小圆柱上蟠曲着一条圣龙,自古以来就正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这样的村口在当今中国依然无处不在,甚至以国族主义的名义,火焰喷得越来越高,这个民族并没有在灾难的火焰中让精神得到痛苦的燃烧,而获得洞观历史的火眼金睛,反而一再陷入火龙的自我焚毁的幼稚激情。
诗意的现代性,汉语诗歌写作的责任,就是要试图破解此宿命?如同卡夫卡在小小的布拉格要面对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灾难,但是,任何试图寻找归属的意念,可能都是一只笼子寻找一只鸟,人世间并没有所谓的逃逸之线,一切都处于越来越精致的笼子包围中。
而在中国的智慧中,则是:“虚无走向我”,诗人赵野晚近的诗歌写作姿态不同于同时代的诗人,就是试图以历史的大尺度来面对诗歌中的虚无主义,现代汉语诗歌基本上是各种虚无主义游戏姿态的一次次粉墨登场,无论是有意的下半身写作,还是无意识的修辞游戏,因此如何面对虚无呢?需要另一种的信仰?
进入第十段之后,诗人回到了卡夫卡的民族性,蝴蝶与飞鸟,桃花源与应许地,都是死结,进入现代性,面对一切都被虚无化,哪里还有不可摧毁之物?只有肉身配得完美的幸福,哪怕是“古典密意熠熠”——赵野的叠词运用深得古典之妙,但“刀锋两边展开”——人性依旧生活在刀刃上,因此,拯救的弥赛亚也许根本就来不了,或者说,弥赛亚也无用了,因为他也永远在路上,从未抵达。
结局是死局还是僵局?哪里还有所谓的胜负手?一切的投注其实都是虚掷的数字游戏,如同死亡的点数。回到族长的开端,回到诗意的高台,无论是信仰的牺牲献祭还是悲风嚎歌,都是虚妄。
9
诗人还是不得不独自面对历史的虚无时刻,在来回的审视中,历史的哪个时刻曾经得到过救赎?从骑马到乘船,“帝国的前世今生犹如海市蜃楼”,如何可能有着穿墙术?在哪里发现解咒的密码?如果捕鼠器依然无处不在,布拉格的雨依然还在燃烧,那么,一个回到中国的中国人,经过卡夫卡的目光洗礼的中国诗人或者文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迈出自己的双脚?这是再次接受一个来自于中国却被中国遗忘的教义:变小,并且消失于自己的作品中,才可能练就一身穿墙术,这是要决然地走向空无,要相信:“无中生出有,拯救降临”。这是第十一段的教义。
赵野的这些诗作,其实更为让我想起布莱希特的那些教育诗,尤其在1938年左右,当纳粹把帝国抓在手上后,布莱希特,还有本雅明,不得不开始逃亡,在逃亡的途中,布莱希特写出了致敬老子《道德经》的诗歌,其中谈到了老子相遇之人的友爱,谈到了柔软胜过刚强的智慧,更为奇妙的则是,在1945年战败之后,海德格尔也开始在《黑皮书》中隐秘改写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智慧,开始新的转向,而在本雅明的解读中,甚至此柔弱的智慧与弥赛亚的救赎教义相当,如同布莱希特对于《道德经》改写的轻盈与从容,抵消了逃亡的恐惧,抵御了纳粹暴力的伤害。
当我阅读赵野的这首诗歌,似乎我们两个人,也如同布莱希特与本雅明,在一边收听希特勒的电台广播,一边下着国际象棋,当然,也一边在阅读卡夫卡,讨论卡夫卡与道德经的关系,讨论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这是一种内心逃亡的文学写作,其中有着对于政治的明确态度,有着对于文学本身异域化的接纳,有着面对灾难的镇定,我们依然还在逃亡的途中,我们从未走出帝国的宫殿,我们笨拙的逃亡依然还回到了帝国的掌纹星象图中。
在一个混杂现代性的社会里,单纯的前现代、现代或后现代,可能都有问题,会流于简单、过气或浅薄,当下的中国诗歌,也许恰恰应该具备这种“混杂现代性”的多重气质,只是古典的高贵容易虚假自欺,只是现代风格又会过于落到个体化小我的圈套抒情,后现代式喻象的国际化可能过于炫目而丧失真实性,需要把三重时间要素,以个体化的悲剧感受与悲悯的剩余情怀重新啮合起来。我们在赵野的诗歌之中能感受到前现代的单纯与高贵,现代的深邃与形式主义,以及后现代的无所用心与无所顾忌,诗人要有一种能力,用语言把它们统摄在一起。只要语言成立,意义自会显现,一旦凝练的提纯形成,语词的结晶就会熠熠生辉。
如此多重混杂的身份,在诗人之前的《读(己亥杂诗)并致余世存》中的那个“我”,就混杂了龚自珍、余世存及他自己的多重身份。这是赵野借鉴了当代艺术的拼贴和挪用,以互文的文学方式,从叙事的多维性,从作者的身份,思想,话语各方面,融进了卡夫卡,夏可君(夏可君的书),他自己的当下情感,形成了文本之多重的赋格对应,这也是与诗人古典音乐的深厚修养相关。诗歌中的“我”既有卡夫卡的维度,也有诗人的维度,所以可以很自然的把圣经、犹太人的命运,和中国的秦制、汉族的命运混杂在一起。这种方法,可以让文本更复杂、丰富,呈现出很多个层面,如此互文性的写作,又带有反讽的含蓄语调,耐人寻味。
如此的反讽式写作,哪怕是多余的写作,如同夏可君书写卡夫卡是多余的附属物,赵野回应夏可君的写作也是多余的诗意评点,夏可君再次回应赵野的击打也是多余的,但如此多余的重复中,诗意的真理得到了凝练的提纯,汉语诗歌的气度就在于承认自身“多余性”的同时,还让真理的传言获得更为精准的传递。
10
这也就形成了诗人赵野的写作态度,在第十二段,诗人明确回到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在持久的迂回后,如同现代汉语诗歌经过西方翻译体的持久迂回后,赵野回到了汉语自身的民族性与历史的命运,不会在巴赫的赋格中走进毒气室,不会像策兰的写作为大屠杀领份罪,而让词语负疚。对于中国诗人赵野而言,
我或许只是一个平面,生活在
一种非生活中,素食朝向南方
梅花与菊花自律,冬夏读诗书
春秋习礼乐,待屏风幻化山水
和美人,我将渐渐隐去,直到
来自德国的大师把这一切摧毁
——这是诗人的谦卑,只是愿意持守在一个素朴的平面上,甚至活在一种非生活之中,但这是前维度的自然世界,以梅花与菊花自律,待屏风幻化山水,这是回到汉语诗歌自身的生存美学,这是接续古典文人的审美生存风格,在自然中重建诗意的准则,而不必害怕被来自德国大师的哲学观念所摧毁。
当然,铁的栅栏,历史记忆的枷锁无处不在,诗人似乎与卡夫卡成为了一体,如果“活着并承担人类的苦——比杀戮更令我害怕”,那么,所谓的路也不过是踌躇,诗人改写着卡夫卡的箴言,如何化解此苦楚的命运?哪怕——“卮言似泉水,空气颤栗”,但也可能无法避免建立与坍塌同时的命运,那么,有着解决的方案吗?
诗人坦言:
但建立与坍塌间,我从没对过
每次言之灼灼,却总含混不清
——这是汉语的宿命,我们依然活在这种闪烁其词的语言之中。
也写过《中国长城》的另一个德语犹太作家克劳斯也将自己置身于中国式的生命经验之中,可能也影响了后来的卡夫卡,他称赞中国人是存在蜗居中的空间艺术家,但其实这是另一种的作茧自缚,是在自残中包裹自身的伤口,以至于遗忘了痛苦的独特“技艺”。对于语词和建筑有着思考的克劳斯,多次将德语比作房屋, 甚至比作语言的避难所,克劳斯试图在中国人身上寻找一种已失落的犹太理想,一种语言力量的纪念碑。而在赵野的诗歌中,诗歌的严整气度,带来了一种语言纪念碑的结实感,让诗歌成为苦闷心灵的避难所。
11
另一个犹太人卡内蒂 (Elias Canetti) 在分析克劳斯的散文写作时,认为其缺少一个总览全局的结构原则,而不得不在单个句子中去穷尽那种心血来潮般的建造欲望,而克劳斯的忧虑在于,如果每个句子都是无懈可击的, 空白、缝隙乃至错误的标点都不能存在———那么,这就一句句、一块块地筑成了一条万里的中国长城。卡内蒂由此得出结论:“长城的每一处都建得一样好, 在哪都不会认错它的特点, 然而这条长城围绕的真正是什么, 却没人知道。这座城墙后并没有帝国存在, 长城本身就是帝国。帝国所有曾存在过的精血, 统统都流进了这座建筑之中。”
是的,如此正确的长城却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它就是帝国本身,因为这是纯粹的建筑,宏大的物自体,此物自体却又是一块块具体的建筑石材,而卡内蒂继认为克劳斯所用的这些方石就是“审判”,它将周遭一切都化作了“荒漠”。对于中国历史,此审判与荒漠却陷入了恶性的循环,只是在帝国衰败之际显现出某种末世论的残局,但最终还是会再次回到长城的围困之中,陷入所谓的内循环。
最后一段,诗人赵野指明了此恶性循环之为不洁的现实:
雪花失忆的当下
唯有书能劈开内心冰封的大海
——这是诗人最后的信念:即便是失忆的雪花,落下来无常地涂抹世界的痕迹,也能够如同书籍——劈开内心冰封的大海,我们这个民族的诗人,我们这一代人,乃是最后相信典书的一代,只要我们还爱着典籍,还爱着典书,还在书写,如同布莱希特与本雅明,如同我们之间的相互书写,那么,即便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一只所谓的卡夫卡鸟,翅膀萎缩,仿佛死亡的剩余物,而且面对着每个街角都充满的敌意毒箭,而且还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像中国长城那样成为镜子,那么,在诗人决然的姿态中,再次重复着卡夫卡的:
没有真理性的呓语,如烧掉我
——但这句没有真理性的呓语,这最后剩余的词汇,这如同余灰一般的多余词汇,在一个已无真理的世界,温暖阅读者的目光,但这余灰也是那不可摧毁的剩余物,保留着汉语最后的诗意。
中国的万里长城,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诗人们的一行行诗句,这是诗歌的置换术,它需要足够的数量与长度,才可能实现此替换,才可能解除这个族类骨子里的诅咒,让一个诗意的民族重新出生。
因为这最后的挽歌,也是献给未来的祖国颂诗,民族命运的史诗写作,如同荷尔德林要苦心实现的回转,诗人赵野为汉族的宿命与帝国的记忆,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所写的这最后的挽歌,不走向悲剧的哀歌,乃是以枯淡的超然气度,消解这个民族淤积的无尽苦涩,而形成高超的诗意。

夏可君,哲学家,评论家与策展人。曾留学于德国弗莱堡大学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述十余部,从“无用”出发,撰有《虚薄:杜尚与庄子》,《庖丁解牛》,《姿势的诗学》,《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烟影与面纱》,《无用的神学》,以及英文著作Chinese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Unthought of Empty。
附:
中国长城建造时
赵野
从未抵达,早已结束
——夏可君《无用的文学》
一
我叫卡夫卡,一个失败的作者
写下的亲吻永远到不了目的地
声音开花,十七世纪的炼金士
像说着什么秘密,黄金巷垂泪
太初,巴比塔倒塌了,因为人
竟想比肩神,欲打开无穷愿景
旧约开始流亡,成上帝坏脾气
或遗弃于苍茫世间的虚无笑话
燃烧吧,布拉格的雨,根本上
我是个中国人,现在我要回家
二
我们这个民族,呵呵,总能够
发明一些高蹈事,让同类诧异
帝六年,桃花太肥硕,游吟的
谶言满街烟尘,说亡秦者胡也
随后浮华的月夜里,鹤琢走了
屋檐上的绿松石,荧惑星坠落
风中早朝,嗟哦的圣旨带寒意
今上放出最大招,旷古的闪电
改写旧文明,让单于记忆崩溃
帝国的活力正好需要新的敌人
三
其实很早,就有一种时尚兴起
全民研究建筑和砌墙术,风以
动之,教以化之,泱泱帝国的
形式主义发展到了炫目的高度
结构都得到解析,要努力成为
体系化艺术,文官们日日唯新
比如,分段而建,一举兼顾了
北方坏天气与人民老困境,噫
每天有细节,与伟大目标关联
修长城就获得了最高的精神性
四
治大国若烹小鲜,古老的隐喻
暗示了帝国统治的秘密,仿佛
魔术师玩弄假巧妙,深谙落花
流水的意趣,商君书说,人民
本复数,绝不会和岁月过不去
彼本质轻率,靠惯性逆天忍耐
在能指里活着,当风撕碎所指
洪水淹没想当然的快乐,然后
制度收拢他们如盐,有朝一日
集体爆发,移山填海大炼钢铁
五
深渊有不同表达,分段而建的
教条,万古星光下,处处裂隙
王气歧路失血,匈奴人十二月
播种春意,觊觎之马踏破修辞
他们风一样游牧着一千座高原
从黑暗中来,俄顷黑暗中隐匿
帝国颜面不容侵侮,依旧一身
老款式的新装,屹立天下中心
我们民族落下过诅咒,它总是
认认真真做好多事却两手空空
六
结果重要吗?圣人说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天地犹橐籥乎
东方哲学是一片大海,越读越
缥缈,让最好的头脑无所适从
我们体制完美,空间锁死时间
旗杆一直等待山水迢递的消息
宫殿血缘般可靠,浩荡的皇恩
紧紧抓住我,叛乱在远方绝望
如果铁链看不见,就没有砸碎
嗟乎,永恒远离才会无限靠近
七
但是天下由来不固久,青灯里
编年史骇然滴血,点燃万古愁
打江山坐江山的合法性,如何
一代代奔流,帝力要气冲北斗
长风黩武,不死的执念把意志
横陈丛山峻岭,写就昭昭大赋
永无止境的劳作,让人民保有
菁菁孩子气,相信一切皆可能
阳谋锁定想象力的终点,目光
鹤唳,生生世世,长城环顾下
八
长城终局暧昧,传说被孟姜女
哭倒了,她的丈夫劳动时死去
天知道每一块石头里,是否都
埋着一个亡灵,白发夜夜振戈
私下悲剧触发公共性,是血肉
建造了形象工程,遂成新叙事
此刻,布拉格的雨,恍惚纳粹
长城怎么看都堪比一次元玩笑
真相瓦解所有辩证法,留一堆
过气的文献,任考据皓首穷经
九
咒语,歌曲,卦爻,我想知道
他妈的长城啊将把我带向何方
以今非古,铸就当朝意识形态
万事即兴发生,世界再无恒义
长城护卫着每个人,消解彼与
帝国的紧张关系,举世同凉热
吾皇指鹿为马,骑手全部消失
典籍不再有鹿和它的全部言说
那谁,我们无非往昔幽灵,而
长城就是我们的身份,以及命
十
哦,笼子走向鸟,虚无走向我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蝴蝶栩栩
如果笼子变成鸟,我变成虚无
桃花源,或应许地,都是死结
心中有不可摧毁之物,但弃绝
追求,肉身只配得这完美幸福
古典密意熠熠,刀锋两边展开
弥赛亚永远在路上,从未抵达
结局早注定,谁还投下胜负手
我的亚伯拉罕,我的高台悲风
十一
匈奴人不骑马了,后来改乘船
万世招魂幡,令水波穿上制服
帝国的前世今生犹如海市蜃楼
城墙跃跃解咒,谕令迟迟未发
燃烧吧,布拉格的雨,他们说
捕鼠器无处不在,我还是愿意
做一个中国人,我站立的土地
不超出双脚,变得小,更小再
练就一身穿墙术,当我们走向
空无,无中生出有,拯救降临
十二
我想,如是中国人,我将不会
在巴赫的赋格中,走进毒气室
也不会像策兰,为奥斯维辛后
继续写诗领份罪,让词语负疚
我或许只是一个平面,生活在
一种非生活中,素食朝向南方
梅花与菊花自律,冬夏读诗书
春秋习礼乐,待屏风幻化山水
和美人,我将渐渐隐去,直到
来自德国的大师把这一切摧毁
十三
失眠和头疼折磨我,我的身上
背着铁栅栏,而上帝总在别处
为什么我不是长城颧骨上那个
守夜人,活着并承担人类的苦
比杀戮更令我害怕,唉,原来
我们称之为路的,不过是踌躇
彼时,卮言似泉水,空气颤栗
我的噩梦或带来不可能的杰作
但建立与坍塌间,我从没对过
每次言之灼灼,却总含混不清
十四
不洁的现实,雪花失忆的当下
唯有书能劈开内心冰封的大海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一只
卡夫卡鸟,翅膀萎缩,飘忽在
永远陌生的城市,仿佛死亡的
剩余物,每个街角都充满敌意
如果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像
中国长城那样成为镜子,那么
勃罗德,或许你应该烧掉这些
没有真理性的呓语,如烧掉我
注:夏可君博士杰出的著作《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启发了此次写作。我努力让此书的笔意与卡夫卡的言辞,产生美妙的互文意趣。此诗开端“我叫卡夫卡”和结尾“烧掉我”,出自张枣的十四行组诗《卡夫卡致菲利丝》,仅以此向温馨的故友致敬。此诗的写作也让我相信:当下诗歌要进入更深邃的现实,卡夫卡是一个起点。
赠夏可君,2021

赵野 当代诗人,1964年出生于四川兴文古宋,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出版有诗集《逝者如斯》(作家出版社,2003),德中双语诗集《归园Zuruck in die Garten》(Edition Thanhauser,Austry,2012),《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赵野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2017),《剩山—赵野诗选》(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2023)。现居大理和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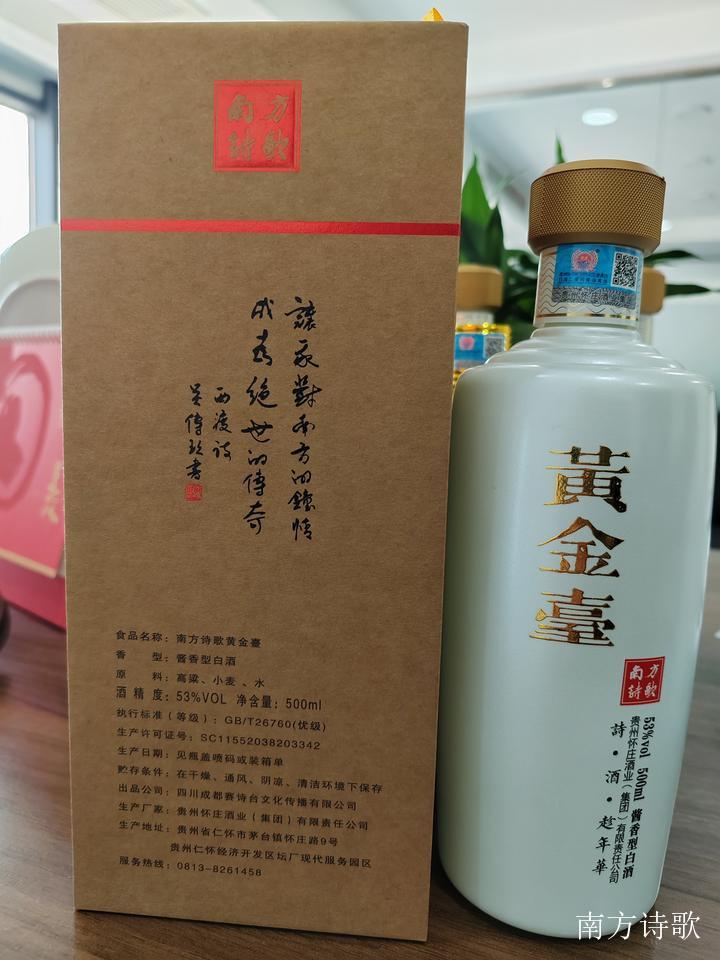

《南方诗歌》2023年12月目录
“未来诗学“:冯强|”及物性/不及物性”:一个回溯到“兴”的诗学讨论
“90℃诗点”:陈陈相因&张媛媛| “写美的人与审美的人”:诗的双重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