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寅九 画
崖丽娟: 王寅老师,早就计划要访谈您,第一阶段访谈接近尾声才如愿以偿。大约有两年时间,我经常参加您策划的“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我的直观感受是,这个活动虽然立足上海,但是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专业水准高,赢得良好的口碑,很多诗人都十分乐意参与,这的确是引进和推荐国内外优秀诗歌的一种很好形式。从2012年开始,您邀请的诗人坚持“国内顶尖、国际一流”,树立了品牌。我系列访谈的多位诗人就曾是“诗歌来到美术馆”嘉宾,所以也要感谢您给我的帮助。在此,先请您介绍创办活动的初衷以及运作经验,后续有什么考虑?
王寅:丽娟你好!我记得自从民生美术馆搬到汶水路以后,你就开始一期不拉地参加。你对活动的及时反馈和建议,给了我很好的启发。
“诗歌来到美术馆”是一个单纯、朴素、安静、生长于民间的小项目,从2012年10月21日第一期黄灿然《奇迹集》朗读交流会,至2021年9月12日方商羊诗歌朗读交流会为止,共 举办了77期,邀请了74位海内外诗人。 最初是民生现代美术馆热爱诗歌的朋友邀请,才有了在美术馆做诗歌活动的可能。我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活动的形式和基调,由对话、诗歌朗读、观众互动三个基本环节组成。活动每个月一次,每次只邀请一位诗人,选择的标准是国内顶尖,国际一流。诗人和主持人进行深入对谈,充分展示诗人的生活和创作,特别是每位诗人极具个人化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包括他的困惑和矛盾,同时也让观众和诗人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每一场活动,观众都会免费领取一本当天活动的场刊,场刊印有诗人自选的20首左右的短诗,如果是外国诗人,则是中外对照的双语版本,诗人和听众可以对照场刊朗诵和聆听。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次是阿多尼斯专场,共有700多人,美术馆特地开放了最大的展厅作为活动现场,平时的活动最少也有一两百人。由于是在美术馆举办的诗歌活动,在活动的现场,也配合举办过诗人的小型摄影展和画展,如阿多尼斯画展和翟永明的摄影展。
我后来才知道,“诗歌来到美术馆”是很多诗人诗歌生涯的第一次个人诗歌朗读会。到目前为止已经邀请到21个国家或地区的诗人,涉及英、法、德、意、日、西、葡、波兰、马其顿等十余种语言,有不少诗人的作品是因为“诗歌来到美术馆”,才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英美诗歌因为被翻译得较多,更为中国读者熟悉,但英美诗歌不是世界诗歌版图的全部,还有很多小语种的优秀诗人因为语言的关系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所以,我在邀请诗人时,有意识地向小语种诗歌倾斜,这样才能让中国读者有机会更全面地了解英语世界之外的诗歌动态。必须一提的是,长期担任主持的诗人胡续东和担任现场口译的金雯教授,他们的出色表现和发挥给活动增色不少,很多观众就是冲着他们来参加“诗歌来到美术馆”的。
“诗歌来到美术馆”当年启动时,有人义正词严地怒斥:看看诗歌现在有多堕落,已经到了去巴结美术馆的地步。十多年过去了,美术馆早已不是只有单一的展览空间,而是功能多样的复合体,人们可以在美术馆表演舞蹈和话剧、开音乐会,看电影,甚至用餐、开派对。诗歌应该走进更多的空间,去和其他艺术相结合,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和可能性。“诗歌来到美术馆”的目的是让观众感受到诗歌的魅力,他未必成为诗人,但他会因此影响到他周围的人、他的孩子读诗、写诗,这就是成功了。
一件事要做成,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另外还需要一点点运气。2020年,我邀请了七位外国诗人(他们分别是七种语言的代表了),他们的诗也已经委托翻译家翻译完成,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们未能如愿来到上海。很多朋友问“诗歌来到美术馆”什么时候恢复?由于民生美术馆搬迁后还在装修,活动处于暂停状态。再等等吧。即使因为各种无法控制的原因,“诗歌来到美术馆”最终停办了,也没有关系,只要诗歌存在,我相信会有其他的诗歌活动出现。现在面向社会的高质量的诗歌活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多一些,再多一些。
崖丽娟:这些年您经常游历国外,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也邀请不少国外优秀诗人来到上海做诗歌分享,注重于中外诗歌交流。您的作品被译成16种文字,先后出版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斯洛文尼亚语等各语种诗集,国际视野对您的创作带来什么影响?除了策划美术馆诗歌活动,您还尝试制作诗歌音乐剧场,二者之间的衔接点在哪里?
王寅:我对远方和异域的想象浓厚兴趣由来已久,也因此写了很多异国题材的诗,最具代表性的诗是1983年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这首诗的长标题是受到我喜爱的诗人詹姆斯·赖特和罗伯特·勃莱的影响,而他们的长标题则是从唐诗中得到的灵感。1990年代初,诗人鲁萌从布拉格给我寄来明信片,提到了这首诗,我至今还珍藏着那张薄薄的纸片。后来,很多朋友给我发来信息,告诉我他们正在布拉格旅行,而我自己直到很多年后才去了布拉格。
我的诗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得益于各国的翻译家朋友,他们中有些是我合作多年的老朋友,我和我的英语译者凌靜怡(Andrea Lingenfelter)已经认识十七年,我和我的法语译者尚德兰(Chantal Chen-Andro )认识更早,已经将近20年了,彼此十分默契。更多的翻译家至今尚未谋面。乔治·斯坦纳说过:“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确实如此,当代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广泛而且深入,相比之下,外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少了很多,外国翻译家们的辛勤工作对于国际间双向的文学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策划“诗歌来到美术馆”和制作诗歌音乐剧场,是我的兴趣所在,诗歌音乐剧场更是我多次参加国际文学节和诗歌节之后心生羡慕、受到启发的直接结果。举几个例子,2005年,我去参加波兰卡托维茨艺术节,在一座中世纪的剧院里,戴墨镜的诗人坐在高脚凳上,在乐队的伴奏下,用连贯的爆破音朗读诗作,与其说是读诗,不如说是在演摇滚。2015年的挪威文学节,挪威老诗人扬·埃里克·沃勒(Jan Erik Vold)的新诗集朗读会在音乐厅里举行,600个座位全部坐满,室内乐队伴奏,演奏的曲子都是作曲家为这场演出专门创作的,可以单独演出的作品。2018年,斯洛文尼亚诗与酒的诗歌节,在始建于12世纪的普图伊城堡里,德国诗人米盖尔·克鲁格(Michael Krüger)的钢琴朗读会上,诗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女钢琴家演奏德国作曲家曼弗雷德·特罗亚恩(Manfred Trojahn)根据诗人的诗创作的音乐。诗人读诗和钢琴家的演奏交替进行,音乐与诗歌交织辉映。同样是2018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诗歌节,开幕式几乎成了各国诗人的才艺表演盛会,没有诗人不会吹拉弹唱的。
2019年5月,终于有机会在上海1862时尚艺术中心完成了三天的诗歌音乐剧场演出,我邀请的二十多位诗人和音乐家们来自八个国家,他们中既有包括英、德、西班牙等主要语种的诗人,也有瑞典语、斯洛文尼亚语等小语种的诗人,他们都是活跃于当今诗坛,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的著名诗人,其中既有年逾八十、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老诗人,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诗人,更有欧美当红的新锐年轻诗人。所有的诗人都用母语朗读他们的诗作,来自大西南的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也用彝语朗诵。诗人的原声朗读也许是最精准的诠释,断句,空白,停顿,甚至呼吸,都是一次又一次不可复制的静止与启动。大屏幕上与诗人朗读同步出现的是原文和中译的字幕。这三场演出的音乐和诗歌不仅关联紧密,而且是有机的结合。诗人们和他们熟悉和合作过的音乐家一起完成演出,把诗歌、音乐,影像作为一个整体做成了具有剧场效果的诗歌音乐会,此次演出有中国传统乐器,有民间音乐,有电音,有民谣,不同的音乐风格同台碰撞,充分体现差异性。在体会声音魅力的同时,让人去想象诗歌描绘的一切,去体会超越语言和音乐的感动。
1862时尚艺术中心是一个有800个座位的剧场,三场演出,2400张票,剧场给演出定的最高票价是1080元。此前我从未做过演出,更何况是大型演出,真是无知者无畏,做起来才知道有多困难,各种意外接连发生,包括在临近演出之前,有诗人因为身体原因突然来不来了。我记得演出前一个月采访林怀民,他告诫我说:你会和所有的人吵架,和导演吵,和演员吵,和工作人员吵,你会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演出了!但是演出完了以后没几天,你又全都忘了,觉得可以继续试试。下半年,林怀民又带团来上海,看完演出我去后台看他,我说:林老师,你真是料事如神,你说的几乎都应验了!林怀民幽幽一乐:老狐狸厉害吧。
之后我还在深圳风火创意空间制作了规模更大的跨年诗歌音乐剧场,通过影像、多媒体、舞蹈、音乐、当代艺术去演绎诗歌,比1862的演出走得更远。但是因为疫情,很多已经在实施和进行中的诗歌音乐剧场不得不停了下来,本来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崖丽娟:您游历广泛、阅历丰富,喜欢摄影,曾在《南方周末》做过记者,这种观察者身份似乎构成您与世界的对话方式,给您的创作带来什么影响?您有一本法文版诗集《无声的城市》是关于上海主题的诗选,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您觉得有“诗意”吗?“诗意”对城市、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寅:每一个城市都有其诗意的一面,上海的诗意,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又有其多元和丰富性,但是诗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要强调一点,诗意和诗歌创作一样,意味着无处不在的创造力和可能性,而不能狭隘地理解成“唯美”的代名词。
与其说一座城市是否有诗意,不如说一座城市是否有足够吸引人的地方,足够丰富,足够有特色,足够让我流连忘返,甚至有足够一目了然的缺陷和需要慢慢发掘的优点,巴黎、伦敦、纽约、柏林就是这样的城市,也可以加上近几年的上海,经历过封城静默之后的上海也不一样了。
当年在上海电视台工作期间,我曾经参与拍摄二十集的《大上海》纪录片,在两年多的时间,埋头于故纸堆,寻访当时还在世的老人们,获得很多精彩的发现,历史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呆板枯燥,而是充满了鲜活的故事。我很庆幸生活成长在这样的城市,有机会和历史深处匪夷所思的幽灵相逢。
是的,我在我的法文版诗集《无声的城市》(这是一本上海主题诗选)的前言里写过这样的话:
“这里是我出生和生活的地方,但却又是我最感陌生、最不敢触碰的地带。
在我面前,有三个上海,一个是已经成为传奇的历史之城,一个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一个是当下面貌发生了巨变的魔都。
第一个上海年代久远,神秘、冒险、奢靡、放纵、繁华、战争……但是由于衍生和附着了太多的注解和想象,面目已经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我怀念第二个贫穷但却亲切的上海,我无意提及它的过去,就像不习惯援引忧伤。过去意味着叮当响的无轨电车,意味着爬上家中的老虎窗,就可以遥望外滩的海关钟楼、听见黄浦江上的笛声,意味着闷热溽湿的夏天、寒冷刺骨的冬天、漫长得无休无止的霉雨季节。对贫困和忧伤年代的回忆有时候竟然是甜蜜的。
如今的城市令我倍感陌生,太多的奢华浮浅、太多的贪婪喧嚣,已经越来越像一个舞台……”
上海在我的生活中如此重要,以至于我最终要用一本书来书写它,形式可能是多样的、混杂的、丰富的,就像上海本身一样。
摄影与诗歌有着天然的联系,很多优秀的诗人也是风格独特的摄影家,如艾伦·金斯伯格、吉增刚造、北岛等,中国当代诗人玩摄影的就更多了。几年前,答诗人沈苇对我做的访问,现在依然适用:
“摄影教会我观看世界的别样方式,就像诗歌教会我歌唱和聆听一样。摄影让我更多地接触到现实世界神秘的部分,我经常在照片的暗处发现那些肉眼没有察觉之物、那些看不见的幽灵:隐藏在黑暗中的人、一道隐秘的光亮。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奇怪物体……
“诗和摄影采用不同媒介,但两者又有很多共同之处,词语、色彩、韵律和意象,诗歌中有的,摄影中也有。相对而言,诗在表达上更趋于抽象,摄影则要具体得多,摄影看似直接和安静,但也隐藏了更多的隐喻和解读的可能,诗歌的呈现则更为赤裸。
“创作经常是盲目和自发的,可以从一首诗出发,也可以从按下快门出发,一切取决于机缘和情绪。取景,在按下快门之前,就已经预先完成构图和曝光了,就像写诗,在落笔之前,草稿已经在心里完成。我很喜欢曼·雷的一段话,这里稍稍改动了一下:‘我用摄影表达诗歌不能表达的,我用诗歌表达摄影不能表达的。’”
崖丽娟:正如您上面所言及,词语、色彩、韵律和意象,诗歌中有的,摄影中也有。诗歌作为一门特殊的综合艺术,通过语言营造声音、意境和画面感,您的诗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语言既有古典的诗画融合的意境,又具有现代汉语的质感,甚至带有戏剧性写作特征。您在处理诗意与画面感的关系、在寻找自己的诗歌声音时有什么独特体验?
王寅:你很敏感,每一首诗的起点和来源都不尽相同,有的是从音乐性出发,有时候从画面出发,有的仅仅是一些特别的字和词语,组合在一起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我有一首专为听觉写的诗,词语在语意上并无关联,而是以同音词组成的纯听觉的诗,其目的除了语言的实验,也为了打破固有的阅读习惯,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获得新的感受。诗歌写作也是一种倾听和凝视,音乐性、图像和语言之间的切换是有趣的话题。诗歌和文学也一样,也要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实验,不断拓展边界。
崖丽娟:一首好诗肯定会让读者享受到情怀与智慧交织的愉悦,体会到思考与发掘的意义。好诗的标准有哪些基本要素?您的诗歌基本上在30行之内,几乎没看到您写作长诗,为什么?
王寅:好诗是没有标准的,更准确地说,每一首新的好诗都是横空出世的,都是无视所有前人的创作,在打破之前好诗的基础上产生的,每一首好诗都确立了好诗新的标准,这也是诗歌迥然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之处。如果一定要说好诗的基本要素,那就是“新”——表达新、语言新、让人眼睛一亮的那种新。
我写过长诗,并不成功。以我有限的尝试而论,我曾经以为长诗在某种程度上是多余的。现在看来,这个结论可能下得太早了。
崖丽娟:我访谈的嘉宾中,有不少诗人兼事批评,您却不太写作评论,您会思考一些诗学问题吗?比如,您参加过国外很多诗歌节活动,如果与国外诗歌创作氛围进行比较,中国当代诗坛存在哪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王寅:我刚才说过,中外诗歌的交流其实是不对等的,中国对外国文学(包括诗歌)的了解远远大于外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的了解。不是中国没有好的诗人,恰恰相反,中国有世界一流的好诗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机会被大量地翻译成外文,被外界所了解。
文学评论,尤其是诗歌评论是一门学问,和写诗不尽相同,那些既写得一首好诗,又写得一手好评论的诗人,是不可多得的双枪将。对我来说,写好诗,就够了。
崖丽娟:您应该算真早慧诗人,十岁就开始写诗,还记得在什么刊物发表第一首诗吗?获得的第一个诗歌奖是什么?
王寅:一个诗人发表的作品再多,他也是不会忘记他的处女作在哪里发表的,更何况在当年发表作品非常困难的时候。在《诗集的故事》里(此文收录在我的新诗集《低温下的美》中),我回忆了处女作发表的过程:
“1986年冬天,我去兰州出差,特地去《飞天》编辑部看望了诗歌编辑张书绅。我的处女作当年就发表在《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上,很多后来成名的诗人都经张书绅之手在《飞天》发表过作品。张书绅每信必回,而且他的回信永远用铅笔写在杂志社小小的便笺上。
“在不知投了多少次稿之后,终于有一天,我收到的不再是退稿信,而是刊用通知。《飞天》1983年10月号发表了我的两首短诗《面对青草》和《非洲》,收到14元稿费后,就请好友们去徐家汇的新利查吃了一顿西餐(这家西餐厅居然还在),给女朋友买了一只网球拍(因为吃饭后余下的钱只够买一只)。当时尚未谋面的封新城等兰州大学学生正在《飞天》实习,他们说服张书绅发表了我的成名作《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我获得的第一个诗歌奖,也是《飞天》颁发的——《华尔特·惠特曼》获得《飞天》1985年优秀诗歌奖。“
崖丽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时,诗人陈东东和您是同班同学,现在你们都成为了代表性诗人。四十年来,你们之间保持深厚友谊,这种纯粹的诗歌友谊给您最大的受益是什么?
王寅:我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文学狂热的特殊时代,我就读的大学,中文系人人写诗、抄诗、谈诗,诗歌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这在现在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就是如此。我也很庆幸在大学时代遇到了陈东东这样优秀的诗人,我们在一个宿舍同窗四年,入学之初,他每天手捧厚厚的、让我望而生畏的《战争与和平》看得津津有味,而且全部看完了。我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一起写诗,一起办油印诗刊,一起旷课,一起骑车郊游,干过很多调皮捣蛋的事情,……陈东东在他的长文《游侠传奇》里写过这段经历。
崖丽娟:您如何保持激情和创造力以克服长期写作中遭遇的瓶颈和低谷?您写作依靠灵感触发吗?这是否得益于做记者的职业敏锐?对写作环境有要求吗?平时是用零散时间还是整块时间进行创作?会经常修改旧作吗?
王寅:我经常遇到所谓的瓶颈和低谷,但我从来没有为此烦恼过,写不出就放下笔,该干嘛就干嘛,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过一段时间,诗歌自然会来找你。即使你不再写诗了,别人还是会把你当成一个诗人。
曾经有朋友发出疑问,一个诗人怎么也能当得好记者?事实上,我对当记者的热情远在做一个诗人之上,在媒体兴盛的年代,记者有很多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可以极大地满足我云游四方的愿望。我给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业余诗人,诗歌只是我的众多兴趣之一,我很乐于尝试各种新奇的玩意儿。
我是一个从不挑剔写作场所的诗人,在旅途中,在高铁上,汽车里随时可以写,大部分时候是记录在手机的备忘录里,来不及记录下来,就用手机录音。特别的环境反而会激发我的创作热情,我有不少诗是在密闭的飞行器里一气呵成的,飞机上的呕吐袋经常被我胡涂乱抹,写得满满的,我收集了不同航司五花八门的呕吐袋。有大学的研究机构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收藏我的这些呕吐袋手稿,在送出去之前,先做一个呕吐袋手稿展也未可知。
修改,当然有,但不会有诗人多多说的修改七十次那样多。我基本不改旧作,与其花时间修改,不如去写新的作品。
崖丽娟:诗人北岛曾这样评价您:“作为先锋诗歌,王寅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但是您似乎对诗作的出版很谨慎,目前只看到您在国内出版《王寅诗选》《灰光灯》《低温下的美》等诗集,哦,对了,2022年您的第二本英文诗集《和幽灵在一起的夏日》由纽约书评出版社出版,著名诗人阿多尼斯作序推荐。接下来还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王寅:诗集出得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原因。早年出诗集很困难,我一直到四十多岁,才由林贤治老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寅诗选》,这也是我的第一本书,远远晚于同辈出版第一本书的时间。由于出诗集难,我的第一本诗集变成30年创作的选集,如此的好处是略过了出各种诗集,直接就成了一本诗选。林老师是我的恩师,我对他唯有感谢,如果不是因为他,我的第一本书还会遥遥无期。此后诗集出得不多,是我写得少,对自己的作品也不甚满意。
今年年初出版了《低温下的美》,去年夏天,纽约书评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诗集《和幽灵在一起的夏日》。此外还有由古巴艺术家手工制作的西班牙语诗集,这本诗集限量200册,是美籍古巴诗人朋友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努涅斯((Victor Rodriguez Nunez))策划的,原本应该在前年出版的,由于疫情顺延到今年,是我十分期待的诗集。另外,还将完成记录近年来旅行的随笔集《偶然的时间》。
2023年8月31日

附:
王寅的诗
水
有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
有很长一段时间河水看着我的脸
河水是句子
和你一起沿着夜晚的河岸散步走过铁桥
最后一次默默地看水
因为无言,因为形同独自一人
因为这时候可以看见自己想些什么
看水,因为不知道时间,因为水向下流去
像我们的脚步,因为水向下流去不会再流回来
看水,成为一种特殊物质
但我们饮水不是为了成为水,不是立即
水使我手指柔软品质坚定
看水,是因为我想干些什么
而工作是有限的,休息是无限的
这时候,水像阳光一样闪闪发光像爱人的头发
水有倾泻而下的声音
水有一种以上的颜色
水把我和你隔开在城市两边
水是句子
水经常从天花板从墙上流过
我展开的手掌上也有流水有痕迹
水像风
水里看不见红色的马看不见黑色的马夫
梦里常感到焦渴,太阳斜照下来
井里没有水
南方的河流不会封冻
水没有门,如果我不想死
我不会死
水是清澈的
水中有鱼,而鱼是没有声带的
没有一封信用水写成
在黑暗的地方
水就是灯
水果里有水,书和草木
我们的身体里也有水
石头也有流动的时候
我们已不看远方的绵绵群山
水平静的时候
像一把椅子一条街道一片天空
我映照你,映照水
只有睡在水上才没有痕迹
才会平稳得像水下的船航行
最后一天我从铁桥上下来
河水是句子
他们的流逝使我安心
生活要有条不紊,从容不迫
他们去的地方我是不能去的
送斧子的人来了
送斧子的人来了
斧子来了
低飞的绳索
缓缓下降的砖瓦木屑
在光荣中颤栗
送斧子的人来了
斧子的微笑
一如四季的轮转
岁月的肌肤
抹得油亮
被绳索锁住的呜咽
穿过恐惧
终于切开夜晚的镜面
送斧子的人来了
斧子的歌曲中断在它的使命中
送斧子的人来了
我们的头来了
珍 藏
这就是我分享的犹豫
早晨的波浪
幽禁的芬芳
依然甚于不朽的黑暗
这就是相像的鸟群
鸟所期望的天堂
天堂里的我们
散发出骸骨的气息
这就是岁月的岁月
终结的朝露
每一个飞逝的隐喻
停泊在致命的月光下
晚年来得太晚了
晚年来得太晚了
在不缺少酒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杯子,夜晚
再也没有了葡萄的颜色
十月的向日葵是昏迷的雨滴
也是燃烧的绸缎
放大了颗粒的时间
装满黑夜的相册
漂浮的草帽遮盖着
隐名埋姓的风景
生命里的怕、毛衣下的痛
风暴聚集了残余的灵魂
晚年来得太晚了
我继续遵循爱与死的预言
一如我的心早就
习惯了可耻的忧伤
炎热的冬天
为什么我的时代要反对我
为什么要扭断我的脖子
为什么我歌唱过的季节
也要将我毁灭
为什么异己的气味弥漫广场
天然的敌意,不祥的沉寂
伪善的精华,虚假的承诺
我一无所知的阴谋
和调羹一起搅动
为什么命运将我置于冲突的中心
为什么要控制我胆怯的灵魂
使我免于抽泣
为什么又使我像普通读者那样
在图书馆光滑的桌面上消磨时光
为什么我的心脏
成为世界上跳动得最为缓慢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上帝依然对我如此仁慈
使我有时间看完这一切
使我在这炎热的冬天
将一再延误的时间
倾吐而出
幽暗中的人弹着吉他
幽暗中的人弹着吉他
吟唱的是红色的花朵
也许是郊外摇曳的罂粟
也许是另一种不知名的花
有松树的庭院,黎明时分
落满松果,孔雀在花园里踱步
一把黑伞一顶帽子
沉在水池底部
午夜的雪花从桥下涌起
漫过头顶,升上星空
它们从高处俯瞰城市
就像格列柯一样
郊外开满了腥红的花朵
幽暗中的人弹着吉他
你摘下的珍珠耳环
在桌面上来回滚动
它们互相撞击的声音
微乎其微,就是罂粟
摇曳地开放,就是有人
再次拨响了幽暗的吉他
你偏爱冷僻的词语
你已经感觉不到痛了
你也已经感觉不到冷了
你开始偏爱冷僻的词语
偏爱低产,偏爱均速,
你偏爱气泡水
你偏爱旧书的气味
偏爱昏睡,而不是清醒
你偏爱用听不见的声音读一首诗
用铅笔在纸巾上写下难以辨认的字迹
就像无法复原的破碎梦境
你已经感觉不到痛了
你也已经感觉不到冷了
你偏爱的春天也有阵亡的花朵
它们延续了上一季的寒意
恶作剧
这是两个
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
他们的诗集
却在书架上成为邻居
就像把他们紧挨着
葬在一起

王寅,诗人,出版诗集《王寅诗选》《灰光灯》《低温下的美》等,获得第一届江南诗歌奖、第三届东荡子诗歌奖等多个诗歌奖。作品被译成十六种文字,先后出版法语诗集三种、英语诗集、西班牙语诗集各两种、波兰语、斯洛文尼亚语诗集各一种。

崖丽娟,壮族。现居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兼诗歌批评。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其中,《会思考的鱼》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奖“,编著有10余部文史书籍,诗歌、评论、访谈发表于《上海文学》《作品》《诗刊》《诗选刊》《诗林》《诗潮》《星星》诗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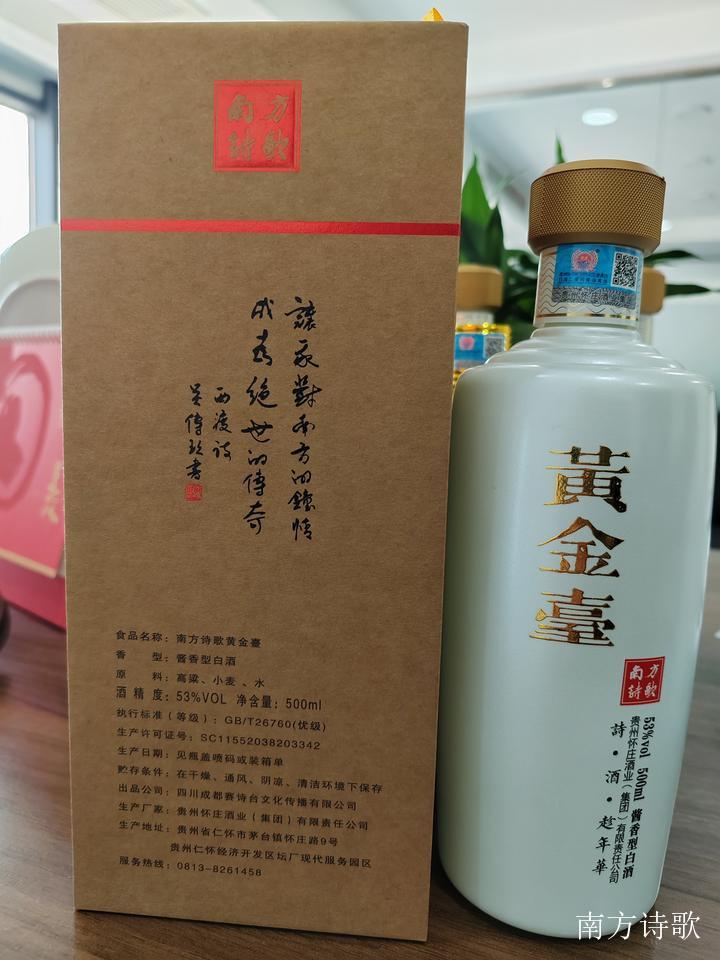

《南方诗歌》2023年10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11月目录
张卫东:晦暗的布局刚好盖过了词语
李聿中:十二份的悲伤(组诗)
“90度诗点”:冯晏&张媛媛|观测与被观测的诗——读冯晏近作
“香樟木诗学”:中国当代诗歌呼唤“绝对文本”
“他山诗石”:温经天 译|鹿是光芒之间游走的幽灵——外国诗歌精选10首
“未来诗学”:王东东|漫谈一种现代诗教
阿娜尔:千山外,白云边
也牛:菩萨寂寞时长一身灰
许天伦:信仰被高高举起又落下
“未来诗学”|婴儿易:王君的诗歌创作与刘凡中的书法互文
高春林:躲雨的人(8首)
游天杰:天空是我爱你唯一的理由
卢文悦:世界的骨灰——献给艾略特《荒原》
桑克:最难拿捏的生存技艺
麦豆:感受一个词的反义
哑石:六月“非诗”
“他山诗石”:黄琳 译|娜塔莉亚.科雷亚 诗十八首
“未来诗学”:蔡启鹏|“现代主义”不一定“贫困”
广子:荒野的召唤(系列诗组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