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毅 《互托邦》 (纸面水彩)
在前阵子有关“未来诗学”的讨论[1]中,张伟栋提出了“现代主义的贫困”,批评当代诗日益陷入了现代主义的书写逻辑,包含四个层面:历史的消解;个人写作的盛行;语言的本体论意识;“历史分裂症”。[2]但他又没有彻底否定这类“现代主义”[3],尽管张限于他本人强烈的问题意识,并没有指明这类“现代主义”的优长到底何在。而其他论者也几乎都没有指出这类“现代主义”的长处。我们知道,在当代新诗的每一个阶段中,确实都存在着一大批走现代主义路子的诗作,比如朦胧诗时期的《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雨夜》、《阳光中的向日葵》;第三代诗歌时期的《表达》、《震颤》;九十年代的《下雨——纪念克鲁泡特金》、《祖父》;新世纪的《知音学丛书——纪念陈敬容》、《珠海见闻录》等等。那么,走现代主义路子的当代新诗到底有什么优长?
“现代主义的贫困”属于一种比较宏观的说法,像许多宏论一样,大体上来看,是没问题的。但是,此说也像许多宏论一样,仔细考察,就可以看出它的粗疏之处。因为,不少走现代主义路子的当代新诗其实已经溢出了该说中的很多定性。比如,张认为当代新诗是“个人写作”,“个人私密化”的,这当然有道理,适合不少走现代主义路子的当代新诗,但是,以此来框限有些这类诗歌,就未免多多少少存在牵强之处,例如北岛的名诗《回答》、顾城的《一代人》、 肖开愚的《下雨——纪念克鲁泡特金》。这些诗歌或关涉时代、或隐含政治性,不完全是个人私密化的。
不过,笔者试图论证的关键点在于“现代主义”尽管“贫困”,但也有不贫困之处。如果我们沿着“存在即合理”的思路,一种延续了近50年的诗歌路径,果真会没有任何优点?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许多当代新诗的优点就包括:对诗歌修辞的深入开掘、书写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里的噬心生命体验。如果对这些优点视而不察,任由当代新诗的优长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过多地去批评之前的当代新诗,就很容易变成诗坛上又一次反抗前辈、树立新旗的占位行为,那么,这样一来,不仅无法很好地吸取前人的优长,造成集大成的伟大诗人,还很有可能导致批评的狭隘化、偏激化,讨论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了。
对于诗歌修辞,诗坛流行的是一种轻视的态度,因为这会妨碍诗歌书写生命体验。但是,在当代新诗中,修辞和“生命”虽然确实经常无法协调,但这似乎只能归因于写作者本身处理不好,二者实则绝非是必然会冲突的。张枣诗里就有一句“她感到他像图画,镶在来世中”(《历史与欲望(组诗)》)。这句诗中的修辞(比如比喻)是非常明显的,但它将恋人“她”的细腻情思写得相当到位,这里的修辞和“生命”又有何冲突呢?因此,尽管我认为在批评修辞妨碍“生命”时,确实符合部分事实(比如欧阳江河及其模仿者的一些诗),但是,它不能说明全部,而且,它也无法否定当代新诗在修辞上的贡献:因为修辞不是一件坏事,很可能还会是件好事,不应被随意地拒绝。
西方现代主义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浪漫主义发展到极端,情感泛滥,而技巧苍白,现代主义因而更重视诗歌的技艺。事实上,许多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当代新诗确实为新诗的修辞和语言表现力贡献甚多。民国时期,胡适乃至郭沫若的诗歌在修辞上、技艺上都是贫瘠的,后起的象征派和现代派为新诗的语言修辞提供了不少生机,但直到当代,历经朦胧诗、第三代诗歌、90年代诗歌、新世纪诗歌,新诗的修辞才有了较大的成熟。可以说,现代诗不如当代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诗歌的修辞能力。所以,正如南北朝时期为古典诗歌积累了丰富的修辞、技术,才有了唐宋诗歌的繁荣局面,当代新诗开掘修辞,也为之后的新诗储备了语言资源,即使就以修辞为工具的角度,也提供了一套相当实用的工具,贡献实则不小。需要注意的是,南北朝诗歌往往受到奇技淫巧、情感空洞的指责,但仍然无法否认它们在诗歌修辞、技艺上的贡献,当代新诗确实可以笼统地说成轻视生命体验的表达,但与南北朝诗歌类似的是,修辞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
第三代诗人张枣的诗之修辞就相当成熟。比如,有论者如此评价张枣的诗:“他的比喻结构非常特殊,常以一个夸张丰盈的动作或场景为本体,却冠以一个抽象动词为喻体。比如《何人斯》中很出名的一句:‘我咬一口自己摘来的鲜桃,让你/清洁的牙齿也尝一口,甜润的/让你也全身膨胀如感激”,或‘屏息的樟脑紧握自己像紧握革命’(《夜色温柔》)……这些比喻很难以相似性原则去揣度,更多是令人会心一笑的灵感乍现。其中,本体和喻体之间具象和抽象的颠倒成为巧智最为集中的体现……当然其中也不乏句子长短节奏的考虑。”[4]
一行指出,臧棣的修辞技艺有着多样的手法和细致的方法。比如“在《蝶恋花》中尝试了新的句法(在后来的作品中被反复使用),其标记是‘于……’这一介词或连接词。将‘抚摸’比作‘切线运动在引线上’,这个几何式的比喻在此有了强烈的直观性。”又如, “《抒情诗》则是为每一比喻安排一个恰当的情境的典范:对‘细’的诸多形容,每一个喻体都被引向一个事件性的情境。”可以说,“臧棣对比喻之可能性的持续探索”,使“我们现在可以更精密地使用词语和句法”[5]。
前文提及欧阳江河,他的一些诗歌确实存在重修辞、妨碍生命体验表达的问题。但内里的情况也很复杂,因为这些诗作写得不好不完全是“生命”的问题,也是因为新出现的修辞用到后来,用得太多了,显得重复,变得陈旧,即这也是一个修辞本身处理得不好的问题。如果我们看欧阳江河的《手枪》、《玻璃工厂》、《咖啡馆》、《时装店》等等将修辞处理得较好的诗作,就可以看出他对当代新诗在修辞上的贡献。比如,他差不多第一个将悖论、奇喻的手法大量带入诗歌:“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玻璃工厂》)、“就象鸟在一片纯光中坚持了阴影。”(《玻璃工厂》)、“就像到处都是空气,空气近于不存在。”(《玻璃工厂》)、“从她的胸脯里拉出两只抽屉”(《手枪》)、“草莓只是牙齿到肉体的一种速度”(《草莓》)等等。尽管后来类似的修辞在欧阳江河的诗中出现得太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修辞刚出现、用得还不是太多的时候还是很新鲜的。又如,一行指出,欧阳江河“在新诗中第一次将日常生活、自然、文学、历史、艺术、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等领域的专业词汇,全部融合在具有清晰秩序和良好语感的修辞句群中:
七根琴弦的彩虹骤现。旋律即天空。
唱片在地轴上转动,铭记乌鸦的纹理。
彩虹的七根琴弦像七条宽阔的大街,
把一座城市勒在我手里,就像
一匹狂奔的马看见悬崖时突然停住。
街道通向古罗马……
这一节包含着非常高超的比喻手法和对语言的控制力。[6]
当代中国属于一个现代化社会,此际的有些现象是在西方也有的,比如工业化、城镇化、环境保护问题,以及社会氛围的娱乐化、大众狂热追求物质等;有些则是中国本土的现实经验,比如申奥成功等。许多走现代主义路子的当代新诗就书写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社会里人们的噬心生命体验,这就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和表现力,也使诗歌有了更亲切的贴地性,不至于沦为脱离时代的空中楼阁。无可否认,这种“走进时代”的写法自然也属于书写生命体验的生命写作之一种,也有它本身的价值与意义,比如促进了生命写作乃至新诗的多元化。
现代主义往往被认为追求技巧,忽视生命体验。这样的认知实则不太对。现代主义产生于西方,产生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表达在西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所感受到的苦闷、颓丧、异化。可以说,现代主义的起因中即包含了生命感。在里尔克、艾略特、波德莱尔等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诗中,触动我们的,还不完全是它们的技艺,也在于诗中的生命体验。
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许多当代新诗一方面追求技艺,一方面也在书写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带给人的生命感受。比如北岛的《触电》,陈超指出,此诗“以‘触电’作为整体隐喻和象征,尖锐而准确地反思和命名了一个异化的时代。在生存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电击’的猜忌和仇恨关系”,“但诗人马上将此导入自审和忏悔层面”。北岛类似的诗作还有《履历》、《同谋》、《白日梦》等。[7]
多多的《痴呆山上》以精湛的艺术手法“深深触及了当代中国城镇化历程中的某种现实”:“当矿区隐在一阵很轻的雷声中/一道清晨的大裂缝//也测到了人/沉默影子中纯粹的重量//那埋着古船古镜的古镇/也埋着你的家乡”。结尾“在平静、冷漠的语调中,暗藏着切齿的恨意”:“多好,恶和它的饥饿还很年轻……”。[8]
于坚有不少诗歌反思、批判工业社会,表达抒情主体在现代文明中的诸多个人感受:愤慨、失落、痛苦等等。这样的诗歌包括:《愀然》、《很快》、《读康熙信中写到的黄河》等等。不妨摘录一些:“念旧的毛病总令我扑空 月光垂下来/含着谁的眼泪或遗珠 歇在全新的地球上/像是刚刚从原子弹爆炸后的废墟爬出/深度烧伤的患者 我缠着看不见的绷带”(《愀然》);“从红灯到绿灯很快/从公鸡到铁公鸡很快/从诗人到商人很快/家搬得很快/话越说越快/便宜的时代/熙熙攘攘滔滔不绝/人去楼空很快/从离婚到结婚很快”(《很快》)。
因此,走现代主义路子的当代新诗自有优长,单单批评它们,就会以偏概全,存在矫枉过正之弊,有点像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要驳斥“未来诗学”中的诸多批评走现代主义路子的当代新诗的言论,当代新诗由于长期沉浸于“现代主义”,几乎发展到极端,确实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但是,如果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事物总是既有短处,又有长处。而事物的长处里就包含短处,短处里也暗藏长处,“现代主义的贫困”里也一定包含着不“贫困”之处,比如,张伟栋指出走现代主义路子的当代新诗“追求语言本身的新颖性”,“这使诗不是朝向生命打开”[9],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这类诗作为当代新诗的修辞贡献很大。笔者有些出人意料地论述这类当代新诗的长处,不是完全肯定这些诗歌,也不是要挑战之前的言论,更不是故作惊人语、博人眼球,而是为了更好地还原事物的真相,更多地揭示事物的尚算晦暗的另一面,以期为看到全部的真理发挥作用,也为当代新诗的未来提供某种应有的动力:当代新诗的修辞能力似乎还可以继续拓深,现代主义还将有可能发挥极大的作用。更何况,即使是像海子这样极其背离现代主义的诗人,也不乏现代主义气质,海子诗歌的修辞里就可以找到很多现代主义的影子,我们很可能进入了“无边的现代主义”时代。但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论题了,就此打住吧。
注 :
[1]对于“未来诗学”的相关讨论,可参见微信公众号“拾壹月论坛”里的相关文章, javascript:void(0);。
[2]张伟栋等:《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上半场]座谈纪要》,微信公众号“拾壹月论坛”, javascript:void(0);。
[3]比如,张伟栋在“未来诗学”的讨论中指出:“我不是用这个东西去否定谁,九十年代当然非常重要”,见张伟栋等:《如何想象一种未来诗学——“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下半场]座谈纪要》,微信公众号“拾壹月论坛”, javascript:void(0);。
[4]李倩冉:《被悬置的主体——论张枣》,《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
[5]一行:《“修辞机器”:九十年代诗歌中比喻的专业化》,微信公众号“诗评媒”, javascript:void(0);。
[6]一行:《“修辞机器”:九十年代诗歌中比喻的专业化》,微信公众号“诗评媒”, javascript:void(0);。
[7]陈超:《让诗与真互赠沉重的庄严——北岛诗歌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第280-304页。
[8]对多多《痴呆山上》的相关分析,参见周东升:《多多的孤愤:细读<痴呆山上>》,《诗歌月刊》2021年第3期。
[9]张伟栋等:《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上半场]座谈纪要》,微信公众号“拾壹月论坛”, javascript:void(0);。

蔡启鹏,生于1996年,浙江温州人。爱好写诗,写诗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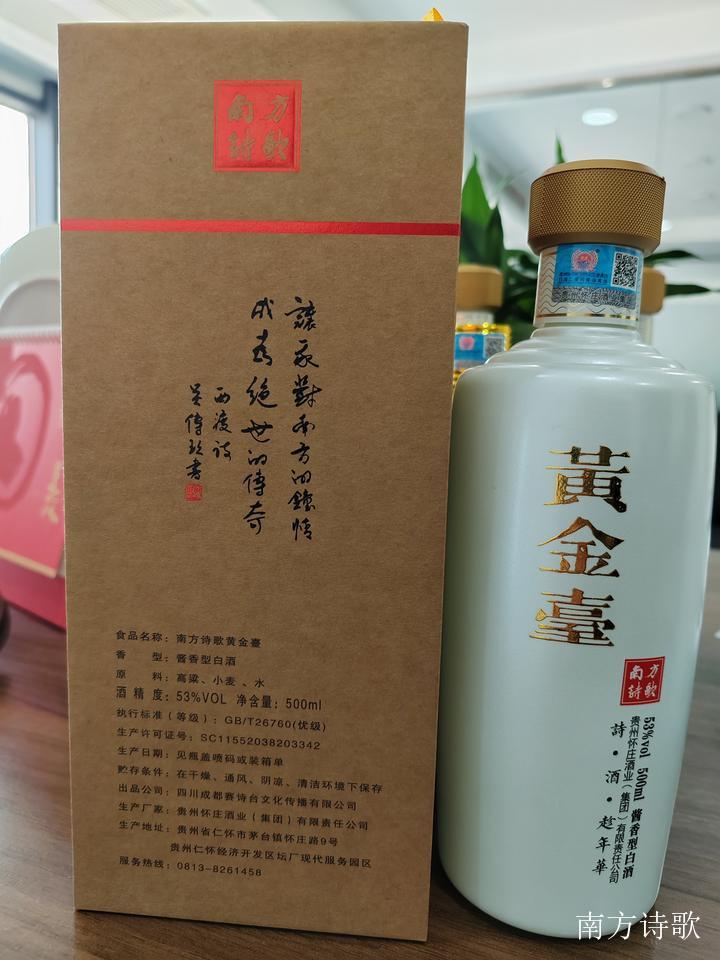

《南方诗歌》2023年10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11月目录
张卫东:晦暗的布局刚好盖过了词语
李聿中:十二份的悲伤(组诗)
“90度诗点”:冯晏&张媛媛|观测与被观测的诗——读冯晏近作
“香樟木诗学”:中国当代诗歌呼唤“绝对文本”
“他山诗石”:温经天 译|鹿是光芒之间游走的幽灵——外国诗歌精选10首
“未来诗学”:王东东|漫谈一种现代诗教
阿娜尔:千山外,白云边
也牛:菩萨寂寞时长一身灰
许天伦:信仰被高高举起又落下
“未来诗学”|婴儿易:王君的诗歌创作与刘凡中的书法互文
高春林:躲雨的人(8首)
游天杰:天空是我爱你唯一的理由
卢文悦:世界的骨灰——献给艾略特《荒原》
桑克:最难拿捏的生存技艺
麦豆:感受一个词的反义
哑石:六月“非诗”
“他山诗石”:黄琳 译|娜塔莉亚.科雷亚 诗十八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