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 梁崴 画
敬文东:早在1991年,您就在题名为《写作》的短诗里树立了写作的方向,那就是向母语和伟大的汉语传统致敬。而在更早的1988年,您写下了早期代表作《字的研究》,结尾处有这样的句子:“我自问,一个古老的字/历尽劫难,怎样坚持理想/现在它质朴、优雅,气息如兰/决定了我的复活与死亡。”在那个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如日中天的年月,您年纪轻轻,为何有那种退回传统的想法?
赵野:我的写作一开始,就与先锋无缘。我最早热爱的诗人,并在风格和审美上深受其影响的是何其芳、冯至与卞之琳,他们是我诗歌的源头,让我对语言和形式有着固执的要求。那是1979年,我生活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没有外来的风暴,都是自己在生长。1981年我进入四川大学,瞬间遭遇各种现代主义诗歌,不停地受着各种冲击。影响是全方位的,从一个意象、一个比喻、一种句法,到诗歌的种种方法论和价值观,让人眼花缭乱,加之深度介入成都的诗歌运动,那个时期比较开放,也做过很多尝试。可能还是心性使然,1984年,我读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高尔泰的《论美》,里面的部分内容让我一下子感觉到和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与美学接通了,我迷恋他们的心灵和生活,并意识到写作应该建立自己的语言,建构一种真正的现代汉语。可以说那时起,我已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只有几十年历史的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还不成熟,作为独立的诗歌文本,除了一些短诗,基本上是不成立的。那时我对语言做了很多思考,有了一些想法。1985年,我写出了组诗《河》,算是当时那些想法的一次实践,以抒情诗的形式,表现语言和它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有着思想和哲学的东西。1988年的《字的研究》,是分析性写法,回到汉语的源头,想找出汉字的特质,以及我对汉字的一些观念性认知。我后来看到周有光说,因为汉语的语法结构,中国哲学都成了关于人生的哲学,而与逻辑和科学无缘。那么,辜鸿铭说汉语是一种诗的语言,应该是完全成立的。事实上,庞德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现了汉字有一种自然的势能,“言语中的各部分一个字一个字地蓬勃生长,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一方面,我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想到退回传统,但在思考汉语成其所是的那些要素,我理想中的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要建立在这些要素上。另一方面,我需要找到人之为人的那些要素,中国古人的生命态度和精神方式,完全契合我的内心。也就是说,生活和写作都让我往回看,传统里有我真正需要的东西。准确地讲,我没有退回传统,只是明白了要从传统出发,传统是我的起点和根基,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前面。
敬文东:在一篇回忆性的短文里,您曾这样写道:“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以加速度变化着,我们所有的经验和价值观,都源于农业时代的趣味和标准,这眼花缭乱的一切,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农耕经验原本是古典诗歌的地盘,用新诗描写农耕经验,您是否有一种违和或者矛盾的感觉?
赵野:其实,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说法,或者说个人隐喻。这儿的“农业时代”,指的不是农耕文明,而是一种以轴心时代的思想为基本价值的人类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或者说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对心灵和精神、人性和情感、永恒和不朽,还持有同样的标准。我对前沿科学会有一些好奇,隐隐有一种担忧,就是未来的人类,和迄今为止的人类,会完全不一样,他们可能完全不需要诗歌,以及其他我们信奉的东西。这篇文章是2008年写的,今天来回答这个问题,感觉更应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星际穿越、元宇宙等,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和理解范围。我甚至觉得,我们可能是最后几代还信任语言,还梦想着写完美诗歌的人。也许再过五十年、一百年,诗歌,以及我们现在还相信的那些价值,就不在了。一百年以后的人类,看诗歌和诗人,和我们看李白、杜甫一定是不一样的。里尔克和艾略特他们,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让人沮丧,不能深究,想得太多会质疑写作的意义和价值。这个上午我还看了一个视频,说在宇宙中,恒星的数量比地球上所有海滩的沙子加起来的总数还多。佛经里常常说“恒河沙数”,以前觉得是一个比喻,现在看来就是事实。想到对宇宙而言,地球真的就只是一粒沙砾,实在是虚无。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用的“农业时代”一词,指一种传统的时空观,而非一种农耕经验。我们已经无法像前人那样,不管是一千年前的,还是一百年前的,对永恒和不朽有着坚定的信念了。
敬文东:2007年,您在小长诗《归园》一开篇写道:“半世漂泊,我该怎样/原宥诗人的原罪/像哈姆雷特,和自己/开一个形式主义玩笑。”我很好奇,作为一个现代中国诗人,他(或她)的原罪到底是什么。
赵野:这个词用在这儿,意义确实比较含混。诗人的原罪,或者说中国诗人的原罪,是指我们身份的不确定,或者我们扪心自问时的不踏实?我们一生中命定的东西?诗人对母语的失职?对正义的缺席?对专制的顺从或沉默?对文化沉疴的无视?又或是诗人本身对时代和生命的对抗与突进?对自由的追求?天生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和对庸众的敌意?也许这个词表达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意思,像德里达的词语游戏。不过,汉语的词不需要通过词形或字母的变异来达成这种效果,它们本身就可以是多义的。当然还可以说,这只是简单的愤世嫉俗,觉得当下的中国诗人只是一帮混混,行走在一个低级的江湖上。这也符合我的词语原则:一个词如果在整首诗的语感里是成立的,那么,它的多义或歧义,会让这首诗的意蕴更丰富。诗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一种感受和意会,诗也不说明什么,它只是一种冒犯和唤醒。
敬文东:“万古愁”是古典汉语诗歌的伟大主题,它甚至可以说是汉语的乡愁。这个词也是您的诗歌中的关键词之一。您可否谈谈新诗到底怎样书写万古愁才是有效的,或者说才是具有现代性的?
赵野:万古愁,还有天下忧,确实是古典汉语诗歌最迷人的地方,但为什么仅仅是古典汉语诗歌呢?如此高级的东西,还是我们独有的特质,应该是汉语本身的。新诗只有在写出这种万古愁和天下忧后,才能接通汉语的文脉,真正成熟起来。万古愁和天下忧对于诗歌,就像仁义礼智信对于人类一样,是我们文化的普世性发现,是汉语诗歌伟大的伦理。中国的现代性,首先要关注的是文明是否抵达。我赞同这样一个观点,文化是民族的、地域的,而文明是普世的,文明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都要得到尊重,每一个心灵都能自由不羁,文明是个人和他人及外部世界的合理的关系。对我们而言,文明还在被种种邪恶的力量阻隔在路上,我们需要表达出一种期盼和挣扎,而这种期盼和挣扎,就是当下的万古愁和天下忧。我认为,欧洲现代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是:上帝死了,只有自己,只有卑贱,只有徒劳,害怕死后的世界(艾略特语)。而中国现代主义最核心的问题则是:世界那样了,我们还这样。那样的世界与这样的我们之间持续的对抗和张力,对当代生活与我们处境的深刻理解和忧患,就是当下汉语诗歌的现代性所在。具体到诗歌写作,还有一个审美的现代性,或者说语感的现代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像玄学,很难说清楚。新诗的语言很有意思,一方面它是新的,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句法和语感;另一方面,它又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这个传统的丰富性妙不可言。伟大的诗歌,要能在这个厚重的传统里纵横捭阖,上天入地,抵达诗意的核心,如万军之中取上将头颅。我近年来有一个看法,我们其实身处一种混杂的现代性里,我们的社会同时具备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种种表象与特征,也同时面对着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与困境。面对匪夷所思的强大的中国现实,单纯的前现代、现代或后现代写作,可能都有问题,会流于简单、过气或浅薄,很难形成对等的挑战。最有力量的作品,应该在情感和美学上也具备这种混杂的现代性,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前现代的明晰、崇高与启迪,现代的深邃、精神性与形式主义,以及后现代解构既有的无所用心与无所顾忌。诗人应该有一种能力,用语言把它们统摄在一起,才能匹配这个现实。这也是我的万古愁和天下忧。
敬文东:海岸对面的余光中几十年前曾在现代气息浓郁的台北市,写下了对唐时洛阳的牡丹、宋时汴梁的荷花的怀念。批评者认为,他是在制造假古董。我认为这样的批评虽然刻薄,但未必没有道理。也有朋友为您捏把汗。您觉得怎样做才能避免重蹈余氏的覆辙?
赵野:余光中和我,完全没有可比性,他的写作路数和我的写作路数,是完全不一样的。回溯传统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很久以来,很多人都在这么说。朦胧诗时期,杨炼写陶罐、半坡,江河写《太阳和他的反光》,都说是回到传统。80年代在成都,宋炜和石光华他们的整体主义,理念直接来自《易》,遑论20世纪30年代时废名、卞之琳他们做出的尝试和努力。古代的人物和事件,唐时洛阳牡丹与宋时汴梁荷花,只是一个个题材,谁都可以写。但写什么重要吗?重要的是怎么写。一首诗成立与否,是看它是否建立了一种成熟的语感。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看到的台湾新诗,语感都是怪怪的,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课题。他们那几代诗人,古文和西学的底子都比我们好,看到的东西也比我们多,经历的一切也不比我们轻松,不知道为什么一写起诗歌,语言就黏糊糊的,民国的腔调一直没有化解开。那么,我们的诗歌语言,是否因为粗鄙的口语化而得到了锻炼?这里扯远了,回到传统这个话题,我觉得传统不是道具和符号,而是精神气质,是我们对社会、自然、人性的态度,以及我们面对虚无、死亡和美的方式,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入传统的,因为“古典并不等于古代。现代与古典的关系并不是现代与古代的关系,而是时代与永恒的关系,这个关系存在于任何时代(柯小刚语)”。近年来我喜欢用“语感”一词,来说明我对诗歌的一些判断,这本身就很传统、很中国,像严羽的“气象”、王士祯的“神韵”、王国维的“境界”。我认为诗之成为诗,首要在语感,但语感就像禅一样,只能绕着说,批评可以分析语感的各种要素,却无法说出语感本身。另外,语感在我这儿,只是诗的普遍价值,而不是诗的最高价值。
敬文东:里尔克认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应该说,敌意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起点。尽管您也曾在诗中写到“我一直低估了诸夏的恶”,但您更愿意坚持在诗里诉说“古老的善意”。这和我们的现实经验是不合拍的,您如何在虚构的善意和真实的敌意之间周旋并辗转成诗的呢?
赵野:里尔克的意思是,诗歌与现实之间一直有一种紧张关系,诗歌要表达出这种紧张关系,需要有对现实的冒犯、反抗、对峙、批判。生活永远是庸常的,而诗必须挺拔高迈。超越一些说,佛家讲无善无恶,因为万法皆空,王阳明也讲“无善无恶心之体”,但王阳明说佛家着了善恶的相,不可以治天下。佛家和王阳明的善恶说,如果在一种奇妙的语感里,也有强大的诗意。我不认为我坚持在诗里诉说“古老的善意”,我是在古老的善意和古老的敌意之间找一种张力。古老的敌意和古老的善意,一直在我们的情感和生活中,也在我们的现实经验中,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生相克,它们之间无穷无尽的冲突、转换和融合,就是诗意的一部分。具体到我的写作,敌意不是我的起点,善意才是,但一路下来,必须冲破重重敌意。不久前我回答了为什么写作,一则直面当下,反思文明;二则解脱心灵,了悟生死;三则重振传统,再塑语言。在这里,第一条是身姿,诗人在语言里会呈现一种身姿,他看着天空和大地,看着人心和历史,直面当下,就是看清我们的生存处境,明了我们的精神危机,洞悉社会和人性的黑暗,并由此反思我们的文化进程、制度设计、历史危局,以及它们和当下的关系;第二条是自我诉求,我希望通过写作,能够让心灵进入一种觉悟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明了生死,实现自我的完成;第三条是抱负,就是要建构一种理想的诗歌语言,重塑传统和山河。诗歌有一万种写法,我尊重所有的写法,但自己只会写内心想写的东西。我关注历史的意义,希望能写出一种正派大气的诗歌,这种诗歌本身就能构成一个宇宙,我们得以在里面确认身份,完成自我,放飞梦想。
敬文东:明代人王璲是您我的四川乡贤,他有两句好诗:“南朝无限伤心事,都在残山剩水中。”在您看来,伟大的汉语传统的美被现代文明破坏了,眼下我们正生活在残山剩水之中,因为您在2018年的一首诗中明确写道:“我们就是文明的灰烬。”您似乎更愿意以文化遗民的身份自居。问题是,这种样态的残山剩水属于现代经验,遗民心态能表达新状态、新形势下的残山剩水吗?
赵野:在我看来,被破坏的不仅仅是“伟大的汉语传统的美”。陈寅恪挽王国维有句“吾侪所学关天意”,我觉得伟大的诗歌,应该有这种气象和格局。我生活在当下,为当下忧心,我的心态和经验当然是当下的心态和经验,自居文化遗民只能说我在坚守一些东西,一些美好和价值,也许还可以说是时代的遗民。这种坚守并不是朝向过去,而是朝向未来的,而且本身也是一种现代经验。
其实,本雅明就是这样做的,他带着当下回溯过去,把过去当下化。
我确确实实相信,当下或未来的伟大的汉语诗歌,必须能承载我们全部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美丽和哀伤,以及我们对它的扬弃和希冀,这才是汉语诗歌真正的现代性。对传统最大的误读,是把传统看作单一形态,认为保守主义者紧紧抓住过去的幻觉,生活在今天的复杂现实中。殊不知传统像一条大河,滚滚而来的除了河水,还有泥沙,以及水面上发臭的浮尸。但河流在那儿,长江黄河日夜流淌,我们不能无视,也无法逃避。
敬文东:《庚子杂诗》直接处理现代经验,整体上很成功,既古意也很现代。看来,您的诗学追求成功的可能性极大,您可否告诉我们您是在何种心态(包括遗民心态)下完成这组了不起的作品的?
赵野:2020年,就是汉语里的庚子年,我们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恐惧、慌乱和忧心。之前的半年里,我一直在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以及余世存先生对《己亥杂诗》的现代解读《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新冠疫情刚开始的那两个月,各种乱象排山倒海般扑来。我开始了《庚子杂诗》的写作。“杂诗”的体例,每一首都是独立的,彼此没有关联,但笼罩在一种统一的氛围和情绪里。每一首都是即兴的,每天看到的新闻,读到的书,经历的人和事,甚至网络上的一句话,都是题材。在形式上每首都是四段八行,每首诗的起兴和完成,和传统的绝句有相同的思路。写作过程中感到这种形式的承载力和包容性都很大,几乎什么心志和情绪都可以表达,像真正的绝句。我认为新诗的形式,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很多的可能性,我通过回到古典诗歌的句法和起兴方式,通过词语的音韵,想找到一种现代汉语诗歌的理想的语感。《庚子杂诗》我总共写了一百二十首,最后定稿为一百零五首,算是对龚自珍的一个致敬。这里我还想谈一谈正在写作的大型组诗《碧岩录》,非常长,一百首,总计一千两百行。这组诗以宗门第一书《碧岩录》为一个原点,希望借助禅宗的语言观和方法论,解放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写作的过程中,感觉是在写一部关于语言、诗歌、色空、生死的元诗。这里也含有我的一个诗学观点:语言如果成立,意义自会显现。七八年前,你的学生颜炼军让我为他的博士论文写一个序,我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这句话。我是过了几年后才突然意识到,这句话其实呈现了一个诗学观点。一般的诗作皆以意义的逻辑或情绪的逻辑展开,而我想试着以语言的逻辑,或者说是感觉的逻辑展开,近几年的写作,不少都是用这种方式完成的,《碧岩录》也是,可能还更极端一些。这组诗我也想找回汉语的节奏、音韵和气象,努力恢复汉语奇妙的语感。因为还没有完成,我不能确定是否成功。不管怎么说,我在写作中感到了巨大的自由和愉悦。词完全解放了,物翩翩起舞,苍山上滚滚而来的风,窗前的蝴蝶,飞进打开的书里又在我不小心合上时葬身在书页中的苍蝇,瞬间在头脑里闪现出来的人和事,不期而来的种种意象和句子,都可以自由无碍地径入诗歌。我在时间、空间、人称、身份等方面任意切换,古汉语的词和句子、古谚语和谣曲、当下生活中的话语、网络语言,我也尝试着混杂在一起。万事和万物都成了词语,历史和当下建构出句子,思想和情感自带着诗意,这是我想象的语言效果,我正在努力接近。六祖云,一念悟则众生即佛,一念迷则佛即众生,套用他老人家的话,我会说一念迷则诗滞万物,一念悟则万物皆诗。归根结底,诗就是一种语言的玄学。
敬文东:2016年,您有一首短诗《霾中风景》,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如果一切未走向寂灭,我想/我就要重塑传统和山河。”这两句令人振奋的诗行,应该是您多年写作想要达到的目标。您觉得您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赵野:《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尚书·尧典》说,诗言志;《诗纬·含神雾》说,诗者,天地之心,万物之户;《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中庸》说,不诚无物,所以诗人必得诚实,如叶芝说“态度恳切”,方能彻见万物。我想,我是在上述意义上,回溯一种诗学传统。我们最早的诗歌《诗经》,同时具有诗的意蕴和经的意蕴,而诗与经浑然一体,已经就是福柯“词不是指向物,词就是物”的意思了,后世腐儒把诗与经对立起来,或者剥去了诗,或者剥去了经。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何尝不是一个有抱负的诗人应有的理想?既然是重塑,那就表明传统和山河已经坍塌很久了,我们是在废墟或灰烬里开始工作,重塑起来的东西,一定既有过去的材料和质地,又有今天的技术和呼吸,既有过去的厚重,又有今天的温度。至于目标,那永远是在前面,罗素说过,静态的完美和终极的智慧,都是不可企及的。我已经写出了一些自己也心仪的诗歌,还有很多明确的构想和写作计划。我的一些作品,从有写作动机,到最后完成,可能要好多年。写作是我的宿命,是我这一世生命最有意义的事情,我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至于最后能达成什么目标,实现什么结果,真的是一种天意,一种定数,人力不可强求。
2022. 2

赵野 当代诗人,1964年出生于四川兴文古宋,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出版有诗集《逝者如斯》(作家出版社,2003),德中双语诗集《归园Zuruck in die Garten》(Edition Thanhauser,Austry,2012),《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赵野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2017),《剩山—赵野诗选》(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2023)。现居大理和北京。

敬文东,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有《流氓世界的诞生》《指引与注视》《失败的偶像》《随“贝格尔号”出游》《事情总会起变化》《牲人盈天下》《皈依天下》《艺术与垃圾》《感叹诗学》《小说与神秘性》《新诗学案》《李洱诗学问题》《味觉诗学》《自我诗学》《絮叨诗学》等学术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颓废主义者的春天》《梦境以北》《网上别墅》《多次看见》《器官列传》等随笔、小说和诗集,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灵魂在下边》《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用文字抵抗现实》等学术文集。获得过第二届西部文学双年奖·小说奖(2012年)、第二届唐弢文学研究奖(2013年)、第四届东荡子诗歌批评奖(2017年)、第二届陈子昂诗歌批评家奖(2018年)、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批评家奖(2018年);第四届当代中国文学优秀批评家奖等(2019年)。
点击链接可查看:
“未来诗学”专栏往期文章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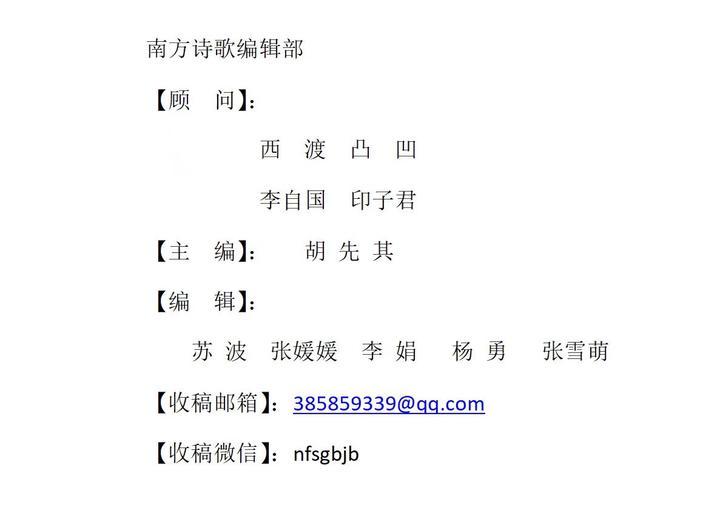
申明:刊头配图如未注明作者,均取自网络公开信息,如涉侵权,请联系编者删除。
《南方诗歌》2021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2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元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二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三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四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五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六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七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八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九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十月目录
“未来诗学”:冯强|文明论“文学性”发微
勾勾:月光月光,一地冷冷的咒语
骆家:荒年好年都往黑夜撒一把葱花
“他山诗石”:吉庆 译|芭芭拉.格斯特 诗五首
欧阳关雪:我为内心的蓝色知更鸟包扎了伤口
阿鲁:天空越来越沉默
杨镇瑜:喊不醒一块透明的铁
蔡建旺:此刻,他的手可以抵达天空吗?
“品鉴”:王之峰|诗的尊严就是人的尊严——读木郎诗札记
卢文悦:骑着青芒果去旅行(修订版)
吕布布:当太阳无法胜任,雨便沸腾而来
轻鸣:我知道宇宙比沙粒还多的秘密
梁威:月光下洒满翩翩飞翔的歉意
远洋:航标灯(组诗)
“诗访谈”:诗人就是星辰大海|黄礼孩答冯娜
刘振周:光明的地址
“黄金台”杯第二届南方诗歌奖征稿启事